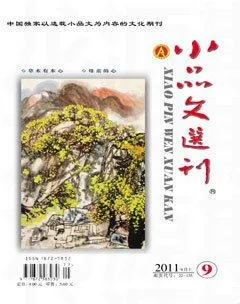唐古拉的綠雪
我所在的城市已經很少看見雪了,就是下雪,也是星星點點的那種,在地上是坐不住的。所以看見的雪也只是一種顏色白色。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顏色的雪。2003年8月底的青藏之行讓我見識到了雪的其他品種。
那是一種綠色的雪。
開始并沒注意,我像所有第一次走青藏線的人一樣,眼睛總不夠使,被褐色的高原和連綿的雪山吸引,間或還要睜大眼睛,看有沒有藏羚羊在地平線上出現。快到唐古拉山口的時候,忽然下起了雪。雪不大,但很急,車上的乘客立即緊張起來,司機則不溫不火地開著車。氣溫急劇下降,人們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緊緊地卷縮著身子。這個時候,我看見了一種異樣的顏色。那是一面山坡,山坡上光禿禿的,沒有牦牛,沒有藏羚羊,更沒有牛羊一類的生靈。其他山坡河谷都是褐色的,而這面山坡是綠色的。我以為是幻境,看了好一陣,才確信,這是一種真實的顏色。那是一種綠,一種淡淡的、溫柔的、似有似無的綠,一種飄忽不定的、游移著的綠。雪下得很清爽,不粘不連的那種,在雪花的紛飛中,依然能看清那是青藏高原罕見的顏色。柔和的、溫暖的、散漫的、綿長的。介于綠與不綠之間,給人嫻靜、優雅、恬淡的那種感覺。雪繼續下著,在頭頂的天空是白色的,而那面山坡上的雪是有色彩的,不管在天上還是地上,都是綠色的,是那種粗略著看無,細看則有的綠。
不一會,就到了唐古拉山口,這是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方,雪依然下著,司機停了車,讓乘客下車拍照留念。公路一側是標注唐古拉山口海拔高度的石碑,上面掛滿紅紅綠綠的經幡和風馬旗,另一側是一尊巨大的石頭雕塑。人們爭相在經幡和雕塑前拍照留念。這時候,有兩個藏民從雕塑后面走過來,手里捧著兩塊石頭,整個軀體被厚厚的棉衣包裹著,臉上只露出兩只遲緩的眼睛。他們沒有穿雨衣,沒有打雨傘,沒有戴防雨的帽子,他們把石頭壘放在公路邊上,轉身走了,一會又捧著石頭過來了。我注意到公路邊的石頭,一塊一塊規整地壘放著,像內地高速公路邊的護欄。兩個人旁若無人地干著,好像我們這伙見什么都稀奇的內地人不存在一樣。
一個人倒了下去,這是一個江南女子。一路上高原反應都很厲害,已經吃了好幾次紅景天和高原安了,但還是倒在了唐古拉山口。手捧石頭的藏民正從江南女子旁邊經過,快速地丟了石頭,把女子扶起來,架到車上,待吸上氧氣才離開。一個男人追趕過去,往他手里塞了一張百元鈔票。藏民褪下手套,將錢握在手里,遞還給那個男人。又戴上手套往雕塑后面走去。我們都注意到了那只褪下手套的手,那是一雙黑色的、骯臟無比的手,不比大同和本溪的煤白凈到哪去。那雙手吸引了我們,同時吸引我們的還有雕塑后面的那面山坡,也是那種奇怪的、恍惚的、飄游著的綠。
那究竟是一面綠色的山坡,還是綠色的飛雪,不得而知。
選自《南國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