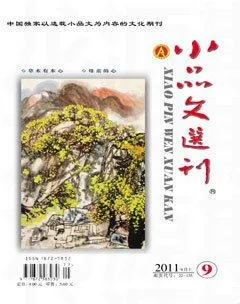最美的剎那
“捕捉宇宙間千變萬化最美的剎那,將之定格,攝入鏡頭,化為永恒。”這是臺灣作家白先勇對臺灣攝影大師柯錫杰的評價。耐人尋味的是,對于柯錫杰的事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攝影作品,卻恰恰是從“丑”開始的。
那是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一天,年輕攝影師柯錫杰到高雄采風。高雄位于臺灣西南部,這里終年綠樹成蔭,花香裊裊。如果將臺北比作一位優雅的紳士,高雄則是一位儀態萬方的淑女。她一顰一笑,都那么迷人。柯錫杰沉醉于這初戀般的美景中,一時竟不知從何拍起了。
就在這時,目標出現了:那是一對帶著兩個小孩、又臟又丑、正在向漁家乞討的盲夫婦……柯錫杰決定,他要暫時背棄一貫堅持的美學原則,將這幅毫無美感的畫面拍下來——如果說在面對邪惡時他的相機是一支槍,那么,在面對弱者時,這冰冷冷的機器則會變得柔情似水。
這幅照片拍攝后不久,柯錫杰就去了日本,進入東京一家權威攝影學校深造。兩年后,他學業結束回到臺灣,就在他躊躇滿志準備干一番大事業時,一次他路過臺南,又遇到了曾在高雄見過的那家人。
幾年過去了,這一家四口仍靠乞討為生,最大的變化是小孩多了一個,父親卻不在了。柯錫杰隨口問了一句,盲女人垂下了頭。不用說,她的丈夫已去了另一個世界。
他決定再給他們拍一次照。但他知道,僅有同情是不夠的,藝術的本質還是要表現美。好在現在的他已經非常有經驗了,懂得在拍攝人物時鏡頭要抽離被拍攝對象的社會身份,讓他們自然入鏡,這樣方可呈現出最“美”的剎那。
但幾個小孩卻一直在鬧,拍攝始終無法進行。盲女人把最小的孩子抱在懷里,在一個小凳上坐下,輕輕地撫摸著他的頭,被施了魔法的孩子很快便閉上了眼睛。
這一幕固然溫馨,但卻是暫時的,在一個連自己的生存都成問題的母親那兒,孩子們談何幸福?于是,柯錫杰開始勸她,如果從孩子的前途考慮,應該將他們送進孤兒院。
盲女人遲疑了一下,但瞬間她就仰起臉,用異常堅定的口吻說:“不,先生,謝謝,孩子只有在媽媽懷里才是最幸福的。”就在女人仰起臉的一剎那,柯錫杰發現,她竟是如此的美,那是鳳凰涅槃、化蛹為蝶般的美……他的手顫抖著,按下了快門。
柯錫杰為這張照片取名“最美的剎那”,但在展出前夕,他又將其更名為《盲母》。他想驗證一下,不經提示,觀眾是否還可以看出那獨特的美。讓他欣慰的是,所有看過這張照片的觀眾都被深深地震撼了……憑借這張照片,柯錫杰一舉成名。
“至情至性,恐怕就是柯錫杰成為一位攝影大師的首要條件。”始終關注柯錫杰的白先勇說。對此,柯錫杰深有感觸,“我的作品沒什么技巧,只和你看到什么有關。”他說,“人要保持心靈的潔凈,心是干凈的,你看到的東西就美。”
選自《潤?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