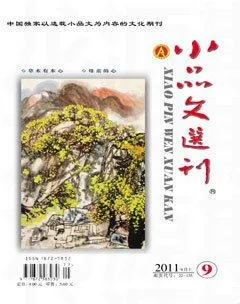母親的心
在這世上,誰愿為你操碎了那顆心仍不知怨悔?是母親,也只有母親!
母親一天比一天老了,走路已經顯出老態。她的兒女都已經長大成人了,各自忙著自己的事,匆匆回去看一下她,又匆匆離去。往日兒女繞膝歡鬧的情景如今已恍如夢境,母親的家冷清了。
那年我去湖南,去了好長時間。我回來時母親高興極了,她不知拿什么給我好,又忙著給我炒菜。
“喝酒嗎?”母親問我。我說喝,母親便忙給我倒酒。
我才喝了三杯,母親便說:“喝酒不好,要少喝。”我就準備不喝了,剛放下杯子,母親笑了,又說:“離家這么久,就再喝點兒。”
我又喝。才喝了兩杯,母親又說:“可不能再喝了,喝多了吃菜就不香了。”
我停杯了。母親又笑了,說:“喝了五杯?那就再喝一杯,湊個雙數吉慶。”說完親自給我倒了一杯。
我就又喝了。這次我真準備停杯了,母親又笑著看看我,說:“是不是還想喝?那就再喝一杯。”
我就又倒了一杯,母親看著我喝。
“不許喝了,不許喝了。”母親這次把酒瓶拿了起來。
我喝了那杯,眼淚就快出來了,我把杯子扣起來。
母親卻又把杯子放好,又慢慢給我倒了一杯。
“天冷,想喝就再喝一杯吧。”母親說,看著我喝。
我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
什么是母愛?這就是母愛,又怕兒子喝,又想讓兒子喝。
我的母親!
我搬家了,搬到離母親家不遠的一幢小樓里去。母親那天突然來了,氣喘吁吁地上到四樓,進來,倚著門喘息了一會兒,然后要看我睡覺的那張六尺小床放在什么地方。那時候我的女兒還小,隨我的妻子一起睡大床,我的六尺小床放在那間放書的小屋里。小屋真是小,床只能放在窗下的暖氣旁邊,床的一頭是衣架,一頭是玻璃書櫥。
“你頭朝哪邊睡?”母親問我,看著小床。
我說頭朝那邊,那邊是衣架。
“不好,”母親說,“衣服上灰塵多,你要頭朝這邊睡。”
母親坐了一會兒,突然說:“不能朝玻璃書櫥那邊睡,要是地震了,玻璃一下子砸下來要傷著你,不行不行。”
母親竟然想到了地震!百年難遇一次的地震。
“好,就頭朝這邊睡。”我說,又把枕頭挪過來。
待了一會兒,母親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又突然說:“你臉朝里睡還是朝外睡?”
“臉朝里。”我對母親說,我習慣右側臥。
“不行不行,臉朝著暖氣太干燥,嗓子受不了,你嗓子從小就不好。”母親說。
“好,那我就臉朝外睡。”我說。
母親看看枕頭,摸摸褥子,又不安了,說:“你臉朝外睡就是左邊身子挨床,不行不行,這對心臟不好。你聽媽的話,仰著睡,仰著睡好。”
“好,我仰著睡。”我說。
我的眼淚一下子又涌上來,涌上來。
我沒有想過漫漫長夜母親是怎么入睡的。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老了,常常站在院子門口朝外張望,手扶著墻,我每次去了,她都那么高興,就像當年我站在院門口看到母親從外邊回來一樣高興。我除了每天去看母親一眼,幫她買買菜擦擦地板,還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母親!我的矮小、慈祥、白發蒼蒼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