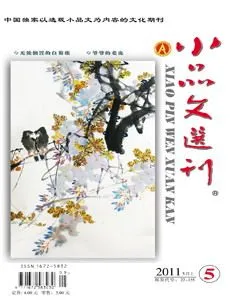動(dòng)人心弦的絕唱
那只德國(guó)種的褐色芙蓉鳥,來(lái)我家有六七年了,當(dāng)時(shí)和它一起來(lái)的還有一只日本種黃芙蓉,它倆都有一副美妙甜潤(rùn)的歌喉,時(shí)常一起歌唱。但好景不長(zhǎng),那只日本芙蓉在一次沐浴時(shí),被阿姨用澆花的噴壺給嗆死了,那是2003年的悲劇。德國(guó)種老鳥那時(shí)還年輕,可能是目睹了兄弟死去的慘景,從此除了吃喝一聲不響,我們懷疑它是不是得了憂郁癥。為不讓它太寂寞,我又領(lǐng)回了現(xiàn)在這只日本種小黃鳥。它像個(gè)傻乎乎憨厚的小伙子,在我晃來(lái)晃去領(lǐng)它回家的路上,什么也不怕,只顧埋頭吃米。到了家就直著嗓子大叫。老鳥對(duì)它的出現(xiàn)毫不理會(huì),對(duì)它河北梆子一樣的喊叫不屑一顧,一年半中老鳥沒有正眼看過(guò)小鳥,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老鳥就會(huì)狠狠地啄咬小鳥,盡管小鳥用各種啼聲對(duì)它獻(xiàn)媚,老鳥仍然深深地沉浸在對(duì)老伙伴的思念中。
小鳥會(huì)回應(yīng)我們的呼叫,老鳥不會(huì)。我們一直以為它啞巴了。妹妹從美國(guó)回家時(shí)認(rèn)為我們冷落了老鳥,在我們熱情地叫“小鳥、小鳥”時(shí),她總是蹲在老鳥的籠子旁,一遍遍地叫著“老鳥、老鳥”。一天,老鳥用沙啞的嗓音,“嘰”的一聲回應(yīng)了妹妹的呼喚,打開了封閉一年半的喉嚨。我們歡呼雀躍,每天鼓勵(lì)它、叫它,它的聲音越來(lái)越響。結(jié)果,當(dāng)它開始歌唱時(shí),是那么嫻熟,那么舒展,特別是用舌的顫動(dòng)讓氣流滾動(dòng)發(fā)出的一串串的顫音,簡(jiǎn)直是美妙難言。就這樣老鳥與小鳥開始了西洋美聲與傳統(tǒng)戲曲的結(jié)合。這一對(duì)“斷背山”似的好兄弟,當(dāng)一個(gè)見不到另一個(gè)時(shí),就會(huì)焦急地相互呼喚,宛如隔山對(duì)話。
一年年過(guò)去,老鳥老了,小鳥成年了。老鳥歌唱的聲音越來(lái)越低,歌唱次數(shù)越來(lái)越少。小鳥卻越來(lái)越活潑,越來(lái)越調(diào)皮。只要你稍不注意,籠門沒關(guān)嚴(yán),它就會(huì)跳出來(lái)在客廳里大搖大擺地踱步,甚至飛到窗邊向樓下張望。但它又知道它們這種鳥飛出這扇窗不是摔死就是餓死,它永遠(yuǎn)不敢冒這個(gè)險(xiǎn)。它真是個(gè)傻小子,每次都找不到回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