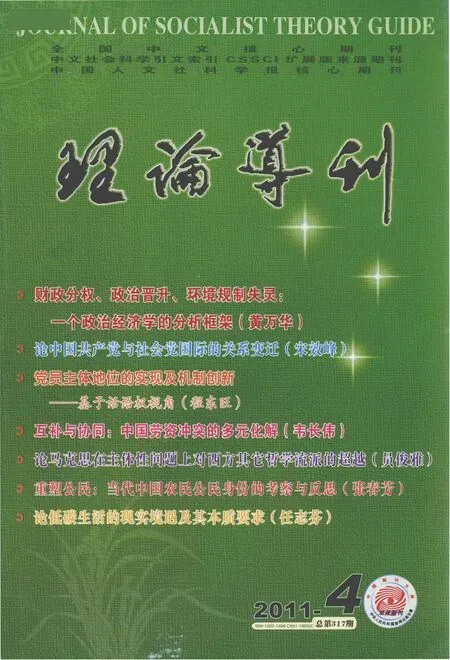略談詩歌的跨文化互文性解讀
王衛強
(寶雞文理學院外語系,陜西寶雞721013)
略談詩歌的跨文化互文性解讀
王衛強
(寶雞文理學院外語系,陜西寶雞721013)
讀者對文本的解讀不可避免地會與已知文本產生關聯,在相關文化網絡中發生聯想,從而使其與前文本形成互文關系。對詩歌的解讀也是如此,首先讀者在同一語言中,然后在跨語言、跨文化的層面尋找互文關系。比較漢語詩詞,發現其與英文詩歌傳統雖有所不同,但在題材甚至是語言表現形式上,兩者之間卻多有相似之處。通過英漢詩歌跨文化互文性的欣賞和解讀,讀者不但可以體會譯詩的奇妙,還可以讓心靈在英漢詩歌共通的審美意境之中自由馳騁。
詩歌;跨文化;互文性
(一)
詩歌之美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詩人的主觀創造,更是讀者的意念、感受和聯想共同作用的產物。詩歌文本一經出現,就完全或部分地取決于讀者的創造性解讀,通過文本所觸發的讀者的認知圖式和前文本框架,在多文本互文的運作過程中產生切身體驗和審美感受。對每一首詩歌,讀者必然會在自己已知的文本中搜尋相似或相關的內容和形式,并結合自己的體驗做出合理而特有的解讀。這種互文性操作可以是同一語言內的,也可以是跨語言的、跨文化的,當然首先是同一語言內的。但對于英語詩歌來說,漢語讀者必定會將某些異域文化的東西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框架中,做出具有調適性特征的解讀和賞析。這種互文性解讀可以從對以下幾個詩人詩歌的閱讀和分析中得到證明。
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1770-1850)堪稱英國文學史上詩歌時代的代表人物,他以其與柯勒律治合著并于1798年出版的詩集《抒情歌謠集》開啟了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時代,并與柯勒律治、騷塞并稱為“湖畔詩人”。華茲華斯簡潔和純粹的語言很多都表現出詩人自己對大自然的熱愛,細致傳神地描寫了大自然中美麗的湖泊、江河、草地、森林、天空、云彩等。[1]8他的詩作如《我像云一樣孤獨地漂泊》和《孤獨的刈麥女》可謂英國詩歌的經典和絕唱,對浪漫主義文學在英國的盛行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連他的一首短詩《她住在人跡罕到的路邊》,也給人無限的跨文化詩歌聯想,使人驚嘆于英漢詩歌相似的審美情趣和可以共享的詩歌意境。
《她住在人跡罕到的路邊》只有短短的三個詩節,用同樣簡潔而純粹的語言,把一位花兒似美麗卻孤單的女子形象簡潔而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她的美似乎不是那么短暫的一瞬在天空中如流星般劃過,而在詩人的心理留下了永遠揮之不去的愛戀和傾慕,從而使人浮想聯翩、情緒蕩漾。第一詩節用直述的手法描述姑娘的人生際遇:由于不被人賞識而處于孤獨之中;第二詩節以類比的手法,把生長在曠野中的嬌艷而孤獨的紫羅蘭與“住在人跡罕到的路邊”的美麗的姑娘相比較,更加凸顯出姑娘的凄美人生;第三個詩節用了對比的手法,敘述了姑娘生前和死后給人帶來的影響:生前不被人看重,死后才使人感到猶如失去珍寶一樣的痛楚,但悔之晚矣!這只是詩人的感慨萬端?實際上,每個人讀到此處便會聯想到自己的人生境遇和心目中的那位或真實或想象的才子佳人,禁不住潸然淚下,難于釋懷。
從詩歌結構來說,這首英詩的結構與漢語詩歌的結構略有不同。漢語詩歌多采用比興的手法。比興是中國詩歌中的一種傳統表現手法,宋代朱熹認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也就是說,比就是譬喻,是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鮮明突出。在《詩經》、《離騷》中都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創作的傳統,即所謂“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中國第一部長詩《孔雀東南飛》開頭用“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起興,用具體的形象來激發讀者想象,從美禽戀偶聯想到夫妻分離,這樣就給全詩籠罩上一種悲劇氣氛,起了統攝全詩、引起下面故事的作用。以賀敬之的詩歌《回延安》為例,“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即為起興,表現出延安在詩人心中如母親般的崇高地位,因此詩人才會有對延安故地的無限向往之情:“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英語詩歌與中國讀者所熟悉的比興結構的詩歌雖有不同,但從敘事的角度來說,詩歌開頭首先引出人物并描述其所處的境況,其次將人物的境況與自然中的事物進行隱喻性或象征性的描寫,也是英漢讀者大體相同的認知心理。在英詩的解讀過程中,不妨將原詩結構加以調整,使其適合漢語讀者的傳統詩歌閱讀習慣,就能更好地觸發漢語讀者的認知框架。我們不妨將漢譯詩歌的第二詩節前移,并將其中的語詞稍加修改,這樣會讓漢語讀者讀起來思路順暢,使譯詩也更加流暢、連貫,更能給人美的感受。試看改譯(根據黃杲炘譯文):
一朵半隱半現的紫羅蘭,
開在長滿青苔的石旁!
美得像顆星星忽閃忽閃——
獨一無二地掛在天上。
一位多吾河畔出生的姑娘,
居住在人跡罕至的路邊;
她嬌媚迷人卻無人贊賞,
更無人把她深深地愛戀。
英詩中描述的是一位姑娘的孤獨和凄涼哀怨的處境,姑娘就像長在深山曠野中的紫羅蘭,只能開在長青苔的石旁,與漢語讀者所熟知的“長在深山無人識”的意境、寓意恰好吻合。
(二)
即使是那些為世人所經常視而不見的普通的鄉村景象,普通的生活場景,普通的生命跡象,在中外詩人的筆下也得到了升華,引發人無限的情愫。英國十八世紀“墓園派”詩人托馬斯·格雷(1716-1771)的《墓園挽歌》的開頭是這樣的:
晚鐘響起來一陣陣給白晝報喪,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聲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腳步踉蹌,
把整個世界留給了黃昏與我。(卞之琳譯,下同)平靜的鄉村,爬滿常春藤的塔寺,天將黑,四周蕭瑟蒼涼,月亮慢慢地升起,牧人趕著羊群,羊群蜿蜒入村,農人勞作一天后邁著疲憊地步履回家,這又是另外一種人生的際遇的寫照,其意境和氣勢頗與中國古典詩詞“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等詩詞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幾首詩,都用沉靜哀怨的語調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或者直接對大自然的景物進行描述,或者通過對比來反映詩人特定的心理感受。
格雷的《墓園挽歌》中所描寫的那些一文不名的鄉村老叟和婦人,盡管可能有彌爾頓的才華,有英雄的稟賦,但由于缺少后天的機遇和培養,天生的才氣未被發覺而變成了平庸的凡人。因此,詩人感嘆:
世界上有多少晶瑩皎潔的珠寶,
埋在幽暗而深不可測的海底;
世界上有多少花吐艷而無人知曉,
把芳香白白散發給荒涼的空氣。
接著,對那些雄心勃勃和有權有勢的人也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闡釋了詩人對生命意義的理解:
門第的炫耀,有權有勢的煊赫,
凡是美和財富所能賦予的好處,
前頭卻等待著不可避免的時刻:
光榮的道路無非是引導到墳墓。
與華茲華斯和格雷一樣,通過描寫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場景,來表達詩人自己的對生命存在意義的理解和感悟,被譽為“美國資產階級革命詩人”、“美國詩歌之父”的菲利浦·弗瑞諾(1752-1832)的詩歌《野忍冬花》中也有這樣的詩句:
美麗的花呀,你長得這么美麗,
卻藏身在這僻靜沉悶的地方,
甜美的花兒開了卻沒人親昵,
招展的小小枝梢也沒有人觀賞,
沒游來蕩去的腳把你揉碎,
沒東攀西摘的手來催你落淚。(吳偉仁、張強譯)
這些詩句不僅讓人為野忍冬花默默無聞、孤獨處幽的境遇而感嘆,為她短暫的生命而嘆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詩人身心入境,推己及“人”的自賞之心溢于言表。[2]63詩人在字里行間描繪出野忍冬花超凡脫俗的境界:獨處幽遠使她“避開庸俗粗鄙的目光”,她的“難免消逝的美使我銷魂”,雖然“這來去之間不過是一個鐘點”,但“這就是脆弱的花享有的天年”。花草別無所求,自己也就無所謂惋惜,看花人將自己的命運與花的處境相比較,在移情的作用下,給花賦予了人的情感,使讀者有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相似情感,也正如同在華茲華斯的前述詩歌里所表露:姑娘的離去猶如花兒落英而逝,美麗雖然失落卻又變成了永恒的記憶。
無論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還是自然界高級生物人自己,新陳代謝、生命輪回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野忍冬花的無欲無求,帶給她的是既短暫而又永恒的美,沒有嫉妒也沒有驕傲,只是盡享自己“脆弱”的天年。不像野忍冬花的常開常敗、習以為然,人生卻是變幻無常的,這不禁使人聯想到麥克白在聽到妻子的死訊之后對人生的感嘆:“熄滅吧,熄滅吧,這短暫的蠟燭!人生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像一個演技拙劣的伶人,在舞臺上一會兒趾高氣揚、發號施令,一會兒眉頭緊蹙、焦躁不安,一旦走下舞臺,便會銷聲匿跡。這是一個傻瓜講述的故事,充滿了喧嘩與騷動,到頭來卻沒有任何意義。”
通過以上賞析不難看出,對詩歌的互文性解讀,甚至是跨文化的解讀,為漢語讀者理解英文詩歌的主題,深刻領會詩歌的意境,把握詩歌的美感可以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三)
無論是讀者的閱讀或者是譯者的翻譯,都會在所讀或所譯文本的觸發下,自然而然地牽引出一個文本或文化網絡,從中找到興趣點,從而對文本做出深刻周到而又別出心裁的解讀。根據羅蘭·巴特的觀點,每一次對文本的閱讀都可以看作是重寫文本,這是由無數引文所構筑出來的文本,文本呈現出來的形態,其實完成于讀者的閱讀,而不是作者的寫作。——正所謂“作者已死”。讀者審美的、文化的或者生活經歷的等等先在的知識儲備都影響著讀者閱讀作品;互文性的狀態是無限編織、纏繞或延伸的狀態,讀者(或譯者)是互文關系中的一個功能單位,不具主體性。詩歌或其它類型的文學作品,與共同文化空間有著深刻的聯系,要產生豐富的聯想效果,必須依賴共同的、先在的文化系統;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不是鎖在文、句之內,而是進入歷史空間的一種交談。”[3]
詩歌作為一種文學文本,對其闡釋需要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漸次遞進過程:辨析語言、體察結構、構建文本間聯系。[4]讀者(或譯者)對文本意義的解讀就經歷了這樣的動態過程。讀者(或譯者)在對前文本的掌握和認識的基礎上體察到此文本與它文本在語言、結構、主題等方面的聯系,從而產生豐富的聯想,得到對文本的多層次解讀,就像游客對風景的感覺,不是建立在無緣無故的僅是對物質對象形態感覺之上,而是加入了各種因素,諸如文化的、習慣的、心境的、愛好的等背景因素。對美的感覺不是看出來的,而是聯想得出來的。以前信息的儲備越大,感受就越深刻,得出來的美感愉悅就越豐富。因此,互文性是讀者更好地閱讀詩歌、理解詩歌、把握詩歌的前提條件。
人類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共性,文化的表達形式——語言也具有共性。尋找共享的文本和文化網絡有助于對不同語言文本的理解和閱讀。比如,愛情是人類最美好的、共同具有的情感,在中外作品中的表現數不勝數,但對愛情的幾近相同的表現需要我們不斷積累閱讀經驗來獲得。愛情也是一種人生際遇,歷代中外文人墨客贊美、描述它,美麗的主人公在不同國籍、不同人種的詩人筆下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1788-1824)在他的詩歌《她走在美的光彩中》中這樣寫到:
增加或減少一份明與暗,
就會損害這難言的美;
美波動在她烏黑的頭發上,
或者散布淡淡的光輝;
在那臉龐恬靜的思緒,
指明它來處純潔而珍貴。(查良錚譯)
詩中有西方人對美的描述:增一分則太亮,減一分則太暗,美應是一種恰到好處。蘇軾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白居易的《長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垂淚”;杜甫《麗人行》中的“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等等都是對物之美和人之美的生動描繪。更有奇者,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里對鄰家女子之美的描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雖然有遙遠的空間和時間之隔,詩人對于美的感受和表述竟如出一轍。在欣賞這些詩詞歌賦時,哪個讀者不會浮想聯翩、由衷感嘆呢!因此,要準確而又深刻地把握詩歌的主題和內涵以及美學價值,沒有跨文化、跨文本的想象與聯想,不從互文性的角度進行解讀,是難以實現的。
再如,十八世紀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1759-1796)在他的詩歌《一朵紅紅玫瑰》中寫道:
縱使大海干涸水流盡,
太陽將巖石燒作灰塵,
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只要我一息猶存。(吳偉仁、印冰譯)
讀到這首詩,讀者會一下子想到一句常常聽到的愛情誓言:海枯石爛終不悔。《漢樂府》中《上邪》云:“上邪!我欲與君長相知難。山無棱,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又有敦煌卷子中唐代無名氏所作《菩薩蠻》一首:“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黃河海底枯。白日參辰觀,北斗回南面。”
綜上所述,即使是不同語言文化中的詩人也可能會遭遇相同的人生際遇,產生相似的精神和情感,擁有相似的認知和審美體驗,以相似的語言形式表達出人的生命意義。通過詩歌表達出人類的共通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狀況以及人生感悟,是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詩歌產生互文性的基礎。正是有了詩歌之間跨文化、跨語言的互文性,不同語言文化的讀者和譯者才能很好地體會、把握和翻譯詩歌。通過詩歌的跨文化互文性解讀,無論是讀者還是譯者就一定能夠讓心靈在英漢詩歌共通的審美意境中自由馳騁。
[1]吳偉仁,印冰.《英國文學史及選讀》學習指南(第二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2]吳偉仁,張強.《美國文學史及選讀》學習指南(第一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3]南帆,劉小新,練暑生.文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44-45.
[4]姚成賀,張輝.動態·多元·互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論[J].學習與探索,2010,(3).
I106.2
A
1002-7408(2011)04-0088-03
陜西省教育廳2010年專項科研計劃項目(2010JK027);寶雞文理學院重點科研項目(ZK109)。
王衛強(1967-),男,陜西眉縣人,寶雞文理學院外語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英美文學。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