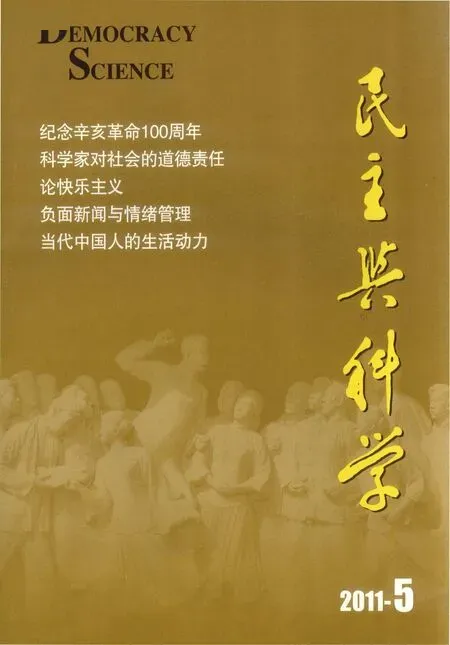由辛亥革命談知識分子的品格
■梁曉聲
由辛亥革命談知識分子的品格
■梁曉聲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紀念和研討的活動都很多。而紀念是一回事,研討是另一回事。紀念是要再次評價的,評價一旦成定論,紀念就差不多體現成儀式了。但是研討不同,研討不著重于儀式的色彩,研討的意義在于匯聚思想認識的多元能量。研討也是紀念,是以思想上的再認識來表達的一種更虔誠的敬意。
另外,對于思想,多元不是消解能量的現象,恰恰相反,具有積極能量的思想往往就是在多元的現象中集中和提升了。沒有多元,就沒有真思想的那種提升、那種能量,也形成不了、產生不了特別有價值的思想。有價值的思想就是在多元的碰撞中產生的。
所以,就辛亥革命討論辛亥革命是一回事,將辛亥革命這一當年中國之大事當作一個核,聯系當年中國的國民性、知識分子之使命感、責任感,以及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國民到后來一直到今天的心路歷程,這是更全面的研討。
中華民族的苦難太長遠,太深重了,我在讀書時,偶然記下了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的遺書——《與妻書》:“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愿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我看到這里受到了震撼,在那個年代,我們的民族產生了這樣的青年。我突然想到陳獨秀和吳越,兩個人是好朋友,但互相爭執起來,以致于打斗起來,爭的是什么問題呢?兩個人都要爭著去完成一項刺殺清王朝即將出洋的五大臣的任務,吳越要去,陳獨秀也要去,他們那時只不過20多歲,最后吳越說,在完成這種匹夫之勇的事無非是血劍之死,橫尸兩具,和那種喚醒我們的民眾,建設一個中華民族強盛的國家,這二者之間,哪個任務重?陳獨秀說,當然后者重,吳越說,那你來完成后者,我來完成前者。
也想到汪精衛和陳碧君,他們后來是漢奸,但他們年輕時是那樣斗志激揚。在那個暴力革命的時代,汪精衛為完成刺殺攝政王的任務,陳碧君知道后,初次見面就說,我知道你此去可能無回,我非常欽佩你,因為你是為國家為民族而去赴死的,我沒有什么可相贈的,今晚你就留宿在我這里吧。
我們講中華民族的古典精神,比之先賢,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夠。蔣百里任保定軍事學院校長之后,曾要求自己的軍官學生們要英勇善戰,但他們后來投降打了敗仗。蔣百里就說自己教得不好,教得不好是要責罰的,說完就拔槍自殺。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中國是強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了,但問題也同時出現,歷史的、現實的、更深層的,但我們大小知識分子卻沒有多大的覺悟,這是可悲的。
有個問題我始終困惑不解,同樣是漢人,為什么康有為、梁啟超們和孫中山們就不一樣呢?康梁主張君主立憲,因為他們跟王朝走得近。王國維這樣的知識分子跟王朝走得更近,他是幼王師。我的問題是,一個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在外族統治的270多年里,他們的思維是怎么樣的逐漸演變的。在時間的流程中,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們、精英們,在一代代時間的流程中,他們和一個外族的專制體,是怎樣過渡的。這個過渡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們今天的一些思維,一些想法,有沒有基因上的關系。另外,一般的國民也是非常奇怪的,清朝最初統治時,最早的皇帝死的時候,他們沒當作是自己的皇帝死了,心里還很高興呢!但是到晚幾任的皇帝死了,后來的漢民族也掉眼淚,也如喪考妣了。這里有什么問題呢?魯迅當初為什么那么強烈的批判國民性,以及這國民性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大唐的時候沒有將國民性叫做劣根性,魯迅指的劣根性就是奴性,而且奴在心里,這在歐洲是沒有的。同樣的封建國家,是不一樣的。晚宋之后不久漢民族就被元朝所統治。之后明朝,之后大清270年,因此600多年的歷史中,我們有360余年兩度是被外族統治著。這個民族這么長時間在這個狀態下,沒有奴性是不可能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沒有奴性,腦袋就掉了。那時的知識分子,甚至小工匠,大家血液里都記著——我一定要保持奴性。保持奴性就能生存,沒有奴性是絕對不能生存的。因此,這個國家有這么強的奴性。辛亥革命的時候,有這么一批人要造反,既要造封建統治的反,也是造外族統治的反,還要造自己本身奴性的反。所以,我們以后再仔細討論辛亥革命意義的時候,把文化的元素都包容進來,對于我們思考從五四以來我們知識分子是怎樣走過來的,以及今天我們知識分子要秉持一種什么品格,我認為都是有點益處的。我認為,知識分子還是要有一點知識分子的樣子,這一點起碼的樣子就是知識分子說話要像知識分子,不向任何人承諾說的話一定是正確的、說的話可持續的正確。我不承諾永遠正確,但要力求說真話,包括我說錯誤的話的權利,真那么想的,就真那么說出來。
我對中國的將來是滿懷希望的,因為這世界必定要進步。世界已是平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例外。
魯迅當年曾言:說現在好的,留在現在!說將來好的,隨我前去!
我加上一句——說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而且我還要對想要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人說——“除有時夢里常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