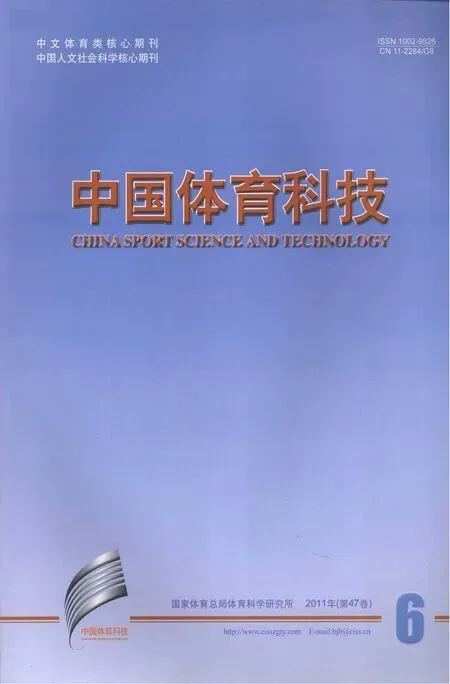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轉型機制
申國卿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勃興,以地域文化為主題的理論研究異軍突起,形成了當代國內學術領域的一個突出熱點。作為中華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交融的歷史產(chǎn)物,作為中國地域文化一項獨具特色的組成部分,中國武術所具有的顯著的地域特征也日漸吸引了學界的關注,圍繞地域武術文化的相關成果如雨后春筍,正持續(xù)掀起著21世紀初期武術文化研究的一波新潮。方興未艾的地域武術文化研究構成了當代中國武術發(fā)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回顧地域武術文化的演進歷程,總結地域武術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探索地域武術文化的轉型機制,對于中國武術發(fā)展而言,具有重要而積極的時代意義。
1 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宏觀解讀
追溯歷史,中國文化地域的產(chǎn)生大約起自舊石器時代中晚期[2],歷經(jīng)新石器時代乃至夏、商、周的發(fā)展、演變,最終成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從削石為兵的原始萌芽一路走來,跨過上下數(shù)千年的漫漫時空,中國武術的歷史進程也深深地烙上了地域文化的印記。伴隨著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熔鑄、熏陶,中國武術淋漓盡致地演繹著中華地域文化博大精深的獨特魅力,同時,也展現(xiàn)出與地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的水乳交融。
1.1 隴上拳家存古意——地理環(huán)境對地域武術文化特色的影響
從文化發(fā)生的角度來看,特定的自然地理條件往往決定了一個獨立文化體系的最根本性質和特征,即使在同一文化體系中,內部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也往往促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生成[6]。不同類型的地理環(huán)境特點對于相應地域武術文化的風格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武術中一貫盛行的“南拳北腿”之說,可謂恰到好處地概括了由于地理環(huán)境不同而形成的南北武術的地域性差異。北方地勢平坦,自然環(huán)境相對惡劣,人的體質較為強壯,其燕趙、齊魯?shù)鹊赜蛭湫g以剛為主,大開大合的腿法運用較多;南方氣候溫潤,地形多樣,故其荊楚、吳越等地域武術多以靈巧、柔化的拳法聞名[19]。因此,正如前人所言:“技擊之有南北二派,實由于天時地理之關系,出諸天演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23]
地處五嶺之南、內涵粵、港、澳三地的嶺南武術,便是中國地域武術文化地理環(huán)境特點的一個例證。嶺南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之處,因位于五嶺之南而得名,史稱“化外之地”。五嶺地區(qū)層巒疊嶂,猶如一道天塹屏障,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與北方中原地區(qū)的文化聯(lián)系,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在客觀上也保障了傳統(tǒng)嶺南武術文化的原真性和整體性特質。時至今日,在中原等地域武術文化大多隨著時代與環(huán)境演進而劇烈變遷甚至瀕臨消亡之際,嶺南武術仍因較多地保存了古樸的傳統(tǒng)面貌而倍顯珍奇。另一方面,廣東等地海洋環(huán)抱的地理環(huán)境因素則又賦予了嶺南武術進取務實的發(fā)展特點。伴隨著嶺南人民越洋過海到世界各地通商謀生的腳步,嶺南武術中的南拳、五祖拳、蔡李佛拳、詠春拳等也開始在東南亞、美洲大陸等地流傳。
與嶺南情況相同的還有隴右武術等。隴右原指隴山(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之地,地處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匯地帶,歷史上,隴右武術因地理環(huán)境之限而一向與外界交流甚少,至今有些民間拳種仍然是“躲在深閨人未識”[28]。而“隴上拳家存古意”之說[18],也正是隴右地理環(huán)境特點對于該地域武術文化特色影響的真實寫照。
1.2 荊楚長劍天下奇——兵戈紛爭對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的推動
在漫長的發(fā)展史上,軍陣殺伐中的兵戈紛爭構成了中國武術的一個重要內容,歷代軍事典籍中的一些武藝記載,如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俞大猷的《劍經(jīng)》等,也一貫被奉為傳統(tǒng)武術的經(jīng)典。毫無疑問,持續(xù)不斷的軍事戰(zhàn)爭對于中華地域武術文化的發(fā)展及其特征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以中州武術為例。古河南之地俗名中州,也稱中原,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與“逐鹿中原”等成語更證明了這一地域的軍陣殺伐之久。據(jù)《中國歷代戰(zhàn)爭史》記載,從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六國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的2 061年間,華夏各地域共有重要戰(zhàn)役721起,其中發(fā)生在中州的則為120起,位居榜首[13]。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中州地域的兵戈紛爭前后延續(xù)近600年;魏晉南北朝持續(xù)400余年的戰(zhàn)亂又為中州帶來了空前劫難,史載中州大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11]。兵禍連結之下,民眾不得已習武圖存,磨煉出了尚武強悍的勇健之風。影響所至,發(fā)源于這片土地上的少林武術與陳氏太極拳馳名中外,成為中州武術兩張文化名片。
其他的代表性地域武術還有隴右、荊楚等。頻繁的戰(zhàn)爭促成了隴右的尚武傳統(tǒng),《漢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四》中皆有隴右各地“修習戰(zhàn)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多尚武節(jié)”、“名將多出焉”等文字記載;歷代詠隴詩詞如“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等也充分反映出了戰(zhàn)爭對隴右武風的影響[5]。兵戈紛爭對于南方的荊楚武術文化發(fā)展同樣影響甚深。嚴峻的軍事形勢迫使楚“在開國之時就重視武力,以求得國勢的鞏固和發(fā)展。周王朝的不斷征伐,促使了荊楚武術的迅速成長”[12]。在戰(zhàn)爭的需求之下,青銅被楚軍大量用來制造武器,由青銅制作的楚國長劍也在當時獨步群雄,“成為天下矚目的利器”[29],其“工藝之精,居列國之首”[26]。明朝末年,由于吳越地域遭受到倭寇的嚴重侵擾,以戚繼光等為代表的一批優(yōu)秀的軍事家先后被派赴吳越定倭,殘酷的軍戰(zhàn)啟發(fā)著這些武藝高強的將領紛紛開始了針對性極強的軍事武藝訓練;國內其他地域的一些著名的武術家也主動展開了圍繞日本刀法的中日武技比較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武術技法總結、探討。“對后世影響較大的一些有關武術論述,不僅在這個時期相繼問世,而且數(shù)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是秦漢以來未曾有過的。”[16]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的《中國武術史》中收錄和介紹明代兵家所撰的10部著述有8部出于吳越地域[5],這場戰(zhàn)爭對于吳越地域乃至中國武術發(fā)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1.3 巴蜀武林移民多——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中的交匯融合現(xiàn)象
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綿延不絕的發(fā)展過程中,不僅充滿著不同地域之間的武術文化交流與共融,而且,也是各地域武術文化長期交匯、融合的必然結果。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的這一特征在巴蜀武術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xiàn)。歷史上,秦漢大移民和湖廣填四川,使巴蜀地區(qū)成為多種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典型區(qū)域。“在移民文化的長期涵化和浸染之下,巴蜀武術的拳種分布也呈出了明顯的地域特點——川西以成都為中心,其拳種風格接近南方拳種,以靈巧技法為主,代表拳種如火龍拳。川東則以重慶為代表,拳勢大而重,進退奔馳,其風格趨向北方,代表拳種如余家拳。”[3]外來移民文化與巴蜀本土文化的水乳交融,猶如一陣清新的風,孕育出巴蜀武術瑰麗奇特而又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同時也突出地彰顯了中國地域武術發(fā)展史上一脈相承的文化交融特征。
類似的例證還有吳越、燕趙等地域。早在三國之前,經(jīng)過秦皇漢武等延續(xù)200多年的大規(guī)模移民,吳越地域的居民構成已經(jīng)發(fā)生了較大的轉變;從東吳到南宋,著名的永嘉之劫、安史之亂、靖康之難又為吳越帶來了三次空前的移民潮流;鴉片戰(zhàn)爭把吳越的上海推向了近代中國發(fā)展的前沿,從而又為吳越地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外來人才。伴隨著外來人口和異域文化的涌入,吳越武術發(fā)展自然而然地吸收百家武藝之長并潛移默化地勃發(fā)出文化融合的動力。明末倭亂之際,戚繼光等帶來的中原各家武技在吳越大地開花結果;另一方面,以吳越為中樞的中外武術交流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主要的標志就是強悍的日本刀法的引入和武術“手搏”之技外傳東瀛。[5]
位于北方的燕趙地域同樣表現(xiàn)出了與巴蜀、吳越武術相似的文化交融特征。早在戰(zhàn)國時期,燕趙大地上就有了以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為代表的漢民族積極吸取游牧民族文化優(yōu)點的先例;此后,北魏、遼、金、元、清等北方游牧文化對于燕趙主流農(nóng)耕文化的沖擊都是無比巨大的;明清時期,燕趙地域也曾經(jīng)多次遷入過大規(guī)模的外來移民。通過民族的大融合,北方民族的剛健之風有力地促進了燕趙地域尚武精神的發(fā)展;燕趙武術中的一些著名拳種,如八卦掌、形意拳等也無不是融攝多家武藝的產(chǎn)物;即使名聲相對稍遜的其他一些拳種,如祁家通背拳等,同樣能夠體現(xiàn)出互參互融的武術發(fā)展特點——祁家通背拳始傳于河北冀梁,經(jīng)過與江南郄蠻子以槍換拳以及從河南馬氏學習刀法等過程,在廣泛吸收多家之長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槍、刀、手為一理的祁家通背拳種,其老祁派展現(xiàn)了燕趙地域的剽悍民風,少祁派剛中寓柔的特點則又體現(xiàn)了燕趙武術的融匯貫通傳統(tǒng)。[21]
1.4 齊魯重德隆技擊——地域武術文化風格中的社會風尚作用
作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地域武術的整體風格不可避免地經(jīng)受著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風尚的宏觀影響,以技擊聞名的齊魯武術便因其處于儒學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故鄉(xiāng)而尤為盛行教化和德行之風。“齊人隆技擊”[15]的文化現(xiàn)象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管仲的練兵體制及國民教育思想,其后的孫臏、司馬穰萓等軍事家也均把“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人本思想放在首位,與“以武止戈”的武德追求堪稱珠聯(lián)璧合。孔子的“仁學”理念追求與文武兼?zhèn)涞摹傲嚒苯逃枷雱t影響更為深遠,其倡導“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射禮可謂中國武德文化的經(jīng)典,“君子無所爭,爭也君子”的觀念在華夏大地一直深入人心。源遠流長的尚武重德傳統(tǒng)造就了齊魯?shù)赜驍?shù)不勝數(shù)的俠義之士,著名的大俠荊軻、曹沫等一向享有武林盛譽,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同樣膾炙人口,而追求兼愛、非攻理想的墨家弟子也是有口皆碑。風尚所至,齊魯各武術拳種的技法拳理對于德義思想亦均有體現(xiàn),如著名的華拳就以儒家風范見長。《論語》曰:“勇者無懼”;《華拳譜》講:“善搏者以勇為先”;孔子提倡“文質斌斌,然后君子”,華拳則強調形健質善;儒家倡導“中庸之道”,追求“知、仁、勇”三德功效;華拳恪守“無過而不及”,以“精、氣、神三華貫一”為行拳要旨。[8]
社會風尚對于吳越、嶺南等南方地域的武術文化風格影響則又另具特色。自宋以來,中國武術的表演性和娛樂性功能一貫在吳越地域有著突出的展示。所以,《中國武術史》對此評論道:“偏安南方長江流域的漢族政權多享樂茍安,崇尚聲色玩樂。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娛樂性武術得到了較大的促進。”[7]兩宋政權皆以崇文抑武而凋零,其浮華奢侈之風也以一貫之,吳越地域商業(yè)活動本就發(fā)達,南宋政府定都臨安后浮靡之習益盛,流俗所至,曾經(jīng)風行于中州開封的瓦舍武術表演也在吳越之地重現(xiàn)高潮。嶺南又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代官宦貶謫流亡之地,宋、明亡國之余響也皆以此地為舞臺,離鄉(xiāng)之苦與亡國之痛的長期熏染,又使得當?shù)刂伊x節(jié)烈之士代有才出,教門、會黨義舉風起云涌,同時也與武術發(fā)展產(chǎn)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如嶺南武術中著名的洪拳和蔡李佛拳等就與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天地會“洪門”有著密切的淵源,而廣東南拳“勇猛剽悍、硬磕硬劈”的剛猛之風,也與嶺南的地域文化心理有一定關系。[14]
1.5 燕趙武藝京師善——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中的都市傳播效應
早在漢朝之際,就有“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的武技總結[9]。回顧中國武術歷史,各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中都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出了明顯的都市傳播效應,位于不同地域的各大都市幾乎皆毫無例外地成為所在地域的武術文化中心。近代以來,以北京和上海、廣州等為代表的都市,由于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方面所具有的顯著優(yōu)勢地位,武術傳播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就更為突出。
在燕趙武術發(fā)展過程中,該地域所擁有的北京和天津就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其中的北京地區(qū),經(jīng)過遼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和清代的京師等皇城沿革,一向是武林高手匯萃、南北流派云集的地方,而宋代以降特別是明清時期,又是中國武術發(fā)展的高度成熟和完善階段,所以,燕趙地域構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武術文化發(fā)展中心。當今廣傳五湖四海的楊式太極拳也是由楊祿禪率先在北京打開了局面,之后,其孫楊澄甫以及眾多弟子等又紛紛南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傳藝,武式太極拳以及孫氏太極拳等也在各大城市得到了積極發(fā)展。顯然,以北京為引領的上述都市的文化輻射作用,在地域武術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齊魯武術文化發(fā)展中的都市傳播效應同樣通過螳螂拳的傳播軌跡得到了展現(xiàn)。螳螂拳產(chǎn)生于清初萊陽一帶,強調象形取意,風格以短打為主,重意于螳螂之勇而不拘泥于螳螂之型,其發(fā)展路線是從農(nóng)村向城市繁衍,先由萊陽、海陽到煙臺、青島市區(qū)傳播,再向濟南、上海、南京等全國重要城市發(fā)展,最后經(jīng)由這些城市流傳到海外。[17]事實上,巴蜀武術分別以成都和重慶為中心形成的川西、川東兩大格局以及嶺南武術以廣州、港、澳為中樞等,同樣也是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中都市傳播效應的客觀例證。
1.6 吳越武風近代先——文化轉型中的地域武術文化發(fā)展特點
任何一種文化,“不管它具有什么樣的‘個性’,它的形成都和它所處的時代相聯(lián)系,都是一定時代的產(chǎn)物”[10]。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之下,地域武術置身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轉型變遷之中,也不能不體現(xiàn)出本能的抗擊與積極的適應,其中,前者以燕趙武術為典型,后者則以吳越武術為引領。
19世紀末期興起于直、魯兩省并最終在京、津達到高潮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極大地震撼了世界,同時也在燕趙武術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義和團運動的產(chǎn)生,顯示了燕趙武術雄厚的群眾基礎和宏大的運動規(guī)模,反映了帝國主義列強和西方天主教肆無忌憚地入侵中國的深刻歷史背景,同時也折射出當時民眾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入侵的無奈、敵視和抗爭。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說,燕趙大地不僅有著深厚的正統(tǒng)文化淵源,同時,也有著濃郁的民間宗教活動等下層傳統(tǒng)文化。因此,以基督教等為代表的西方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的這種文化紛爭,與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民教沖突交織在一直,成為義和團反帝斗爭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一。[20]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沖擊所驅動的現(xiàn)代轉型之際,中國武術文化所具有的精華與糟粕并存、先進與落后共生的傳統(tǒng)特征,在此一覽無余。以燕趙地域為中心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武術在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實戰(zhàn)實踐,伴隨著歷史前行的車輪,中國武術的傳統(tǒng)技擊功能在現(xiàn)代武器的科技威力面前不可避免地顯示出了巨大的反差,同時也啟示著有識之士關于武術文化時代轉型的憂慮與思索。
吳越是近代中華文化轉型的先行地區(qū),上海的中國近代文化前沿地位與民國時期南京的特殊影響,也使得吳越武術應時而動,成為中國地域武術文化近代轉型的先行者。分別成立于上海與南京的精武體育會和中央國術館,作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民間武術組織和政府武術機構,在推動近代武術的普及和發(fā)展方面都起到了引領風氣的作用。在當時排斥西方文化的整體氛圍中,精武體育會在傳統(tǒng)武術實踐的基礎上積極開展近代西方體育項目,并且引進了西方先進科技傳播中國武術。成立于1913年的“精武體育會攝學部”,是中國首家民間攝影組織,其運用現(xiàn)代攝影技術定圖成書,一舉突破了武術舊著述、圖簡略以至仍以口傳面授為主的學習形式,跳出了長期以來武術“因我而傳,無一定軌”的傳統(tǒng)局面[1],堪稱中國武術近代發(fā)展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中央國術館于1928年和1933年舉辦的兩屆國術國考,結合了中國傳統(tǒng)武科考試和西方競技體育競賽模式,對于武術現(xiàn)代化競賽發(fā)展的影響極其深遠;在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的第11屆奧運會上,中央國術館組織的武術代表團向各國觀眾和運動員三萬余人表演了中國武術拳械套路,技驚四座,在奧運舞臺上為中國武術和中華體育贏得了空前的世界榮譽。[17]此外,民國初年就已成為全國出版中心的上海,同時也是武術書籍的重要出版地。據(jù)統(tǒng)計,這一時期在上海成立的主要武術組織就多達45個,作為武術傳播最為成功的太極拳書籍出版的分布地區(qū)計有上海、南京、蘇州、長沙等8省10市,而上海則占領了半壁江山[25]。吳越地域出版的大量武術書籍,推動了近代武術理論的研究和探討,為改變武術界“知之者不能言,能言者不及知”[13]的傳統(tǒng)積弊以及促進武術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等做出了杰出貢獻。
2 中國地域武術文化轉型機制的當代闡釋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伴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變革,面對著西方文化的異域來風,地域武術也開始了內憂外患之下的文化轉型。在以奧林匹克運動為代表的西方體育浪潮強勁沖擊之下,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近代轉型也因此成為一段中西體育全面激蕩、交融的漫漫長征之旅,被動接受和積極求索的矛盾與煎熬貫穿其間,激烈論爭與慨然前行的無奈與勇氣相輔相成,新中國成立以來向奧林匹克運動接軌的競技武術發(fā)展戰(zhàn)略也使得地域武術文化走過了一段不同尋常的發(fā)展歷程。而今,中國地域武術文化又迎來了新一輪的現(xiàn)代轉型思考。
2.1 立足本土,面向時代——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指導思想
時至今日,幾乎與新中國同步的競技武術已經(jīng)走過了一段難忘的發(fā)展歷程,在國際競爭空前激烈的文化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積極融入世界體壇大舞臺。在近代以來的武術文化發(fā)展中,由不同地域組成的中國武術在引進之路上的確有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們至今仍沒能建構出適合自身傳統(tǒng)特征的當代武術發(fā)展格局。由于歷史性地忽略了組成中國武術的不同地域武術個體的特點與差異,由于沒能夠前瞻性地認識到文化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個性的寶貴意義,中國武術的現(xiàn)代轉型之路似乎一度伴生著曲折與迷茫。
21世紀是人類文化大融合的世紀,東西體育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是體育文化發(fā)展的時代趨勢;與之前武術文化轉型最為顯著的不同之處還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建設成果與改革開放30年成功經(jīng)驗共同提升的國際語境賦予了武術作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瑰寶所肩負的民族特色窗口與文化傳播橋梁使命。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是中華武術的生命之本,風格各異的不同地域是地域武術的文化之魂,無論組成中國武術整體的各地域武術文化正在經(jīng)受如何猛烈的現(xiàn)代撞擊,無論中國武術的各地域武術分支正在如何艱難地游離于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因子之間尋找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價值,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必須要能夠旗幟鮮明地彰顯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傳統(tǒng)本原性與當代主體性。因此,充分依托中國武術綿延千年的地域文化傳統(tǒng),在致力地域武術文化傳統(tǒng)當代弘揚的基礎上,積極汲取和借鑒奧林匹克運動等國外體育文化的優(yōu)秀內核與發(fā)展形式,力爭為人類體育文化的交融與進步做出中華民族特有的貢獻,不僅是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武術發(fā)展的宏觀方向。
2.2 見微知著,整合創(chuàng)新——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基本原則
中國武術的博大精深,來源于其內部生成的多姿多彩;武術文化的歷久彌新,取決于其眾多元素通過內容解構和碰撞交融所迸發(fā)的整合創(chuàng)新的強大動力。從燕趙到吳越,從隴右到巴蜀,從三秦到齊魯,從中原到荊楚,五光十色的地域武術文化不僅是中國武術具體而微的真實展示,其承載的地域文化精神同時也為我們解讀和闡釋中國武術的當代發(fā)展提供了技術和文化的雙維座標。見微方始知著,整合才能創(chuàng)新。地域武術文化研究不僅是由微觀層面上揭示中國武術技術與文化內涵的一條重要途徑,針對不同地域武術的挖掘、提煉、整合、創(chuàng)新,對于當代中國武術文化發(fā)展同樣極具戰(zhàn)略意義。
2.3 融入生活,雅俗共賞——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現(xiàn)實路徑
當今時代,科技飛速進步,信息空前發(fā)達,緊張的生活節(jié)奏和嚴峻的生存壓力之下,“通俗性、娛樂性、消費性、平面性的大眾文化日益盛行,并逐漸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27]。文化的轉型語境啟發(fā)著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發(fā)展也應能適應并體現(xiàn)這一特點。地域武術本來就是一種擁有廣泛大眾基礎的民間文化,當代地域武術文化同樣應該一如既往地進入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在傳播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同時,踐行雅俗共賞的現(xiàn)實路徑。這也啟示,在倡導以“高、難、美、新”為特征的現(xiàn)代競技武術戰(zhàn)略的同時,針對國內、外受眾群體特點探索不同地域的大眾武術傳播對策,或許不失為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思路。
2.4 依托地域,發(fā)展產(chǎn)業(yè)——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全新動力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總序》中指出:“區(qū)域文化如同百川歸海,共同匯聚成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這種大傳統(tǒng)如同春風化雨,滲透于各種區(qū)域文化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區(qū)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國文化的共同價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獨特個性支撐著、引領著本地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24]置身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宏觀背景之下,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同樣不能離開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影響與適應。正如學者所言:“在21世紀武術文化發(fā)展的新階段,從文化資源的發(fā)掘到文化資本的形成,從文化資本的形成到文化產(chǎn)業(yè)的實施,其保護與發(fā)展,開發(fā)和利用,是新時期武術文化并行不悖的主題。”[4]
近年來,全國各地紛紛興起了文化旅游之風,地處中原的少林寺與荊楚武術中心武當山等都成為眾多游客的向往之地;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一股傳統(tǒng)武術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熱潮,一些武術之鄉(xiāng),如河南、河北、湖北等紛紛投入巨額資金打造中國傳統(tǒng)武術文化產(chǎn)業(yè)園區(qū),以地域武術門派為亮點的央視武林大會與中國武術職業(yè)聯(lián)賽則更讓人感受到了地域武術文化產(chǎn)業(yè)的震撼前景;而在此之前,不同地域武術的代表拳種依托雄厚資本進入當?shù)馗骷墝W校教育的消息早已此起彼伏。各地域方興未艾的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格局,為地域武術文化轉型提供了創(chuàng)意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顯然,緊密聯(lián)系地域文化發(fā)展最新熱點,在積極服務地域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過程中實現(xiàn)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充滿創(chuàng)意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在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過程中,密切吻合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的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已經(jīng)是一項無法回避的時代課題,而由此衍生的地域武術文化研究與高校、企業(yè)等機構的橫向協(xié)作也將會演化成推動當代地域武術文化轉型的一種全新動力。
3 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當代轉型的戰(zhàn)略要義
時代的進步,賦予了中國地域武術文化全新的發(fā)展背景。從中華民族當代崛起的宏觀視角而言,圍繞中國地域武術文化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當代轉型機制的研究和探索,顯然蘊涵著積極的理論意義和戰(zhàn)略價值。作為承載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歷史產(chǎn)物,不同地域武術的文化特征往往反映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tǒng)元素或主要特點,從而對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與弘揚具有突出作用,地域武術文化蘊含的傳統(tǒng)文化精華則又使其成為當代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
從地域武術文化入手,對中國武術的歷史脈絡與當代發(fā)展進行系統(tǒng)、有序的科學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揚當?shù)氐臍v史傳統(tǒng)和文化資源,繁榮和豐富當代的先進文化建設活動,規(guī)劃和指導未來的文化發(fā)展藍圖,增強文化軟實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輿論力量;另一方面,這也是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fā)展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27]。因此,地域武術文化的科學轉型顯然又是當代中國國家文化戰(zhàn)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從民族根脈和國家語境出發(fā),以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文化發(fā)展為視域,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還無可回避地面對著以下4個維度的戰(zhàn)略要義:為國家軟實力建設奠定基礎;為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提供社會原動力;為創(chuàng)建先進文化提供本土文化價值體系;為復興中華文明提供思想資源與精神創(chuàng)造力。[22]而從這一層面出發(fā),中國地域武術文化的當代轉型顯然則又躍升到了一種明確區(qū)別于以往任何時代的全新境界。
[1]蔡揚武.從精武體育會看東方體育與西方體育的交匯[J].體育文史,1996,(2):7.
[2]晁福林.天玄地黃[M].成都:巴蜀書社,1989:39.
[3]陳振勇,李靜山.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語境下的峨眉地域武術發(fā)展[J].搏擊·武術科學,2009,(9):3-5.
[4]陳振勇.從布迪厄的“文化資本”審視武術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7,33(3):23.
[5]丁麗萍.吳越武術文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7:54,70.
[6]馮天瑜.中華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
[7]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中國武術史[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6:106.
[8]郭守靖.齊魯武術文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7:2,29-43.
[9]郭志禹.東方傳統(tǒng)武術都市化路徑一探[J].搏擊·武術科學,2005,2(3):1.
[10]韓劍琴.“后現(xiàn)代沖擊波”對我國文化轉型的啟示[J].探索與爭鳴,2003,(12):39-41.
[11]韓雪.中州武術文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5:57.
[12]湖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編.湖北武術史[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4:16.
[13]胡兆量.中國文化地理概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59.
[14]李吉遠,郭志禹.地域武術傳承與中國武術國際化傳播斷想——嶺南珠三角武術文化的歷史與現(xiàn)實[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0,44(3):58.
[15]梁啟超.諸子集成·荀子[M].上海:上海書店,1986:180.
[16]林伯原.明代武術發(fā)展狀況初探[J].體育科學,1982,2(3):8.
[17]劉萬春.河北武術[M].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0:226-229.
[18]馬明達.殼子棍研究序[A].蔡智忠.殼子棍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1-8.
[19]梅杭強,邱丕相.武術套路形成根源的人類社會學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5,20(1):33.
[20]彭平一.文化轉型背景下的義和團運動[J].湖南工業(yè)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1):41-43.
[21]申國卿.燕趙武術文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9-43.
[22]唐代興.文化軟實力戰(zhàn)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0.
[23]無谷,劉志學.少林寺資料集[M].西安: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61.
[24]習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總序[EB/OL].易文網(wǎng),2006-11-22.
[25]謝建平.二十世紀太極拳的變遷之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5:66.
[26]徐才.武術學概論[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6:49.
[27]楊向榮,姜文君.傳媒時代的文化轉型與知識分子的角色轉變[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4):93.
[28]張勝利.隴右武術文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2.
[29]趙曄.吳越春秋[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