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近鄉情怯啊!對于一個遠離故鄉的游子,這是一次悲愴的歸來。
他踩著一條坑坑洼洼的泥濘路走著,故鄉的風,把他頭發吹得花白。那是1961年4月,正是農歷陽春三月,一個人經歷了三十六年的漫長別離,第一次回到故鄉,但久違的故鄉卻沒有動人地展示出一個游子記憶中春天的美景,沒有花滿枝頭的山嶺,記憶中的那些大樹連同枝椏上的鳥窠一起被砍光了,屋場上看不到一縷飄起的炊煙,連狗吠聲仿佛也在人間絕跡。沒有蜜蜂,沒有蝴蝶與蜻蜓飛舞,這闃無聲息一片死寂的世界,只有烏鴉飛過時滑落的幾聲凄啼。而他緊閉著嘴唇。如果可以,他也想閉緊自己的眼睛。他也不想看見眼前的這一切,他的目光也在下意識的回避、躲閃著什么。
花明樓,一個美麗的名字,一個美麗的小鎮。這里距毛澤東的故鄉僅有三十多公里。同湘中大山里的韶山沖相比,這里是一片更適合農耕的土地。站在靳江河畔,有一種映入眼簾的清澈,清澈得一眼就能看到,陽光下兩座山峰如同雄獅般的剪影——雙獅嶺。這亙古的蒼山,在蒼翠茂密的叢林里積聚著流水與力量,化作一條清泉奔涌的靳江河。這條河,是湘江的一級支流,是她,把原本丘陵密布的花明樓變成了特別適合水稻生長的灌區。據清同治《寧鄉縣志》載:“昔有齊公,擇此筑樓,課其二字,攻讀其中。”并將其子攻讀詩書的那棟木樓取名“花明樓”。這大約是取盛唐詩人王維“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的詩意,又或是源于宋代詩人陸游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境。六十多年前的一個冬日,一個鄉下人剛把火塘點燃的季節,他就誕生于這里的一戶農家,看這老宅院的規模,該是一戶典型的湘中農家,無疑也是當時農家中的一個大戶人家,一座土木結構的四合院,墻是土墻,瓦是小青瓦。整座院落坐東朝西,背靠青山,樹林與竹林環繞在房子周圍。前面有一口池塘,安湖塘,塘邊是一片面積不小的水田。院子里有大大小小三十多間茅瓦房,除了居室外,還有農具室、豬欄屋、烤火屋,此外還有專門供孩子讀書用的書房。這個規模,要比毛澤東的故居大得多,所以土改時劃成分,毛家是富農,劉家是地主。只是,那時候誰又能知曉,一個偉人連同一個偉大的悲劇,就這樣,在流血的母腹探出了腦袋和手臂。
劉少奇,原名紹選,字渭璜,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稱“九滿”。和毛澤東一樣,盡管出生在比較富裕的農家,但中國鄉村的富裕農家從來都有耕讀傳家的傳統。劉少奇從小就要下田干農活,也要干家務活,這是為了學習種田和長大后管理田莊與家事的本領。另一方面,他還必須勤奮讀書,在土地之外尋找另外一條更寬廣也更渺遠的前途。這孩子從小就酷愛讀書,在炭子沖留下了一個“劉九書柜”的雅號。他從一個書生變成一個激進的青年,是1915年,當他聽到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將自己的名字“渭璜”改為“衛黃”,即誓死捍衛炎黃大地和炎黃子孫!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劉衛黃,這個后來消失了很久的名字將又一次出現在他的骨灰寄存證上。回故鄉這年,劉少奇還不到六十三歲。還有誰,能成為這樣一個最徹底的無產者?歷史,或人生,真是充滿了宿命的味道。
往事散盡,一切只能從直面現實開始。眼前的花明樓炭子沖,他的故里,恍如時光中的焦炭,黑灰色的老瓦依舊陪著飽經風雨洗滌的土墻,還有一個個殘存的土高爐,沒有火焰,只有那把天空涂抹得一團污黑的煙囪,依然聳立著,宛如某種偉大的遺跡。
回故鄉的第二天,劉少奇先在屋場里轉了一圈,看望了一些鄉親。這么多年了,故鄉似乎沒有多大變化,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比以前還苦啊,一個個都瘦骨嶙峋、面有菜色。這還是好的,有的已經渾身浮腫了。一個饑餓的人,從消瘦到浮腫是必將經歷一段長時間挨餓的痛苦折磨,到了浮腫的程度,離餓死就很近了。看著鄉親們那蹣跚著艱難行走的腳步,劉少奇原先那份重返故鄉的久別重逢的心情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痛心疾首的心酸與內疚。他無暇回首往事,也無心去回味久別重逢的心情。而很多老鄉過了幾十年后還記得,六十出頭的少奇同志,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還要蒼老,凌亂的白發下面,是一張瘦削的、充滿了憂慮的臉。他走得越來越慢,兩條腿快要走不動了。
故鄉,對于任何人,都是具有精神意義的。為了聽到人民的聲音,早在1953年夏天,劉少奇就交給他侄孫劉正山(劉少奇大哥的孫子)一個任務,那時劉正山還在人民大學讀書,劉少奇讓他回鄉過暑假時給他找幾個“農民秘書”,把他家鄉的情況,事實上也是中國農村的情況,及時寫信告訴他。這也是他和底層人民之間的一條直達快捷通道。經過反復篩選,炭子沖的成敬常、黃端生、齊海湘和王升平,成了他的四大“農民秘書”。劉少奇在繁忙的國事之中,還擠出時間把這幾個農民專門請到了中南海,聽著他們熟悉的散發著泥土味的鄉音,暢敘闊別之情,臨別時,他又一再叮嚀這些家鄉人,“你們回去了,要經常給我寫信啊!”
從這之后,劉少奇每隔不久都能及時收到來自故鄉的信,他要么親筆回復,要么由鄉間進京的人捎話給他們,沒有一封信沒有回音。中南海和花明樓炭子沖之間的音訊,就這樣彼此傳遞著,一條最底層和最高層之間保持聯系的直接快捷的信息通道,多少年來從未隔絕。而通過這些農民樸實的來信,故鄉和中國農村的真實現狀,在他的腦海里始終是清晰的。然而,從1957年冬天以后,劉少奇突然再也沒有收到故鄉群眾的一封信了。故鄉,也似乎變得霧一樣的朦朧不堪了。
他不知道,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次,劉少奇一回故鄉,就想問問,他那幾個“農民秘書”怎么不給他寫信了?
一問,他才知道,不是這些農民不給他寫信,而是有人不準他們寫。
炭子沖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升平也是他的農民秘書之一,他說,有一回,他們公社書記忽然攔住他,問:“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經常給少奇同志寫信?”王升平說:“是呀,我們是他特邀的農民秘書呀!”公社書記立刻把臉繃緊了,陰沉著臉說:“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決。公社解決不了,也可以向縣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縣官不如現管,幾個農民再也不敢給劉少奇寫信了。到了1958年之后,世界變得讓這幾個農民越來越不可思議,農民秘書之一的成敬常于是又麻著膽子偷偷給劉少奇寫了幾封信,反映鄉里的真實情況,種田搞密植,密得連風也吹不進去,這叫莊稼怎么生長啊?炭子沖的農民想不通,但誰也不敢反對,公社里下了死命令。
然而,這幾封信發出之后,卻沒有一點反應。這讓老成心里打鼓,不知紅墻之內的少奇同志收到了沒有?緊接著,又開始放“衛星”,從畝產幾千斤到畝產幾萬斤,而社員的征購糧也要按照放衛星放出來的數量繳,農民的口糧卻不按吹牛吹出的數字發,發得了嗎?于是,他又一次麻起膽子給劉少奇寫信,問他知不知道下面這些情況。信寄過去了,又是翹首盼著回信,又是在心里打鼓。過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一點反應。在接連發出的幾封信全都如泥牛入海之后,成敬常就心灰意懶了,又過了一段日子,想寫也餓得沒有力氣了。
劉少奇回到故鄉第二天就見到了成敬常,盡管他知道家鄉的父老鄉親都在挨餓,但一眼看到老成,還是讓他吃了一驚,一個壯壯實實的漢子,炭子沖種田的好把式,兩只腳已腫得穿不進鞋子,只能踢啦著一雙舊布鞋,撐著一把木椅子,一步一步地艱難挪動。這還怎能下地耕種啊。
“這是怎么搞的,老成,你怎么餓成了這個樣啊!”老成無力地搖著頭,一雙眼也腫得瞇成了一條縫,聲音嘶啞地說:“我得了水腫病,腳腫了,走不動路。聽說你回來了,我也不能去看你,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腳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了!”少陪了!這話,外人聽不懂,但劉少奇聽得懂,這是他家鄉的土話,少陪了就是快要告別人世了。劉少奇聽了,心里越發不是滋味,他一邊安慰老成,一邊有些奇怪又有些責備地問:“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看到你們的信了。你們的生活這樣困難,為什么不把情況及時告訴我啊?”
此言一出,讓成敬常也感到有些蹊蹺了,“這……怪了啊,我們一直堅持給你寫信呀,可怎么也收不到回信呀……”
劉少奇的眉頭一下擰緊了,他相信老成說的是真話,難道是信沒寄到?丟了?如果只丟失一兩封信還有可能,可劉少奇仔細一打聽!
劉少奇震怒了!很多熟悉少奇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天性隨和寬厚,是很少發脾氣的,但這次,他是真的憤怒了,他當即叫湖南省公安廳查一查,為什么在他的家鄉,群眾寄給他的信件都收不到?這些信到底到哪兒去了?
這事情非同小可,省公安廳立刻派了一位副廳長,開始偵查這件信件失蹤案。很快,情況就查清了,劉少奇這四個“農民秘書”以及別的農民寫給他的信件,都被花明樓公社書記和一位縣里下來掛職的大隊長拿走了。但省公安廳找他們談話時,他們卻不承認,還矢口否認追問過王升平為“屁大的事”向上寫信。但鐵證如山,調查組在縣郵電局查閱了當時的有關記錄,發現這種扣壓群眾信件并非偶然個別現象,幾乎每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有這種情況,而人民群眾鼓起勇氣寫給省里和中央的信件,幾乎全都被當地政府扣押了。
情況搞清楚后,劉少奇在炭子沖召開了干部群眾座談。他看見那個公社書記也在座,劉少奇對他說:“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還想和他們常通信。請你們給我一點通信自由,不要扣壓我的信,好不好?群眾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搗公社、大隊的亂,我是想幫你們的忙。我這個人也可能犯錯誤,幫個倒忙,那我再向你們承認錯誤,作檢討!”他又嚴肅指出:“給中央寫信,不管是好人寫的,還是壞人寫的,中央看看也沒有壞處,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黨員,都有權利向上級黨委告狀,這是憲法、黨章規定了的。”聽說很多農民因為向上面反映情況還挨了批斗,挨了打,劉少奇異常痛心,說:“隨意打人罵人,是違法亂紀行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傷人,都要受到審判,包括我這個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在內。”
成敬常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覺得錯怪了少奇同志,連聲說:“一錯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既是這樣,那以后不寫信了,有什么意見,我們上北京,當面向你報告!”
劉少奇點著頭,說:“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們可以到北京來找我。你們認為需要當面向我反映情況,可以隨時來嘛,住房吃飯我出錢!”
蒼茫大地,風雨泥濘,一個又高又瘦的身影就這樣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奔走著。從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劉少奇先后到了寧鄉、湘潭、長沙三縣的東湖塘、廣福、花明樓三個公社、六個生產隊進行調查研究,歷時四十四天。從大背景看,他這次回故鄉,也是為了響應毛澤東“大興調查之風”的號召。毛澤東說,“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澤東提出“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要看群眾是不是面有菜色,群眾的糧食究竟是很缺,還是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
隨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主要負責人,紛紛開赴農村調查。
一回湘,劉少奇對湖南省委負責同志申明:“這次到鄉下,不住招待所,采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里,鋪禾草,睡門板,不擾民。”
一條條逶迤延伸的鄉間小路,連著村舍,連著田野,卻沒有農家的熱氣騰騰的日子,沒有春天茁壯成長的莊稼。那些日子,他身著藍布衣,腳穿青布鞋,一路步行,先后走訪了首自沖、安湖塘、柘木沖等五個公共食堂。揭開灶上的鍋蓋,看社員吃些什么,鍋里黑糊糊的一團,散發出刺鼻的氣味。這些公共食堂大都沒有隔夜糧,只能靠社員去搞些野菜來充饑。走進社員的住房,掂掂床上的被子,看蓋得薄不薄,被子也是千瘡百孔,想起那些在半夜里常常凍醒的農人,他的心也在一陣陣顫栗。
在長沙縣調查期間,他在廣福公社天華大隊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土磚房里,一住就是十八天。潮濕的春天,許多東西都在霉爛發毛,還有虱子、蟲蟻和從墻縫里爬進來的毒蛇。一個國家主席,住在這樣的土磚房里,為的就是離老百姓更近一點,聽聽干部群眾講真話。但那些公社干部、大隊干部還是一片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我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形勢一片大好,糧食畝產八百斤,跨了《綱要》,群眾生活比過去好多了……”這種背誦式的套話大話,劉少奇一聽就能猜出,這是按某種統一的口徑早就準備好了的,他們什么都準備好了,就是沒有準備好老百姓挨過春荒的糧食。他也沒有過多地責備那些縣、公社和大隊干部。他是一個寬厚的人,也是一個平和的人,作為國家主席,他更多是在內心里反省和自責。
每看見一個饑餓的農人,他就會走過去,下意識地把他擁在懷里,就像摟著自己的兄弟。他最想聽的就是他們的話,老百姓的話。但只要干部們跟著他,老百姓就不敢走近他,站得遠遠的。就是劉少奇主動走近他們,他們也不敢開口講話。一個國家主席,竟要面臨這樣尷尬的選擇,他是跟干部在一起,還是跟老百姓在一起?劉少奇只好把那些陪著自己的干部支開了,他以為這樣老百姓就敢講真話了。但老百姓只是低著頭,抽煙,嘆氣,就是不開口。劉少奇知道,這幾年,凡是說過真話的人,都被打怕了。在沉默片刻之后,他慢慢摘下帽子,露出滿頭花白的頭發,一次又一次對著老百姓俯下身,低下頭,他在給老鄉們鞠躬,給老鄉們真誠地道歉。看著一個國家主席一次一次地低頭,認錯,老百姓這才相信,中央這次是下了決心,要整頓了,要動真格了,他們這才開始吞吞吐吐地講真話。他們壓低聲音告訴國家主席,現在幾乎家家都沒飯吃,田里荒了,不是農民懶,餓得實在沒有力氣勞動了。一個老貧農麻著膽子說:“有人說我們公社的糧食畝產八百斤,把禾稈子加在一起稱也不夠哩,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來湊數!滿打滿算,一畝田搞不過兩三百斤,還是谷子,但干部都逼著我們說瞎話,這樣他們就可以提拔當官。”有膽大的,還試探著問他:“劉主席,現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們種田人沒飯吃,那不種地的人還不都要餓死?”
這話,讓劉少奇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他感到,講真話有多難啊,要了解真實情況又有多難啊,農村的嚴峻現實,絕不是一天兩天就能看清楚的,他知道,在這饑荒歲月,城里人的日子也過得緊緊巴巴,但多少還有糧食配給,城里人雖說也有患上了浮腫病的,但沒有鄉下人這樣普遍,更沒有發生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劉少奇在一間土磚房里住了十八天,也走鄉串戶地奔走了十八天,走到哪里記到哪里,記滿了好幾個筆記本,這才把這里的糧食問題、公共食堂問題、分配問題、山林問題大致了解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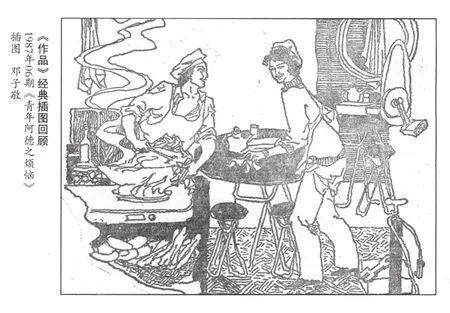
劉少奇在另一個公社考察時,那里還是個先進公社,聽說劉主席來了,數十個衣衫襤褸、拖兒帶女的老百姓跪在路旁,地上擺著一長溜空蕩蕩的飯碗,他們大聲哭喊著:“劉主席呀,我們沒有飯吃,快餓死啦,請求政府救救我們啊!”
幾位老人捧上手中的糠菜,“劉主席,你嘗嘗我們吃的是什么?”
劉少奇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摻雜著野菜的滋味又澀又苦,他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后來才知道,老百姓能吃上這樣的東西,還是當地干部知道他要回鄉,事先撥了幾千斤谷子給公社食堂。
隨著逐漸深入的調查,那些干部不得不承認群眾生活“有一定的困難”,但他們又把這一切歸咎于這些農民瞞產私分。劉少奇想,如果真是農民瞞產私分了,倒也好啊,可他們瞞產私分的糧食到哪里去了?在舊社會,老百姓有把糧食藏起來的習慣,但那是怕糧食被兵匪奪去。可現在,難道他們快要餓死了還把糧食埋在地底下?
在農人們的一片哀怨聲中,劉少奇先在東湖塘人民公社王家灣生產隊一破舊屋子住了五天。當地干部想把他安排在好一點的地方住,他說,老百姓能住,我為什么不能住?快到吃晚飯時,他聽說公社還特意為他準備了一桌酒菜。他一聽,氣就不打一處來,“老百姓吃糠咽菜,卻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嗎?”他要他們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下了米飯和一碗青菜。
一天,途經雙鳧鋪人民公社黑塘侖,灰蒙蒙的天邊,眼看就要下雨了,劉少奇看見路旁一所茅屋前有一個頭發花白、瘦骨嶙峋的婦女拉著幾個小孩在哭泣。怎么回事?他一愣,趕快走了過去。那婦女看見是個干部模樣的人走來了,她撲通一下跪在了劉少奇的跟前,抱住他的腿泣不成聲。劉少奇趕忙用雙手把她扶起來,一看,這婦女看上去年歲并不大,頭發卻已經花白了。他一邊扶著她一邊安慰這婦女:“大嫂,你不能這樣,我擔待不起呀,你有話慢慢說。”聽了那婦女的訴說,他才知道,這婦女叫顏桂英,搞了三年大躍進,她三年搬了八次家,不久前他丈夫死了,說是病死的,實際是餓死的,她一個寡婦現在要獨自撫養三個小孩,原來家里土改時分的房屋被拆掉了,現住幾間茅屋,又不讓她和伢崽們住了,孤兒寡母眼看著就要無處安身,喊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
“家搬三次窮啊,何況她搬了八次家呢!”劉少奇心酸不已,一打聽,像這個婦女一樣的困難戶還有很多。那時候,很多農民的房子,都在大躍進中被拆掉了,有的拆掉蓋了公共食堂,有的被填進土高爐里煉了鋼。但現在不是追究原因的時候,必須趕緊讓老百姓住進房子里。很快,他就把當地干部找來了,一是暫時不讓那個婦女搬家,二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住房困難戶的情況摸清底細,由公社和大隊馬上統籌解決,不能等了!他一連聲地馬上,一連聲的不能等了,老百姓沒房住,他急啊。當天晚上,他又馬不停蹄地趕到縣城,親自找縣委書記、縣長研究解決農民群眾的住房困難。他要求寧鄉縣委立即研究起草一個《關于解決當前社員住房的意見》。凌晨兩點,一個國家主席,還在對一個縣級文件逐字逐句審閱、修改,親自寫了批語。他要求縣委把文件馬上發下去。湖南省委也很快將這個文件轉發全省,這對解決當時農村無房戶的困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對那些縣里和公社的干部們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人民的吃穿住問題,人民受了這么多苦,我們要為他們分憂解愁呵!不然要我們共產黨人干什么!”這是最樸素的真理,老百姓不可一日無糧,更不可一日無房啊。他還提出停止他的故居對外開放,分給社員住。他看到群眾有顧慮不愿搬進來時,便親自點了幾戶社員的名,叫他們馬上搬進去住。他說,不要擔心有人來參觀,我看外國人不讓他來,中國人來沒問題,每人招待兩碗開水。要給錢也可以收。他還說,不但房子要分給社員住,就是這里陳列展出的桌子、凳子、鍋子、爐灶,一切家具什物,都要作為退賠,退給社員,樓板可給社員作門窗用。他還特別囑咐將要住進去的社員:“你們在這里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們有了房子,比這個房子好,愿意搬再搬。”
回到故鄉花明樓炭子沖后,劉少奇夫婦就一直住在炭子沖舊居。
去炭子沖劉少奇故居參觀過的人,應該都看見過那幢風雨滄桑的老屋,老屋里的那間土坯房,那間老式木架子床。整個世界,或許只有中國的國家元首還能躺在這樣的房間了,這樣簡陋的一張床上,安詳地入眠。這是平常事,但要平常心。一個身居高位的人,如果沒有只屬于共產黨人的那種堅定信念,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真的,很難。如果仔細看,這床頭還能依稀看到時間沒有磨滅的一些字跡,那是他在十八歲的生日到來時,在床頭刻下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那些日子,他不是到社員家走訪,就是請鄉親們到他的舊居里來談心,他的大門每天都是敞開的,一直敞開到深夜。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農民,他親自給每個來訪的老鄉沏茶,敬煙,他也愛抽煙,陪著老鄉們一根一根地抽,吸著煙,吐著煙,心里卻在運思一個大國的現實與未來。夜深了,他家里仍然是七嘴八舌的一片說話聲。既然國家主席愛聽大實話,許多老百姓積郁在胸中多時、想講又不敢講的話,就會源源不斷地傾吐出來,那樣的真摯,那樣的熱烈,也充滿了抱怨。
有的老百姓直說,“農村搞成這個樣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還有的說:“劉主席啊,再這樣搞下去,就會弄得路死人絕,到時候恐怕連抬死尸的人都會找不到啊。”這話,越說越刺耳了,但劉少奇知道這是真話,共和國主席又一次謙卑地低下了頭,連聲說,“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鄉親們受苦了,我這次回來就是向鄉親們檢查錯誤的。”
他又找來他的農民秘書之一王升平。這位炭子沖黨支部書記,難免也有頭腦發熱的時候。
劉少奇問他:“你為什么會犯‘五風’錯誤?”
王升平說:“沒有聽黨和毛主席的話。”
劉少奇搖著頭,看著他,他的眼神是平和的,但有一種說不出的光芒,“我看哪,歸根結底還是沒有聽群眾的話,如果真正聽了群眾的話,就不會犯‘五風’錯誤。因此,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
王升平聽了,低頭不語了。這話意味深長,也讓一個農民似乎感覺到了什么。是什么呢?他正在尋思,劉少奇又問他對公共食堂的看法,這是王升平一開始也不敢講實話的,他知道這話的嚴重性。但見少奇同志問得真切,他才大膽地說:“公共食堂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的,只怕有人插田,無人過年啊。”農民一旦開口說話,就是巷子里趕豬——直來直去,這話聽著可怕,但很真實。
劉少奇說:“那好,你先把你那個食堂解散。”
但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不敢解散公共食堂的,還是那句老話,縣官不如現管。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得先征得寧鄉縣委同意后,才決定先解散柘木沖食堂。一個食堂解散了,就絕不止一個食堂被解散,那種如洪水決堤般的力量勢不可擋,幾乎在頃刻間,炭子沖的食堂解散了,花明樓的食堂解散了,全縣所有公共食堂都解散了。
就在柘木沖食堂解散的第二天,劉少奇又深入社員家中走訪,他看到農家的鐵鍋早已煉了鋼鐵,壇壇罐罐也早已打碎,趕緊讓當地政府部門組織生產老百姓急需的鍋碗瓢盆,來彌補農人殘缺不全的生活。為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同寧鄉縣委一起研究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他說,這幾年生產之所以出現了大倒退,糧食出現了大減產,一是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傷害了農業這個基礎;二是大辦農業中搞亂了體制,破壞了生產關系,挫傷了群眾積極性,最主要的是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違背了人民的心愿——要刻石立碑,子子孫孫不要再刮‘五風’了!
在炭子沖大隊干部社員座談會上,他再次重申和強調了人民的主體性,中國農民精耕細作數千年,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農耕經驗,如密植、插雙季稻、種棉花、修公路等,公社、大隊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沒有權作決定,要讓人民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一切都要經過社員大會(或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干部是社員的勤務員,不是社員的老子,應該好好為社員辦事。停了,他還再三囑咐父老鄉親:“這里是我的故鄉,省、縣、公社都有照顧,照顧多了不好,沒有照顧也可以搞好嘛!主要靠自己努力,事情就可以搞好,千萬不能用我的名義要求別人照顧。這里還有我的親屬,不要因為我的關系特別照顧他們。”
這四十四天,劉少奇還糾正了一些錯案。那時,花明樓小學有個五年級的小學生,在電線桿上寫了一句“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被定性為“書寫反革命標語罪”,這孩子所在學校的校長和班主任也被撤職查辦。當劉少奇聽說并且過問這件事時,氣氛一下變得高度緊張。但劉少奇不是要追究這件事,而是要當地有關部門立即撤銷這件案子,放了那孩子。他深知,這幾年的窮折騰瞎折騰,讓老百姓深受其害,一個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只是挨了餓,難免發點小小的牢騷,這不算什么,也不能怪他,更不能連累他的校長和班主任。當然,作為政治家的劉少奇,也沒有把這看作一個孤立的個案,他在向人們展現執政黨的一種寬容姿態,營造出一種寬松的政治氣氛。
劉少奇這次回故鄉,可以說是他清理自己的思路,并在第一線開始經濟調整的開始。四十四天的奔走,四十四天的傾聽,四十四天的沉思,共和國主席的心思,多少次沉下去,又多少次浮起來。而對即將開始的經濟調整,尤其是農村如何調整,他心里,已經醞釀成熟。這次調查,也為中央《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及時出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寧鄉花明樓的經濟調整,也就是后來的中國經驗。
就從這里開始吧,他的決心已經下定。臨走時,他對家鄉的干部說,要穩定體制,土地、勞力、耕牛、農具要固定到隊,保證生產的所有權和自主權,不得任意平調。要給社員一點“小自由”,發展家庭副業。田塍、荒山可以包產到戶,一些空坪隙地,可以分給社員種作物,房前屋后可以讓社員種樹。以后大家養豬有肉吃,養雞有蛋吃。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不要搞供給制。除五保戶必須照顧外,其余都要按勞分配。手工業工人的待遇要提高一些,如果是一拉平,誰還去學手藝?
在他漸行漸遠的身影背后,畢竟是春天了,漫山的杜鵑花開了,還有杜鵑催人播種的叫喚聲,在遠山中悠遠地回蕩著,布谷,布——谷——故鄉的農人又開始忙碌起來,水田里的禾苗正節節拔高,屋場里的豬糞,牛糞,漚出來的氣味,一陣一陣的,和著炊煙,濃濃地彌漫著。這是鄉村的氣味和鄉土的氣味,也是一個村莊開始走向正常生活的重新開始。只是眼前這條艱險的、充滿了無限玄機的路,他認準了,但不知道他能走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