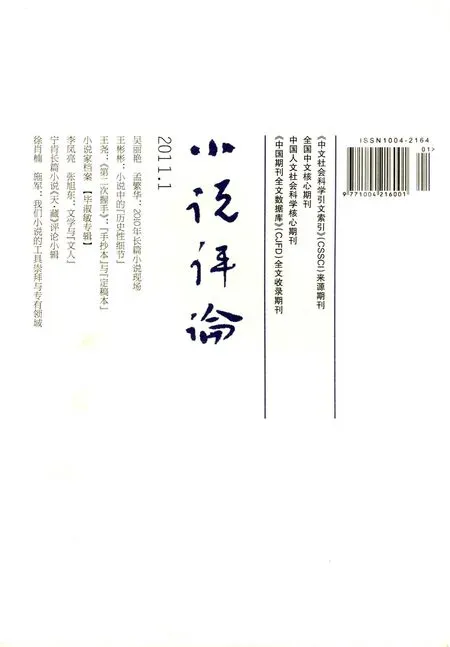挽歌的困境
——論田耳的《夏天糖》①
龐秀慧
挽歌的困境
——論田耳的《夏天糖》①
龐秀慧
曾經是短篇小說的《夏天糖》經過田耳的改寫后,作品的精神意蘊徹底發生了變化:如果說短篇小說《夏天糖》僅僅是一個故事的話,那么長篇小說《夏天糖》就是由故事而升華的一曲挽歌,用作者田耳的話來說,《夏天糖》不但要寫“十年間,從農村到城市變化的過程”,“也想關注一個問題。進入城市后,能不能融入,漂移的狀態,無路可走。”②在這個小說中,文學佴城再次成為故事發生地,但是這一次文學佴城不再是孤立的城鎮,它的成長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佴城人身上也就折射出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特征,而《夏天糖》的成就與困境在某種程度上,和這些特征息息相關。
一
在短篇小說中已經敘述過的司機與小女孩的故事依舊是《夏天糖》的敘述重點,但是作品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者,通過“我”的成長以及活動,串聯起佴城與莞城的歷史與現狀,呈現出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佴城以及莞城的歷史,另一方面是“我”和司機江標等人當下的生活。
從第一個層面來看,小說所展現的不再是一個鄉下人進城的過程,而是人和城市一起脫胎換骨,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步成長。出身農村的母親和舅舅的奮斗歷程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記憶。在田耳筆下,身為知識分子的父親顧豐年和岳父范醫生庸庸碌碌,一事無成:清高的父親一輩子最拿手的事是養蟋蟀打架;逍遙的范醫生總是坐在書桌前寫文章,卻總不見有任何成果。只有母親潑辣能干,勇往無前,以前干個體戶,剝過蛇,到福建販過水貨,現在開餐館搞建材公司承包建筑工程,甚至還在佴城境內修過長城,成為佴城的重要旅游景點。“我”和小伙伴滌青、滌生參與了母親的創業,幾個小孩子幫母親送VHS盒帶,一起翻錄磁帶。在這個過程中,比“我”大四歲的滌青成為“我”最深刻的依戀,是“所有懷舊的華章部分”,這是“我”與滌青的情感起點。而且母親的生命力極其頑強,面對經濟環境的變故所導致的投資失敗,她以退為進,終于東山再起;同樣面對生活的打擊,父親卻從此一蹶不振。
母親的歷史,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鄉村,更值得重視的是連接著城市和農村的鄉鎮。城市文明通過鄉鎮影響農村,與此同時鄉鎮又是農民進城的首選落腳點,鄉鎮實際上成為鄉土社會感受城市文明的第一站,而且鄉鎮對城市文明的看法與感受又會直接影響到鄉村,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鄉鎮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道非常值得研究的景觀。在《夏天糖》中,母親通過在大城市和佴城之間倒賣水貨而發家致富;莞城的發展使得城、鎮、鄉、村聯系到了一起,連小小的佴城都有了自己的飛機場。鄉土社會由一個純粹經驗性的地域變成了一個高度變化的、充滿了理性抉擇的空間,人無意中成了歷史的創造者和參與者,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鄉鎮的變化中,例如母親疏通關系把我安排在群藝館上班;江標的舅舅把江標一家從鄉村帶到了城市,“我”和“江標”對這種安排既欣喜又莫名其妙,不知道母親和舅舅為何這么神通廣大。從黎照里的名言“人總是要發展的,不發展也要讓別人以為你在發展……要不然賺的錢不夠彌補你心頭的失敗感”里,我們多少能感受出來人們的盲目和急迫。
然而歷史在前進,但是價值理念未必能順應歷史的腳步,正如馬泰·卡林內斯庫所說“歷史(記憶)被表明是生活(自發行動)無法化解的仇敵。”③現代化的過程使得凝固化的鄉土社會變得渙散,一切曾經深深依戀過的,自以為堅固無比的東西從此煙消云散。個體和城市一起成長,可成長之后的城市卻不是和所有個體都繼續維系原有的關聯。《夏天糖》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者就預示了這個事實。“我”始終是母親生活的旁觀者,對時代浪潮不過是被動地應和,從來沒有進入母親生活的內在,體會母親和大時代的精神主旨。當母親和父親離婚之后,大時代留給“我”的只剩下了與滌青的感情,而真正吸引“我”的卻是江標所代表的當下生活。
這就是《夏天糖》的第二個敘述層面,江標代表著另外一種生活,他嚴肅認真,如同堂吉訶德對抗風車一樣對抗著高速發展的社會。從思維上來看,江標顯然是農業文明的產物:他留戀在鄉村土路上跑車的生活,缺乏對經濟的敏感,始終維持手工制作球形薄荷糖的興趣,全部激情都維系在當年那個躺在馬路上的小女孩身上;對城市文明的理解僅僅是“城里人誰都不愿當孫子”,為了甩掉字輩,就另取個單名。為了維持鄉土記憶,他不斷追尋著鈴蘭的蹤跡,不顧家庭經濟現狀,資助鈴蘭離開佴城。“我”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個新潮人物:攝影師,時尚,有品位,還鼓勵離異的父親重組家庭,愛人滌青又是頗有影響的地下電影導演。但實際上“我”和江標分享著同一精神世界,“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拒絕著快速發展的現代工業文明和動蕩不安的精神狀態。作為第一批闖蕩莞城的人,雖然四處都有發財的機會,“我”卻缺乏致富動力,天天睡到自然醒,再“掙得足吃飯住宿的錢”就心滿意足了,所以他和江標一見如故,同樣迷戀著小女孩所代表的往事記憶。
當個體被懷念縈繞,很容易呈現出頹廢哀婉的情緒,雖然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認為頹廢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但是當鄉鎮剛剛和城市接軌,初步進入現代工業文明時,這種頹廢實則就是在否定高速發展的現代文化,特別是這種情緒再和以江標為代表的農業文明糾纏在一起之后,城市的面貌就變得模糊不清。所以在《夏天糖》中我們很難找到現代化城市的特征,沒有現代工業文明的氣息,在“我”的生活中,只有滌青是努力向上,奮斗不息的人。但是滌青卻是“我”有意無意貶低的對象:滌青在外多年,飲食和服飾都發生了變化,甚至連佴城的俗諺都聽不懂了;當“我”與鈴蘭偷情時,滌青身上那種由現代文化熏陶出來的“氣場”竟然是“我”與之背離的原因;只有回到父親的舊房子里時,“我”才被喚起一種同滌青相濡以沫的感情。對往事的懷念成為不斷循環往復的主旋律,現實生活中的人要么隨波逐流,要么就被卷入對往事的隨想之中,特別是當滌青因為懷有身孕不得不屈就“我”的生活狀態之后,人物情感指向一致往后,共同緬懷逝去的時間。這其實是一種希望現實固定不變的愿望,非常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敗感。因為在現代生活中,“現實性之顯于我們面前就是歷史性。永恒的現實不可被當作一種無時間的持續的他物,補課被當作一種在時間里常駐不變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現實毋寧是一個過渡。它取得實際存在,而它作為實存又將立即重新離開它的實際存在。它所取得的形態,不是持續,也不是固定不變,而是挫敗。”④這種挫敗體現在很多人身上:滌青放棄了自己的理想重返佴城;鈴蘭見識了莞城之后,覺得自己是泥巴命,城市生活和她無關,又回到了江洋大道作妓女;江標費盡心機維護鈴蘭的純潔,但最終失望,特別是他強迫鈴蘭身穿綠衣,躺在馬路上,試圖重現往事,陡然發現今非昔比,頓生殺機。而這場屠殺在作者筆下,顯得極其唯美,鈴蘭的血是淡綠色的汁液,充滿了“清涼溫潤的氣味”,這是對往事的最終悼念,表現出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的悲哀。
二
總體而言,“無路可走”的挽歌是作品的核心思想,寫出了轉型期的鄉鎮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它又暴露出作品本身的局限和困境。挽歌有多種,有的是悼念逝去的鄉土,如賈平凹的《秦腔》;有的是表達贊美之情,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但是《夏天糖》的挽歌中充滿了抗爭的意蘊。這種抗爭不但表現為“我”在現代文明面前的頹廢態度,更是以江標和鈴蘭的故事為寓言來反抗快速變動的現代社會。由此,它又不單純是反抗城市化帶給人的精神困境,而是混雜著以歷史對抗現實的意味,既不是海德格爾的“詩意的棲居”,也不是費瑟斯通的“刻意的鄉愁’(willful nostalgia)”⑤,而是一種由于缺乏了解和認同而導致的對抗,極大地限制了作品的精神境界。李敬澤曾經說過:“田耳的小說中,在參差差異的主題、經驗和語調之間,貫穿著一種眼光——不是觀點,也不是視角,而是復雜、含混的態度,是本能的、逐漸發展和塑造起來的興趣。”⑥這種態度源自于作者久居鳳凰小城,活動空間有限,對城市生活缺乏具體而微的感受。他對大城市人的中心意識很敏感,但無法體會大城市所代表的工業文明,所以在他眼中所有的城市和鳳凰都很接近。⑦這種對城市文明缺乏認知而導致的平庸境界突出表現在鈴蘭對莞城的認識上:鈴蘭無法想象大城市的超市“比佴城所有的店子加在一起還大”,所以初到莞城時,極其興奮,覺得自己無知是因為生活給她的機會太少,“我要努力,有趣的東西都學一學,有沒有用是另一回事”。這是鄉下人進城敘事中最關鍵的要素:農民在進入城市之后,深感以往的封閉和落后,愿意改變自己以適應城市,鈴蘭希望未來可以是“有很大一套復式樓,還有車,賺錢很多”;但是“我”干擾了鈴蘭對生活的設想。“我”在莞城的生活狀況是很窘迫的,租住的屋子和紙盒子一樣,可“我”還以居家為樂,以至于連鈴蘭都開始詢問“我”的理想。可見“我”始終沒有進入城市的內在空間,對城市精神的感受都是間接的,是源于母親和滌青,“我”無法真正體會到城市文明的內涵。最后鈴蘭因為對“我”的情感依賴無法自立,最終回到了佴城。鄉鎮最終還是不能順應現代化的潮流逐步靠攏城市文明,依舊無法擺脫農業文明的魅影。
或許這就預示了當下中國鄉土小說的宿命,它將不得不和作家們一起去適應現代化城市的逐漸生成和成長,鄉土作家和鄉土小說息息相關,“精神的存在,決定著文學的形態、結構和品質。”⑧目前鄉土作家們最欠缺的地方是無法以歷史的眼光去把握城市作為工業文明的產物所蘊含的精神實質,作家們往往著力描述農民在城市的焦慮和墮落,卻很少能確切地描繪出城市提供給人的特有空間,并由此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其實空間本身并不單純是一個物質性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一樣,“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⑨鄉土小說中對城市的描寫有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有高樓和公交車,還有農民工在城市的狹小住所等,但是很少有人能深入其中,描寫全球化對農民生活空間的影響。其實在現代文學中,對城市空間的描繪比比皆是:茅盾在《子夜》里寫城市的燈紅酒綠,寫股票交易所,寫資本家們周圍的各色人群;新感覺派對上海生活的全方位描述;還有張愛玲作品中多次出現的陽臺。但是在當下的鄉土小說中,我們很少能看到農民在這些都市空間中活動,即便農民不斷游走于城鄉之間,感受到了城市生活帶給他們的焦慮與孤獨、失落與茫然,甚至于頹廢與荒誕。但是他們的空間依舊是狹小的,因此無論鄉土文學怎么關注人的生活,也無法超越前人。姑且不說精神境界的差異,單從描寫內容上來說,當下的鄉土作家根本無法像巴爾扎克寫人間喜劇一樣,無法寫出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新空間,更談不上探索農民在城市的歷史發展趨勢。
田耳也是如此,所以《夏天糖》中的佴城雖然曾經積極投入時代的洪流中,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佴城和莞城的差異越來越大,鄉鎮根本沒有能力承擔起傳播現代化文明的重任,反而被靜穆的農業文化所吞噬。由此鈴蘭與“我”的隨波逐流和順其自然,滌青的瀟灑與執拗都有一種空虛無助的味道;“我”雖然對現況不滿,可抗爭的方式卻不是了解城市文明,并努力融入其中,而是沉溺于對往事的不斷追憶,因此才會無限向往江標的故事,表現出一種價值判斷的迷茫。整個小說沒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再三宣揚的時代精神,卻充斥著大時代變遷中的被動承受者,也就是說以江標所代表的失去精神家園的人群占據了小說的中心,滾滾而來的時代巨輪碾碎了他們的夢想,他們能做的是以一種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勇氣去與這個時代做個告別。當然,這種告別是慘重的,對于滌青來說,她放棄了她一向的理念,屈就“我”所代表的頹廢生活;對于江標來說,他以殺害鈴蘭的方式,對于變動中的現實做出了最為強烈的抗議。但是我們不得不問,難道鄉土文學也要以抗爭的方式來對待逐漸逼近我們的現代文明么?
本文系2010年度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江蘇歷史題材文學作品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0ZWD017。
龐秀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
注釋:
①《夏天糖》本是作家田耳發表在2006年第十一期臺灣《聯合文學》并獲得第二十屆臺灣聯合文學新人獎的一個短篇小說,但是田耳經過長期沉淀后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改寫,這就是發表在《鐘山》2011年第一期的長篇小說《夏天糖》。本文中《夏天糖》除非特指,皆是田耳的長篇新作。
②劉燕:《田耳:底層是個討巧的概念》,《東莞日報》2009年5月31日。
③〔美〕馬泰·卡林內斯庫著:《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57頁。
④〔德〕卡爾·雅斯貝斯著:《生存哲學》,王玖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⑤周憲,《全球化與文化認同》,引自《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同》,周憲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頁。
⑥李敬澤:《靈驗的講述:世界重獲魅力——田耳論》,《小說評論》2008年第5期。
⑦田耳、張昭兵:《田耳:語言是人最難以掩飾的個性》,《青春》2009年第7期。
⑧林賢治:《中國作家精神還鄉的歷史流變》,《揚子江評論》2008年第2期。
⑨亨利·列斐伏爾著:《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王志弘譯,引自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