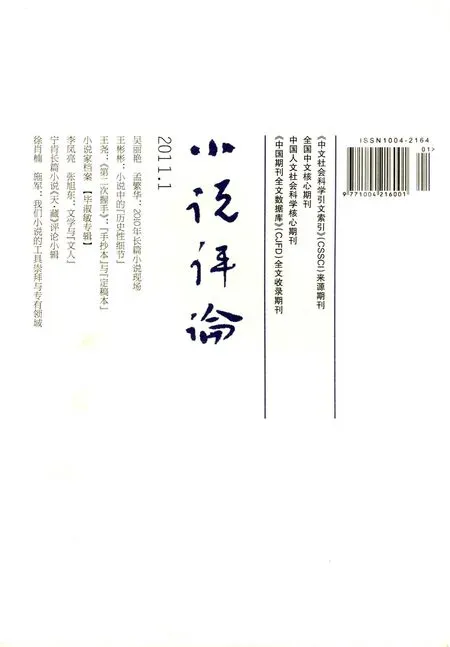西部敘事的古典意蘊與現代追求
——評王新軍長篇小說《最后一個窮人》兼及其他
王明博
西部敘事的古典意蘊與現代追求
——評王新軍長篇小說《最后一個窮人》兼及其他
王明博
西部是一個地域概念,不同時期地域劃分雖然不同,但表現在文學上的美學風格卻大體一致,大氣、清新、粗獷、浪漫,古道西風的蒼涼。在當代文學的書寫中,西部代表了封閉、落后、陳舊,西部敘事的特征表現為苦難、底層關懷、厚重、史詩品格,甘肅作家的創作就有較集中的體現。在邵振國的《麥客》中,可以看到吳河東父子在欲望和道德撕咬中的痛苦掙扎;在牛正寰的《風雪茫茫》中,可以聽到活的渴求與人的尊嚴的兩難處境中西部女性的滴血呻吟;在雷建政的《西北黑人》中,可以感受到麻哥和尕五舍棄以命相搏的戶口證明時的慘烈悲壯;在張存學的筆下,可以觸摸到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永遠也走不出的貧困和愚昧。還有閻強國的《紅色的云霧》《女人秋》,雪漠的《大漠祭》《白虎關》,柏原的《喊會》《背耳子看山》等,無不表現了西北偏僻山村農民生活的沉重與苦難。這些作品往往給人一種逼仄、壓抑、沉郁的感受,而王新軍的小說卻是耳目一新,如沐清風。同樣反映的也是西部農民的生活常態,王新軍一改當下甘肅小說慣常的沉重風氣,用溫婉的筆調、詩意的語言,抒寫鄉村生活,展現底層命運。王新軍有意淡化了那種令人唏噓、令人扼腕的苦情,用看似輕松的調侃、灰色幽默式的筆觸,既寫出了鄉村的純樸、寧靜與詩意,又寫出了封閉、落后和荒涼,在給人以清純、自然感的同時,也給予了人們現代城市文化參照下的憂郁與悵惘。他筆下的苦難是耐人回味的,能勾起讀者記憶中的苦澀憂傷,他能把這種苦難“內轉”——也即讀他的小說,不是從故事情節中接受那些苦難,而是在他故意的輕松中,喚起讀者善意的悲憫,涌起一股股生活熱情,心中充滿了關愛,充滿了扎入泥土的踏實的收獲感和對純凈生活的向往。王新軍不刻意描寫人物在苦難中的呻吟與掙扎,不刻意將讀者挽留在人物的辛酸中,而是把窮鄉僻壤的饑饉病痛作為讀者偶爾經過的一條小河,用它的溫涼與清澈洗滌著行路人的腳踝,讓人生的腳步停下來,體味人性的美好和道德的善良。
王新軍被稱為“甘肅八駿”之首,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以來,先后有長、中、短篇小說百余部(篇)作品發表,作品曾獲第六屆上海中長篇小說優秀作品獎,第一屆、第二屆黃河文學獎中、短篇小說一、二等獎,第四屆、第五屆敦煌文藝獎等。由敦煌文藝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的《最后一個窮人》,是王新軍歷時八年精心創作的長篇小說,這部力作可以說是王新軍鄉村敘述的一個突破,他自己曾坦言:“我曾經熱衷于精確地表達自己朦朧的心情,但后來還是迷戀上了敘事的長度和難度,我一直盼望寫出與前一部不同的小說來。”①
《最后一個窮人》延續了他在“大地上的村莊”系列的美學風格。“大地上的村莊”系列是以他的短篇小說《大地上的村莊》命名的。這一系列的小說有《大地上的村莊》《村莊的開始》《閑話沙洼洼》《吹過村莊的風》《與村莊有關的一頭牛》《農民老木》《七彩山雞》《大草灘》《八個家》等,作品以疏勒河周邊的農村為背景,虛擬了一個“沙洼洼”的村莊(其中有的作品并非寫這個村莊,但是作品的主題和風格都大致相似),以村莊和“與村莊有關的”事物(牛、狗、風等)為主體,敘寫了新時期以來,時代變遷過程中西北偏僻農村農民的生存狀態,以及城鎮化經濟對農村的擠兌,農民生活方式、心理結構發生變化的矛盾和焦慮。作品不是以寫實的筆觸刻畫這種苦焦的生活,而是以小寫意的手筆寫出了經濟大潮沖擊下,傳統農村所保留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對其小說的審美特征,李建軍的評論是極為到位的:“王新軍的小說有喬治·桑的溫暖的愛意,有汪曾棋小說中的濃厚的人情味,樸實中富含著詩意,平靜中包蘊著熱烈,將愛情及其他形式的倫理親情,表現得感人至深,別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倫理內容和道德力量。”②這種濃厚的人情味和感人至深的倫理道德,在《最后一個窮人》中表現的更突出。《大草灘》中的許三管,《羊之惑》中的玉根老人,《農民》中的李玉山等都是普普通通的農民,而《最后一個窮人》中的馬三多卻是普通農民中的下層。他的父親是個瞎子,他18歲了才讀到三年級,還寫不上一個“手”字,正是這樣一個“頭腦像五月的綠麥子”一樣的主人公,才去收養一個又一個被人拋棄的女嬰,才去一次又一次拯救被宗法社會道德戕害的女人。他的至真至善在于這一系列的行為源自一個人,一個沒有受社會規訓的人的心底的善良。
《最后一個窮人》的美學特征還在于作品“最后”文學類型的選擇上。新時期以來以“最后”命名的較多,形成了文學中“最后”現象。典型的有《最后一個漁佬兒》《最后一個匈奴》《最后那個父親》等。這一類作品在在審美特色上都有一種“若有所失”的淡淡的憂傷情懷。李繼凱教授在談到“最后”現象時指出:“從作家涉寫‘最后’現象所體現出的情感態度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側重于歌項、贊美的,即致力于開掘或發現‘最后’現象中寶貴的東西;其二是側重于揭露、批判的,即致力于剝露和剖析‘最后’現象中落后的東西或腐朽的東西;其三是側重于調合、靜觀的,即對‘最后’現象采取的是通達的多維視角,冷靜客觀地、全面地觀照,其情感態度也最復雜、最隱微。”③我認為《最后一個窮人》屬于第三種情形,作者的情感是復雜的,馬三多這個在商品經濟主導下的最后一個窮人,他身上所呈現出的這種淳樸道德日益在喪失,作者的“最后”情結正是對這溫情傳統道德異化所唱的挽歌,又是對不能與時俱進被社會所淘汰農民的一種詠嘆。從理智上講,這種傳統生產、生活方式下的傳統精神,傳統性格應該被淘汰,但情感上又覺得是美好的、溫馨的。作品超出了表層悲劇故事的呈示和淺薄的哀憐悲憫,超出了由一般的心理痛苦轉化的審美快適,具有相當的審美深度。
《最后一個窮人》不同于“大地上的村莊”系列小說,關鍵在于現代性追求上,也即先鋒性的探索上。首先,重復的充分運用是最鮮明的特點。米勒指出:“不管是什么樣的讀者,對小說這樣的長篇作品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對重復以及因重復而產生意義的識別來達到理解的。”④。米勒所提出的重復并非簡單的故事內容的重復,而是通過重復表現一種深層意義。具體說,小說的深層結構經歷了一種“圈”的形式,一個主體與回歸的循環往復。其關鍵是透露出的一種為生存而抗爭的動力。現代小說中的事件重復通常是主題的意義增殖過程——文本的情感、意義得以積累并進而抽象成為一種象征意義。余華的《現實一種》通過接二連三的家庭內部兇殺凸現了人類生存現狀的殘酷。海明威《老人與海》中重復出現的同大魚搏斗的事件則成為了一個恒定的母題,啟示了人生的一種永恒意蘊:生生不息的追求。在格非的《褐色鳥群》中,事件的重復表現為三個敘事的怪圈,最終不僅消解了時間還消解了空間。《最后一個窮人》無論在結構還是在語言上都運用了這一策略,形成了喜劇格調,以喜劇的形式建構了悲劇的意味。所以文本閱讀時忍俊不禁,充滿爆料,但讀后卻是一股酸楚的滋味。小說的結構簡單,就是以收養三個棄嬰和二個女人為線索完成文本敘事的。一個連自己都不能保障的主人公——馬三多,卻在不斷重復收養被“公共”認為要遺棄的不道德的女人和被傳統封建思想所拋棄的女嬰,這在小說環境中就成了一個戲謔的對象,形成了一種反諷距離。小說除了結構的重復之外,在細節和語言上也存在著大量的重復。小說第一章寫的是包干到戶,分牲畜的一個情節,馬三多興高采烈從大隊里拉回來了一頭老牛,第二次拉回了一只獨角母羊,第三次拉回一個小驢車,在動作的重復中完成了這個悲劇人物的喜劇道具。他的喜劇事件都是在這三個道具下演繹的,不配套的耕種工具,形成了滑稽的場景。小說從開始到結束,馬三多一直重復著一句話:“我想要一頭毛驢”,可是奮斗了30年,最終還是沒有得到一頭毛驢,這不是更具有反諷性和悲劇味嗎?
悲劇進入現代社會喪失了它的崇高與莊嚴,代替它的是生活中的平庸與瑣屑。希瑟·拉夫(Heather K。Love)就認為,“悲劇的現代化和民主化意味著苦難成倍增加,而遭受苦難的原因卻變得越來越模糊。”⑤。不斷重復既是喜劇的手段,也是形成悲劇的手段。主人公重復犯相同的錯誤(至少是在別人看來)使馬三多的生活越來越窘困,他的生活與現實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愚、拙的性格特征逐漸在加強,反諷的意味也在不斷遞增,悲劇性也就不斷強化了。
其次,《最后一個窮人》的現代性還表現在中心人物的選擇上。南帆指出:“文學時常對于‘傻瓜’、‘瘋子’、‘白癡’表示特殊的青睞,例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魯迅的《狂人日記》,或者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這個世界的許多異常現象已經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可,以至于只有某些特異的眼光才能發現問題。如果說,那些高踞云端的思想家、哲學家具有一雙洞悉一切的慧眼,那么,另一些‘稚拙’的追問也可能甩開種種世俗的成規,返璞歸真——許多時候,思想家、哲學家與‘傻瓜’們并沒有多少區別。”⑥馬三多就是這一畫廊中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不同于《塵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爺,土司二少爺帶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是那種“大智”者的類型;也不同于《狂人日記》中的狂人,狂人具有瘋癲性和批判性。《最后一個窮人》中的馬三多是一種“拙”,是一種不合時宜,是與“聰明人”相對應的“傻子”形象。他不懂社會游戲規則,不圓滑、不世故,敢說敢言,無知者無畏,能夠突破世俗的樊籬,做出一些世人看來滑稽的事情,但這正是當下社會所丟失的本真。比如:馬三多種洋芋這一事件,本來“沙洼洼”這個地方就干旱少雨,加之生態的破壞,缺水日益嚴重,馬三多沒有生產工具,只能把種小麥改為種洋芋,可是這一年別人都絕收了,只有馬三多豐收了。這不是因為馬三多有“先見”的智慧,而是以他的“拙”質疑了人們習慣于從眾思維的“合理性”,順應了氣候的規律。這就是傻子形象的主題意蘊。
再者,馬三多形象的多義性還表現在他的批判性上。對他來說,外界變化如清風過耳,絲毫不能撼動他靜止凝固的心靈。除了放羊、種地,他不接受任何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這是一個由自然本能、簡單常識與淳樸道德組合而成的人物,他或許符合自然人性的理想,卻完全不適應現代化的時代。這樣,立足于馬三多的農民道德與智慧,反思工業化、商品化、城市化帶來的文明病,就不免有失偏頗,缺乏強有力的歷史理性的支持。畢竟,以貧窮自傲并不能成為道德與智慧的強心劑。如果道德與智慧必須付出貧窮的代價,那么,這樣的道德與智慧也就完全與現代性絕緣,沒有絲毫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雷達在《牧羊人的兩個世界——談談王新軍的小說》一文中指出:“王新軍的小說有一定的豐富性和獨異的地域色彩,但看多了也會發現,其創作潛藏著某種局限性、封閉性,他的鄉村世界我們漸次熟悉,覺得未知因素在減少,審美形態上的重復卻多了起來,對象和寫法有模式化之虞。王新軍面臨開拓新境的挑戰。”⑦《最后一個窮人》無論在敘事的長度與難度上都應該是一次挑戰,是他熟悉領域內創作的一次蛻變,既保持了他審美風格的古典性,又是對小說現代性的成功探索。我們希望王新軍走得更遠。
王明博 蘭州大學文學院
注釋:
①王新軍,《最后一個窮人》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8年版
②李建軍:論第三代西北小說家[J].朔方,2004.(4) 第68頁
③李繼凱:文學視野中的最后景觀[J].上海文學,1996(4)
④J.Hillis Miller.Fiction and Repetition[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versity Press,1982.(118)
⑤Heather K.Love.“Spectacular Failure:The Figure of the Lesbian in Mulholland Drive”[J].in New Literary History,2004,(35).
⑥南帆:良知與無知——讀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和〉,當代作家評論,2008(1),第8頁。
⑦雷達:《牧羊人的兩個世界——談談王新軍的小說》,上海文學,2005(9),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