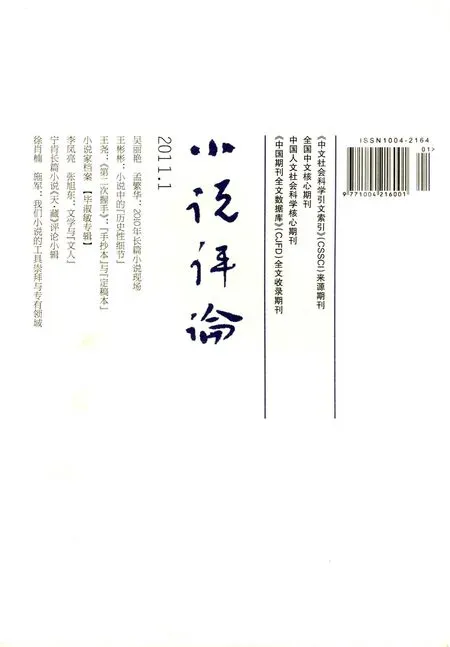寫在生命的懸崖邊上——論畢淑敏小說生命關懷主題的深化
趙 艷
寫在生命的懸崖邊上
——論畢淑敏小說生命關懷主題的深化
趙 艷
王蒙在為畢淑敏小說作序時曾寫下這樣的句子:“愛心是主干,責任是永久,使命是奉獻。”①誠如其言,畢淑敏的小說一向以對生命的熱愛和誠摯關懷為人稱道。那么,這份愛與關懷將幻化出怎樣的藝術世界呢?當我帶著這個問題系統翻閱畢淑敏的小說時,遭遇到的卻并非生命的良辰美景,而是滿目的荒蕪與瘡痍,她將生命的反面翻過來,將筆觸深入到險惡冰原、臨終關懷醫院、戒毒醫院、心理診療室等種種自然、社會、肉身和人心的絕境,將實踐愛心的使命交付臨死者、吸毒者、心理殘缺者這些極端化的生命樣態來承當。可以說,她所有的文字都是寫在生命的懸崖邊上,因此,行走于她的小說世界,常常令人艱于呼吸。為什么她如此執著于這些冰冷徹骨的生命境地和殘破不堪的生命形式?這些生命境地和生命形式之間存在何種內在的精神聯系?她是如何走來,又將去向何方?她的助力是什么?這是我在閱讀畢淑敏時一直探究的問題。
一
1980年畢淑敏創作了她的成名作《昆侖殤》。這部作品在壯麗奇崛的雪域高原背景下,展示了青春為“理想”而殤的故事。雖然這種理想只是歷史激進思想的一個錯誤剪影,但作者對熱血青年追隨信仰、死而無憾的真誠是傾心贊賞的。一方面控訴給生命帶來傷痕的歷史,另一方面反思生命在歷史假正義之名實施的暴行中收獲的價值,似乎缺乏有別于傷痕反思文學范式的新意。但在敘述的微觀處,一種頗具畢淑敏氣質的藝術世界正悄然展開:這就是故事發生的遼闊時空背景——藏北高原,這里遍布“可以掃瞎你的雙眼”的山風、“萬古不化的寒冰”、“高寒、缺氧、病痛……”,“時時聽到某人睡著睡著就過去了的傳聞”,更有“無人區”見證生命的脆弱和易逝,這種高原景象壯美且壯美,但更多地激起人們的畏懼,很多生命瞬間消亡了,還有很多生命在宿命般地走向消亡。這種生存處境不是一般地消磨意志或壓抑人性,它不給你回旋反思的機會。死神時時游蕩在你周圍,直接將你逼到生命的死角,每一個生命分分秒秒都活在死亡恐懼之中。源于此,畢淑敏才感嘆道:“注視著生命的短暫與無常,我在這一瞬,痛下決心,從此一生努力,珍愛生命。”②可見,極端嚴酷的生存環境使畢淑敏的生命體驗在起點處就已經觸到了人本生存的重大主題——死亡恐懼。
但是,當時的畢淑敏還沒有力量把死亡作為生存事件來體驗和表達,也就并未深入到死亡恐懼的生存論層面。無論歸因于毀滅性的極端生存環境(藏北高原),還是錯誤的歷史暴行(強行超越無人區的拉練),她的死亡恐懼都指向外在對象世界,并完全受其牽制,無暇反觀自身,探究作為生命體驗的死亡恐懼。因此,在與之對峙中,也就自然地將面對對象世界的英雄無畏氣概作為了倚仗。她筆下的那些已經或者即將消亡的年輕生命總是堅忍無畏地生活、工作,他們無視死神的威脅,個個手捧血書參加穿越“無人區”的拉練,甚至他們在死亡瞬間的感受、思緒都透著明亮。畢淑敏希望從他們的英雄氣概中得到傲視毀滅性的對象世界的助力,并從中獲取戰勝死亡恐懼的勇氣和自我生命升華的想象。事實是否真能如此呢?恩斯特·貝克爾曾指出:“首要地說來,英雄主義是對死亡恐懼的反映。我們最為贊賞面對死亡的勇氣,我們給這樣的勇敢以最高、最忠誠的尊敬。這樣的勇敢深深打動我們的內心世界,因為我們對自己將會有怎樣的勇敢心存懷疑。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毀滅,我們竭盡想象力一再傳誦這最偉大的勝利。”③可見,英雄主義式的想象其實是一種死亡恐懼的移情或者說轉化,它的訴求目標是征服對象世界,只能帶給我們“人造不朽”的臆想,而無助于解決問題本身,即通向真正的解脫之道。因此,盡管畢淑敏的“昆侖意象”作為一種極致生存環境持久地帶給我們凈化、崇敬、畏懼、悲憫等復雜的審美體驗,但她此階段的生命關懷主題還停留在起步階段,也為同主題的后繼深化預留了大量空間。
二
時隔十多年后,畢淑敏相繼創作了《生生不已》《預約死亡》和《紅處方》等一系列作品。與此前的“昆侖系列”相對照,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轉變,即由對外部世界的被動感受、對生命和所處社會關系之間的外緣性思考轉向對生命本體的觀察與求索。以對生與死的思考為例,《生生不已》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出個體生命的獨特性,以及生與死之間因循轉化的可能。《預約死亡》則是她脫離開特定時空環境、專注于死亡問題本身后的收獲。其中,她這樣反思我們對死亡的態度:“我們崇尚的是壯烈的死,慘烈的死,貞節的死,苦難的死,我們蔑視平平常常的死。”“你可以拒絕一切,但不可以拒絕死亡……我決定探索普通人之死”。④這意味著她終于拋開死亡的一切附麗,將其作為生命必須經歷的一個生理和意識環節來考慮,也由此得以深入到生命本體層面,細致呈現出了臨終病人在生命彌留之際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他們身體的腐壞、精神的麻木或痛苦、以及他們對死亡的想象或超驗的感知。通過此番種種努力,畢淑敏力圖實現一個死亡的去禁忌化,直面死亡和在生命的輪回中理解死亡中孕育的生機是畢淑敏此期在死亡這一生命大限面前的應對之策,較之于以前的英雄主義式想象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即“懷著對死亡的自覺意識活在世上。”⑤
值得注意的是,對生命感覺的發現與執著關注既讓畢淑敏的生命關懷主題進入了生命本體的生存層面,同時也拘囿了她在此空間的進一步深入。比較《生生不已》(1993)和《預約死亡》(1995)的創作時間可見,寓言式的對生命的感悟在前,而具體的對瀕臨死亡者的具象描繪在后,后者似乎是為前者的結論式認知尋求切實的現實邏輯支撐的產物。基于這種需要,畢淑敏直接找到了死亡最切近的具象呈現——臨終者,希望以觀察和紀錄的方式留住鮮活的生命經歷。但是這些人中,大部分意識已經處在彌散狀態,有的還是老年癡呆者或者被生理疼痛霸占了全部意識空間。也就是說他們的心靈和意識世界幾乎是完全封閉的,因此,對死亡的“預約”大多偏向生理層面的生命感覺。而生理層面的生命感覺很難直接通達彼岸世界,只有如史鐵生那樣徹悟了生命的偶然與必然之后,才能令人信服地飛升出對生命輪回的理解與想象。而這些只屬于超越肉身感覺的、心靈維度的空間。
經由這一缺失,畢淑敏再次出發,走進戒毒醫院,于是有了《紅處方》。之所以選擇吸毒者作為言說對象,畢淑敏自言是想給我們看生命的禁忌,知可為與不可為。而從創作主體思維的連續性上考慮,我想還因為在生命鏈條上,他們是一群由毒品麻痹導致的精神死亡者,最靠近死亡邊緣,這與畢淑敏此期關注的肉身生存范疇相當靠近,有自然過渡的可能;同時,又能夠真實地切入意識空間,便于她去發現在精神層面人是如何病變并走向消亡。在《紅處方》中,她依然采取觀察與紀錄的方式。那些吸毒者或者他們親人的講述,為他們在選擇毒品、依賴毒品行為中的心理意象結構(即人物態度和行為的心理成因)提供了有力的支撐。這是畢淑敏由肉身生存向精神、意識生存過渡的有效嘗試。同時,全書的靈魂人物簡方寧值得關注。她是戒毒醫院的院長,她博愛、無私、醫術精湛,是戒毒世界中的“女王”,而與她的完美相伴的是徹底的孤獨,她的戒毒醫院危機四伏、丈夫出軌、導師景天星是個只談戒毒治療的科學怪人、唯一的好友沈若魚時時希望她能脫離戒毒治療的“苦海”。她的生命關懷行動四面楚歌,最后還被自己病人莊羽送的禮物中暗藏的毒品害死。在全書寫實基調中,她是一個頗具隱喻色彩的人物,生命衛士與生命殉道者的雙重身份集于一身,在她身上既寄寓了畢淑敏于絕境中抗爭的決心和希望,也昭示了畢淑敏對肉身生存的惰性、趨惡性的極度悲傷和失望:人性的惡遠大于毒品的惡,專注于肉身療救的行動未必能夠承擔生命關懷的重任。最后,簡方寧寧可死亡,也不愿意切斷大腦中的“藍斑”得以存活,就是因為那樣做會使她失去對世界的豐富的情感感知,而僅僅成為一個生理生存體。這番安排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畢淑敏在簡方寧身上實現了對自己前此階段生命關懷方式的拓展,意識到對生命的愛不僅止于對死亡、病痛(包括身心兩方面)的意識、警示與療救,還必須進入一個更深的人性空間。故事最后作為作者化身的沈若魚要繼續簡方寧未完的事業——“到戒毒醫院去”,她與簡方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相當重視走進病人的生命歷史和人性特質,因此也必將帶來全新的生命關懷方式。這為下一階段畢淑敏走進更加博大的心理敘述空間探尋人性的病痛埋下了伏筆。
三
怎樣開辟新渠道走進人之性靈深處呢?2003年出版的《心理小組》和2007年出版的《女心理師》是畢淑敏的回答。“在沒有神父和懺悔的環境里,我只能找你。”⑥“我”是心理病人,“你”是心理師。心理病人和心理師交互助推,構筑了這兩部作品層次豐富的心靈世界,經由此,畢淑敏最終得以直觀切入人性最豐富也是最隱秘的區域,實施她深度生命關懷的理想抱負。
在這一新階段,畢淑敏放棄了她以往在面對對象世界時較多使用的觀察和紀錄方式,轉化為傾訴與傾聽。這一轉化也契合了她關注重心轉移的寫作實際。以前,她要展示生活和精神的黑洞,引起警示和療救的注意,她是治病者,可以說,她是自上而下降生在她的作品中,即便她深入臨終關懷醫院和戒毒醫院,看似融入對象的命運與呼吸,也終究是“體驗”而非“實際經歷”,因此,自然更趨向外觀式的寫作姿態。而一旦深入心理疾患領域,她就不但看到對象的病,也同時敏感到了自己的病,或者說人之共有的病。兩部作品中,心理師形象的變化即是明證:《心理小組》中的程遠青就已多次感受到自己與自己領導的心理小組組員們一起變化成長;《女心理師》更進一步,其中的賀頓也是一個心理重癥患者,她在深度剖析病人的心理疾患時,也同步進行著自我反身心理問診。因為從心理角度看,“人的一切弱點,心理師都有。”⑦也就是說,雖然心理師憑借專業的知識技能能夠通達形形色色的心理病癥世界,但她同時必然也是這些世界中的一份子。不管命運際遇如何,人在世生存就必然或多或少經受心理病痛的折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病人,這就是生存的宿命。對這種平等共在處境的清醒意識,決定了畢淑敏在此階段必須使用更平等和更具效能的交際方式——傾聽和傾訴。可以說,這一貫穿文本始終的心理治療方式既是畢淑敏心理小說中所有人物最重要的心靈交互方式,也是畢淑敏新的創作姿態的隱喻。那么,通過這種方式到底達至了一個怎樣的心靈世界呢?
首先,這心靈世界聚焦于人的無意識領域。眾所周知,心靈世界包括人的意識領域和無意識領域。意識領域具有自明性,為人的行為和態度提供明確的因果支持。而無意識領域潛沉在心靈世界的更深處,是人物行為和態度背后隱蔽的動因。如鹿路在介紹自己名字時不經意地解釋為五色鹿的鹿、小路的路,不同于一般人習慣且好記的梅花鹿的鹿和道路的路,而且與后者的中性色彩相比,前者明顯更具悲劇色彩,這正傳導出她無意識領域的某些訊號。畢淑敏心理小說首要的著眼點便是大量此類無意識心理事件。其中有對絕癥或死亡的隱諱,如成慕海作為極少見的男性乳腺癌患者,平時以健全的男性形象示人,而在小組中則喬裝為女性患者成慕梅;還有對自我罪行的規避,如卜珍琪幼年時無意間在父親和大庭廣眾之前道出了母親有私情的秘密,導致母親羞愧自盡,從此,她以對父親的報答來掩蓋對母親的愧疚,她不要個人意志、不要愛情,只求在仕途上晉升,以成為父親希望的女兒;還有對過往災難記憶的恐懼,如賀頓時時感到的徹骨冰冷就緣于兒時的慘痛經歷,等等。他們的生命軌跡各不相同,但對這些創傷性記憶或情感的態度都是強制自己遺忘或向他者他物移情,既不肯示人、也不肯示己,久而久之就成了駐扎在心底最隱秘處的“心魔”。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在意識層面受到危險、恐懼、絕望等消極情感因素侵擾后,若無力反應或消解,就會將這些傷害性情緒向無意識領域驅逐,于是,無意識維度的心靈世界往往就成為心靈疾患的集中所在地。這個世界極度晦暗恐怖,但卻是人心走向安寧健全的必經之地。我想,這也正是畢淑敏專注于此的原因。
其次,這心靈世界形象化地展示了“心魔”對人性的毒害機制。它完全破壞了人的完整自足性,使人從一個“我”分裂為兩個我:我自以為的我和我不知道的我,或者說我接受的我和我不接受的我。如卜珍琪自以為對仕途的狂熱是為了實現父親的遺志,實際在她身上還共在一個幼年卜珍琪因為羞死了媽媽而時時羞愧痛哭,這個因兒時罪感記憶無法釋懷而再也長不大的卜珍琪由于被主體強行遺忘而遁形了,表象的卜珍琪對隱在的卜珍琪無知無覺,但一切言行意志均受制于她。這種人格的分裂最直觀的呈現就是成慕海,他接受不了自己是男性乳腺癌患者的事實,就自創了一個妹妹成慕梅,由“她”來承受心靈的裂變。這種生命完整性的破裂導致了主體的深度迷失,有時這種迷失只指向自我,如安疆一生命運都由丈夫安排,從不具有自我意識,即便丈夫死后,她也能夠在夢中領受丈夫的指示,拒絕接受治療,期盼到另一個世界繼續活在丈夫的生命中。但是更多的時候,這種迷失引發向外的傷害或報復行為,如卜珍琪的晉升就犧牲了丈夫理應得到的真實的愛情和家庭幸福;還有那些被周云若頻繁更換的男友又何嘗不是她“心魔”的無辜犧牲品。可以說,不管向內還是向外,“心魔”對人的毒害都是毀滅性的。通過對其的展示和剖析,畢淑敏提示了拯救行動的必須和迫切,同時也為主體的反常言行和意志提供了解釋。
病因及其導致的病理征象已經昭然,依據畢淑敏醫者仁心的慣性必然要為這些創傷性情緒尋求開釋通道。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拯救?回避是拯救之途中最大的危險,“讓心事自生自滅,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它絕不會真正消失,只是貌似離去,耐心地等待著卷土重來”⑧,甚至須臾不曾離開。只有通過痛苦的自問、回憶、傾訴、傾聽等方式,才能發現真相和那個潛藏在無意識深處的自我,進而才有接受真相和隱蔽的自我、復歸主體完整性的可能。《心理小組》中程遠清和成慕海推敲應該將小組命名為“會心”,因為在小組中的每次活動都是不同組員心與心的交會。我想,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它更傾向于明了自我和生活的真相,因為會心的解釋是“領會別人沒有明白表示的意思”,那么,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領會了生命沒有明白顯示出來的陰森晦暗、惡魔化的一面,從而實現了自我與自我的會心。畢淑敏在小說世界中反復演繹的就是這一心靈拯救方式,她和她的人物不斷地由意識層面進入無意識層面,將其中的心魔召喚到意識層面來,再在意識層面或解釋、或疏導、或爭鋒相對。在這一從意識到無意識再到意識的過程中,要經歷無數人心的險與惡,因此也尤其慘烈和艱險,“靈魂的廝殺”、“心靈的蹦極”、“千瘡百孔的心靈漏斗”、“精神裸露在慘淡的廢墟上,骨刺穿過胸膛”等文本中經常出現的字眼,勾畫出了這個心靈煉獄的常態。而經受了煉獄的煎熬之后,心靈也將由地獄通達天堂。所以,那些起初萎靡憔悴的生命再次充滿了生機。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安疆和喬玉華的轉變:安疆在找回丟失多年的自我以后,給自己安排了莊嚴而幸福的死亡盛典,在珍愛她懂得她的心理小組組員們的陪伴下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喬玉華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明白了自己對101個洋娃娃固執的牽掛是由于一生中傷害過101顆無辜的靈魂,并懇請他們原諒,她“直面真相,對善和悔都恢復極度的敏感”,她“走得深刻而辛苦。但走到極致之后,就是拯救和逍遙”。
若此處我們稍加停留,對照一下畢淑敏過往和此時對死亡問題的思考和言說,不難發現其中的深刻變化:從一個生理事件到一個心靈事件,從接受生命大限、想象生命輪回到皈依自我完整性后的寧靜平和、再到清理靈魂罪感后的坦蕩飛翔,之間穿越了漫長的心路歷程。王安憶在《心靈世界》中將小說中的世界稱為心靈世界,她指出在面對同樣的現實世界時人的認識之間存在質量的高低之分,而認識的質量決定了小說這一心靈世界的完美程度⑨。從死亡意象的角度看,畢淑敏在逐步深入她所關愛的生命時,也在不斷提升自我的心靈質量和認識質量,她筆下的心靈世界完美或許并不完美,但我們可以清晰見證她朝此方向的努力。
畢淑敏在《造心》一文中談到要為心靈尋找新的生長點、避雷針、添加防震防爆性能,以使其可以休養生息、承受打擊、維持蓬勃穩定。我認為,她是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從對抗外在世界的威壓與摧毀起步,到對抗肉身生存的死亡與病痛,再到警示精神生存中的惡劣慣性,最終直至勇敢面對無意識層面的“潛我”,她的生命關懷經歷了一個逐步向內向深轉的過程,同時,她也由一個生命的觀察和紀錄者轉變成了一個生命的傾聽和傾訴者。她發現了個體隱秘的心靈事件及其對靈魂造成的壓迫,發現了個體靈魂的悄然質變與主體行為態度之間的隱秘聯系,她提示我們對生命的自覺意識,敦促我們反思:我真的了解自己嗎?今天的我如何生成?我受制于我的無意識秘密嗎?它們是什么?
雖然她的小說世界充滿了痛苦和扭曲,她的人物都是身心遍體鱗傷,但是經過這個世界,她不斷地在現實與超越的層面嘗試拯救與逍遙的途徑,引領我們直面真相、向生命和自我的完整自足性復歸。鐵凝曾說:對生命真正的體貼和愛是“從最初穿越了很多困難、毀壞、甚至是地獄的某一段,仍然沒有沉下去,而是一再地上升,最后達到的境界才是澄明。”⑩這應該可以作為畢淑敏生命關懷深化過程的注腳,幫助我們感受她寫在生命懸崖邊上的愛的世界、及其中愛的力量和光輝。
趙艷 武漢大學
注釋:
①王蒙:《藏地情〈序二〉》,中國物資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②畢淑敏:《雪山上的少女》,漓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頁。
③恩斯特·貝克爾:《拒斥死亡》,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④畢淑敏:《補天石〈預約死亡〉》,中國物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頁。
⑤薩姆·基恩:《拒斥死亡〈前言〉》,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⑥畢淑敏:《女心理師》,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頁。
⑦畢淑敏:《女心理師》,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頁。
⑧畢淑敏:《女心理師》,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
⑨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28頁。
⑩鐵凝:《對人類的體貼和愛》,《小說評論》2004年第1期,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