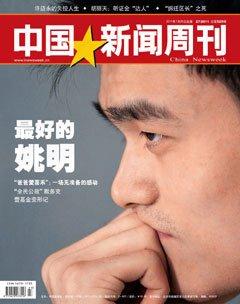讓人類擁有免除恐懼的自由
2011-09-06 14:27:49黨國英
中國新聞周刊
2011年27期
關鍵詞:人類
黨國英
讓理性包容利己心,并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必然冷酷,必然不和諧,因為在很多方面人們可以通過交易實現互利。但有了不確定性,人就很難進行利益算計,也就無法保持其一貫性,于是就遠離理性
我相信理性的意義,相信理性對于人類歷史的價值。但無數事件表明,那些看起來正常的人們,可以在或短或長的時間里陷入非理性狀態。有記敘文學專門記錄人的瘋狂行為,也有經濟學家批判理性假說,用嚴密推理說明非理性行為的現實性。
如果人類的行為全然無理可尋,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癲狂起來,人類還有什么希望?人類若真有這種劣根性,我們探尋文明、追求制度建設又有什么意義?我持有樂觀主義的秉性,寧肯相信人類理性絕非虛幻,只是理性這東西并不總是與我們貼身而行。
現在我們把十年文革作為非理性的、癲狂的時代。我經歷過那個時代,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到高中畢業,除了高中那兩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之外,其他時間都沒有正經上過課。武斗開始以后,我們街道的各家各戶都用陜北人特有的毛氈覆蓋了窗戶,說是可以防止子彈射進家里。父親被掛紙牌游街的“罪狀”之一,是說他用《毛主席語錄》的塑封皮裝了鈔票,后來聽父親說根本沒有那回事,是同事捏造誣告,荒唐的事情數不勝數。
文革前的那場“大躍進”也很瘋狂。據說不少名人在自家院子里也架起爐子、砍掉花木煉鋼鐵。
西方中世紀也有癲狂時期。……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哈哈畫報(2022年4期)2022-04-19 11:11:50
大科技·百科新說(2021年6期)2021-09-12 02:37:27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6:54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8期)2021-01-18 05:13:32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8期)2021-01-18 05:13:26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7期)2021-01-18 05:07:18
好孩子畫報(2020年5期)2020-06-27 14:08:05
小學科學(學生版)(2020年2期)2020-03-03 13:40:1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50
童話世界(2019年14期)2019-06-25 10: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