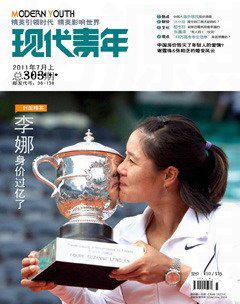“日本韓寒”加藤嘉一 一個高調的“現代遣唐使”
米艾尼
他被稱為“中國通”、“現代遣唐使”、“日本的韓寒”,以及“未來中日關系的一個大人物”;他在中國學界如魚得水,專欄作家、主持人、同聲傳譯、跨國談判……他與眾多政界高官結友,針砭時弊。他就是1984年出生在日本伊豆的加藤嘉一。在2005年中國反日游行以前,加藤嘉一還很少被中國媒體所知。或許那時的加藤并沒有想到,讓他真正開始實現理想的地方,正是中國。
伊豆——富士山下三面環海的小小半島,因為川端康成的名著而揚名于世。生長在這里的加藤嘉一,曾經是一名立志參加奧運會的長跑運動員。但是除了他的親人和朋友,這里也許沒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若干年后,在大海的另一邊,27歲的加藤嘉一成為中國當下最炙手可熱的日本留學生,電視新聞節目里中日關系的熱心觀察家,幾本中文暢銷書的作者,甚至被稱為“中國通”、“現代遣唐使”、“日本的韓寒”。
當加藤嘉一身邊的人們都把他定位成一個具有極大政治抱負的青年領袖時,這個27歲的日本青年卻說:“我從來沒有抱著從政的理想,只是這個工作比較適合自己;我在中國沒有一篇文章是我自己愿意寫的,只是出于社會責任感希望達到我和社會的某種平衡。”
伊豆農村的貧窮少年
“我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因為,我從小就缺乏家的感覺。”加藤嘉一的這句話是有背景的。
19歲以前,加藤的生活異常艱辛,他曾經自嘲是“貧二代、農三代”。父親在他10歲時因為一次失敗的投資破產后,全家為躲債搬家50多次。他13歲開始打工補貼家用,每天凌晨3點起床送報紙,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難時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約30元人民幣),他只得帶著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試吃食品充饑。即便如此,他的性格里從來都沒有軟弱的因子。
加藤嘉一身高1.84米,從小就比別的孩子高。“也許因為我的身高,我從小就是孩子們中的小頭目,從來沒有位居第二過。”在加藤的少年和青年時期,長跑曾經是對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為父親熱愛體育,所以從小學起,他和弟弟就在父親的指導下,每天早上跑5公里,放學再跑5公里,加上步行上學的時間,每天要連跑帶走20公里。加藤說,他從小只有兩個愛好:跑步和看世界地圖,五六歲的他就能把全世界的首都背下來。
“高中時,我希望自己以后去聯合國工作。不過這需要至少懂兩門外語。我認為,要學好外語,必須到那個國家去才有體會。”帶著“聯合國夢”,來自伊豆農村的貧窮少年,考上了日本最好的大學之一——東京大學。隨即,出于貧困和希望出去走一走的雙重考慮,加藤決定退學,并到中國留學。2003年春天,當加藤在成田機場告別父母的時候,他們說,不要后悔,注意身體,好好生活。
留學生中刻苦的“異類”
或許那時的加藤并沒有想到,讓他真正開始實現理想的地方,正是中國。
在2005年中國反日游行以前,加藤嘉一還甚少被中國媒體所知。那時他只是在北京大學進修國際關系的一名刻苦的日籍學生,偶爾會在網絡和雜志上發表一些觀察中國的文章。
2003年,走下飛機踏上中國土地,加藤嘉一發現,現實的中國與他在日本所想象的非常不同。對于古代中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秦始皇。對近現代中國,以前聽到最多的詞是“共產主義”。“我以為中國什么都是統一的,比如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東西等等。”在機場的貨幣兌換處,加藤把兼職做翻譯賺的10萬日元全都換成了人民幣,總共是7000多元,開始了他在中國的新生活。剛在北大安頓好,就遭遇了SARS疫情。當時日本駐華使館在官方網站上公開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國,加藤在父母的支持下,選擇留下來。“我父親說,千萬不要回來,一是機票很貴,浪費錢;二是應該親自經歷一下‘非典形勢下的北京。”
于是,加藤就在那個人心惶惶的初夏,尋找一切機會學習中文,了解這里的一切。他的生活是這樣安排的:每天早晨開始跟學校周圍小賣部的阿姨比畫著聊天,聊到下午5點找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讀,晚上7點準時收看《新聞聯播》,夜里11點聽廣播里的各種人物訪談。“北大旁邊小店很多,那里的阿姨們也都很好,很包容,不會認為一個日本人跟他們聊天有什么奇怪,這大概是北京人的特點。”他說。
這個大大咧咧的日本留學生,用3年時間掌握了中文的聽說讀寫,甚至說話中會夾雜一些北京時下最流行的詞匯,會正確使用兒化音。在北大時,他一直比較另類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后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大家都覺得我無趣和無聊,活得跟機器人一樣。我從小就是這樣的人,每天做同樣的事情。我覺得必須把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讓計劃控制變化。”
加藤覺得,或許他自己是極端的,但是日本大學生都很有計劃性。“他們一天打工不到5個小時的話,謀生都成問題,在東京生活很貴,日本的父母頂多給孩子支付學費,生活費都是自己掙。”加藤說,他也是剛剛還完這幾年向父母的借款。他覺得,北大學生很聰明,知識儲備足夠,但還要學會做人。“要能夠走向草根,從底層開始鍛煉自己,具備了耐力的人,就是人才。”
他的導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朱峰說,加藤確實很刻苦、善于思考,但“加藤只是我的學生之一,我并不希望我所有的學生都成為他”。到此為止,加藤還只是一個留學生中刻苦的“異類”,他心中的理想或許也還未見雛形。
“說什么不重要,怎么說才重要”
加藤真正走入中國人的視野,從2005年的反日游行開始。“我也忘了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東西,開始是發表在一些雜志上,大概內容是寫日本人眼中的中國。2005年反日游行發生的時候,《鳳凰衛視》需要一個親歷者的聲音,他們覺得我的形象和身份很適合出來講,于是我第一次上了電視節目。從2005年到2008年之間,我的寫作量非常大。”
加藤認為,中國社會對他真正開始關注,是他在FT中文網發表文章開始的。他甚至開始受到中國官方的關注。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跟他關系非同一般,曾經說:“年輕人應該怎樣走,向加藤同志學習!”
“說什么不重要,怎么說才重要。”加藤說。在中國將近8年的時間,讓他深諳在中國的官場、民間、媒體等各個領域的生存之道。談到加藤的“走紅”,曾為加藤嘉一的書《以誰為師》作序、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的馮昭奎覺得,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有一個外在的原因:在中國,關注中日關系的人很多,加藤是第一個喜歡評論中日關系的、在中國的日本人,這是他的機遇。“但這同時也是他在中國發展可能受影響的地方,就是受制于中日關系的走勢。釣魚島事件后,中日關系有點問題了,他是日本人,所以
很多媒體就不找他了,他當時也挺苦惱的。好在他的志向不是當學者。”馮昭奎說。
對于一個正在異國實現人生理想的青年人來說,日本國籍的特殊性和中國社會的需求,可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在加藤的心里,未嘗不清楚這一點。
“我覺得自己像個遣唐使”
當中國媒體與這個日本“80后”青年的“蜜月期”結束后,猜測和非議也漸漸出現。
雖然是加藤的導師,朱峰仍不避諱地對記者評價加藤“愛吹牛,企圖心太大”。在馮昭奎的印象里,加藤算不上太張揚。“在日本,搞評論的人寫作量都是很大的,著名的評論家一生甚至會寫100多本書。他頻繁地出書,也許和日本的文化習慣有關。”
很多加藤的中國朋友認為,他很“中國化”,甚至不像是個日本人,但是馮昭奎覺得,加藤其實很愛國,但他對中國有感情,希望中日關系能夠好起來,日本和中國都能得到發展。至于加藤在日本本土的口碑,馮昭奎認為還談不上,在日本他還沒有那么強的影響力。“我不太在意媒體的說法,我從來不看關于自己的報道。”加藤是這樣對待外界評價的。對自己青年時去聯合國的夢想,加藤現在的理解又有不同。“并不是我從小立志從政,是周圍的人都覺得我適合這個職業,我也這么認為。我對從政的理解是多元的,只要可以引導社會政策的走向,我認為都是從政,所以作為學者或者好的媒體人,或者去競選,這都叫從政。”
加藤準備過兩年離開中國,到美國或歐洲國家去。“說實話,不管是出名也好,寫書也好,我從來都沒有高估我的現狀。我個人認為,走到今天我自己的努力不到10%,更多地依靠中國社會的開放和多元。我很謹慎地看待現在的一切。”
加藤說,在日本或在中國,在成長中遇到的困難是一樣的,他不會抱怨什么,“我最大的痛苦是自己還不夠好”。“如果說現在我有一點點平臺、有一點點話語權,這對我整個人生的規劃到底是福是禍,還有待檢驗,有可能是毀滅性的。我一直很自卑,我每時每刻都在懷疑,我是否會失控撞礁,但是對外在的評價,我從不在意。”
他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4個字,沒有任何頭銜。加藤說,他現在寫書、演講,什么都干,還在北大任教。而他今年最大的目標,是能在10月國際馬拉松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加藤嘉一曾經去了西安,他繞著城墻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覺得自己像個遣唐使”。唐時,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長安城墻的淡青色陰影里,最讓他們震撼的,不僅是城市規模之大,還有一點,那就是唐代幾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墻護衛,這是日本沒有的。這讓遠道而來的日本遣唐學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嚴的畏懼。這種情感的底色大概從來沒有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