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趣拾
■ 吳解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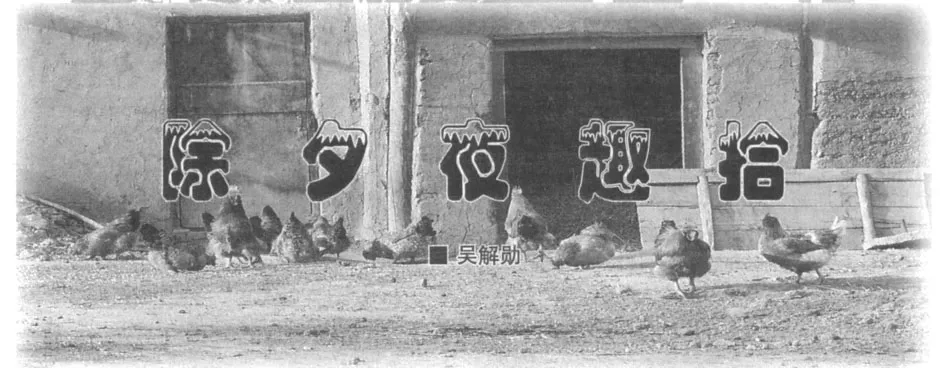
河湟地區人們通常戲言說:“吃了麥仁飯,天天忙過年”,除夕前的這二十多天便稱“忙臘月”。的確,這樣的形容一點也不為過。那段時間忙忙碌碌,風風火火,總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縫制新衣、殺豬宰羊,購供品、寫對聯、掃房子、糊窗子、油炸、籠蒸、水煮……除夕前兩天,男人們都要剃頭刮臉,“有錢沒錢,光光頭過年”,窮富不在乎,要有精神頭。女人們更會洗頭凈身,梳妝打扮。這就印證了“忙了一年,為了過年”那句老話,尤其除夕之夜是過年中最為期待、最為隆重、最為熱鬧的。
平時,由于年幼頑劣調皮,母親從不給我好臉色,總是“橫眉冷對”,“你不要得失”的指責與提示不絕于耳。只有到了每年除夕這天,她突然變得和顏悅色、笑容可掬。這種突變,使我萬分感動的同時,倒覺得很不自在,眼睛不知看誰、手不知放哪兒了。母親總是一邊做家務,一邊叮囑:過年了,家里親戚多,要有規矩、有禮貌。此時此刻,受寵若驚的我不斷點頭,“嗯、嗯”地應答著。其實,我當時對于春節的期望,只是放鞭炮,拿年錢,吃幾天白面饃饃,還有不再在風雪嚴寒中去拾糞砍柴,盡情地玩上幾天,僅此而已,不可能尋釁滋事,惹是生非的。
除夕早晨,家族里幾十戶人家會聚集在巷道口,各自帶燒紙、米粥、獻茶、油香之類的祭品到祖墳祭奠亡故者,據說是邀請亡靈與之團聚,共度新春。之后,灑掃庭院門戶,碼放家具什物,院門房門貼上鮮紅的對聯,掛紅燈,貼錢馬,獻供品,壘松蓬。吃過面片,就意謂著辭了舊歲,迎來新年,除夕夜也就拉開了序幕。小孩們穿上新衣,老人們穿上長袍,堂屋供桌燈燭齊明,家里家外鞭炮聲聲,大家圍坐熱炕頭,話年景,敘親情,一派家和人和景象。子時一到,迎天神祖宗亡魂的“接神”開始:松蓬點燃,鞭炮震耳,香煙繚繞,火光沖天,老人們喜笑顏開,不時被小孩們拽去看那些五彩繽紛的花炮和被這些花炮裝點的絢麗夜空。有了電視節目后,除夕夜更加異彩紛呈,熱鬧非凡。全家老小精神抖擻,睡意全無,甚至通宵達旦說笑玩耍,盡享天賜之福。
年景好時,有時是青海“老八盤”,有時是做幾個涼菜、上幾道拿手熱菜,老人、兒子和兒媳們還要喝幾盅“年酒”,甚至可以一醉方休。但是,無論怎樣,吃團圓扁食是不可或缺的。母親把吃扁食這件事會牢記于心,認為這里面蘊含喜慶團圓、大吉大利、祈愿來年順利之意。吃過扁食之后,母親還會將事先準備好的“壓歲錢”分發給我們,“壓歲錢”的多少也是根據生活水平和物價指數,從幾角到幾元遞增的,孫子孫女們有,兒子兒媳們也會有。當然,“壓歲錢”是磕頭之后才能用雙手去拿的。后來我步入中年,母親年歲大了,我們晚輩們給她“年錢”,也由我們給晚輩“壓歲錢”了。這時,除夕夜高潮已過,全家人壓歲守歲,講故事,猜謎語,行酒令,串門子,直到凌晨。
除夕夜也不是年年紅紅火火、高高興興的,凄風苦雨的年份也是不少的。三年困難時期,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掙扎在死亡線上。除夕夜,村子死一樣沉寂,靜得發怵,死神在村子角角落落游弋,聽不到鞭炮聲,聞不到酒肉香,沒有喧嘩,沒有燈光,莊戶人同太陽一起沉沉睡去,同太陽
一起緩緩醒來。記得有一年除夕夜,我們全家五口人焌了大小不一的十三個洋芋,父母親每人兩個,我們兄妹每人三個,狼吞虎咽之后,父親一臉無奈地對我們說:“早早睡吧!”我們也就很順從地各自去睡覺了。當時除父母和哥哥、姐姐外,我剛記事,我不但不覺得凄涼寒酸,倒認為除夕夜很奢侈,還能吃到三個洋芋。就這,我也期待了三年。
后來的日子好了,尤以春風吹度的那次會議后,才算過上了舒心的日子。除夕夜似乎什么都不缺,唯獨缺了兩位歷經艱辛磨難而又慈祥和藹的雙親,他們已安眠在曾勞累一生的那座山的半山坡多年了。每每除夕夜,空中的那束月光,便會撥動我苦澀的心弦,也隨之想起母親親手打理料亂,讓我們盡可能地快樂度過除夕夜的各種各樣的身影。這時,我的心仿佛被月色喚起,又回到老家的庭院里,聞到炕煙和錕鍋的味道,從很厚重的鄉村煙霧中將母親邀請到凡間,享受除夕夜的奢侈和兒孫們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