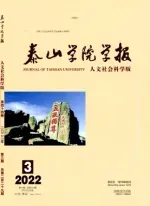“仁且智”與“由仁義行”:孔孟理想人格考論
萬光軍
(山東大學哲社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一、孔子與“仁且智”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的理想人格可以說是仁智統一,即“仁且智”,這一表達主要來自于孔子及其弟子子貢: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矣”。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
孔子自謙、不自稱為圣,而弟子子貢則通過展開“學不厭”與“教不倦”,認為孔子具備了“仁且智”的品格,并認為“仁且智”即是圣(甚至超過圣)。“仁且智”蘊含重要含義:一方面,學不厭之智涉及知識,教不倦之仁涉及道德,仁且智就表明既要有道德又要有知識,并且道德優于知識,這種結構應該影響到了后來的“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才兼備”、“做人與做學問”、“又紅又專”等表達,對中國文化應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學不厭涉及自己、教不倦涉及他人,自己與他人的和諧共進,表現為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成己成人、立人與達人的統一。從正面上說,仁且智說明理想人格要求很高、很全面,既要有道德又要有知識、既要成己又要成人,二者缺一不可;從反面上說,仁與智的分離、有仁無智或有智無仁都有所缺陷,“未知,焉得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并且仁對智的優先決定了德的缺失(無德、缺德)其缺陷會更明顯。如齊景公有地位、有財富,但百姓無德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曹操公開提出“唯才是舉”,對于德有所忽略,在歷史上(相對于劉玄德)也就受到了批評(如白臉而非紅臉、梟雄而非英雄);并且,自己與他人關系隔離、緊張,甚至對立、仇視,產生諸如人際冷漠、勾心斗角、以鄰為壑的不良現象,這些都需要結合孔子的“仁且智”來進行反省改進。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且智”,那孔子的理想人物是誰呢?理想人格的具體化應是理想人物,理想人物應合乎理想人格的模式要求。某人的理想人物是與某人關系最為密切、結構最為相似的人,在中國哲學這里經常表現為“祖述”早于自己的古人,如此以來,某人的理想人物經常就是某人最為傾慕、關系最為密切、結構最為相似的古人。如孔子是因為“仁且智”而被稱為圣人的,那孔子的理想人物也應合乎“仁且智”的模式要求,并且是孔子最為傾慕、關系最為密切的人。簡言之,孔子的理想人物是周公,表現為:“仁且智”是其理論結構、夢周公是孔子的自我表白、周孔并稱是后世的普遍認可。
孔子是“仁且智”,周公也是“仁且智”嗎?這在《論語》中沒有具體材料的直接證明,但我們可以通過相關材料來間接推理一下。孔子說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從較為寬泛的角度,周公之才(兼夷狄、驅猛獸、平定叛亂)是很突出的(后來孟子講三亂三治中周公就占三治之一),由周公之“才”而說周公是“智”應該可以成立;周公之美(一沐三渥發、一飯三吐哺)也是很突出的,由周公之“美”而說周公有“德”、或說周公是“仁”想來大體也可以。由此不妨說,周公“之才之美”大體可以等同于周公“仁且智”,在“仁且智”的結構上,可以說周公與孔子具有相似性。孔子說過“如有”是假設、是借用了周公來推演;并且“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有些消極含義。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當孔子在進行理論推演時,他是以周公來作為標準的,是間接認為周公有才有德(“之才之美”)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周公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當然是很高的。除《論語》外,周公被稱為“仁且智”在《孟子》中有具體材料的直接證明: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于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稱孔子“仁且智”的根據是“學不厭”和“教不倦”、稱周公為“仁且智”的根據應是“知而不使”和“知而使”,盡管稱兩次“仁且智”的根據不盡相同,但在《孟子》中出現了兩次“仁且智”,并且兩次就指向孔子與周公,這還是很明確的,由此而說孔子與周公在“仁且智”上有共識想來大體不差。孔子傾慕周公還有他的自我表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說明在孔子這里“夢見周公”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以“夢見周公”為幸事、以“不復夢見周公”為憾事,說明他時時以周公為表率來激勵自己,周公的地位和作用顯然別人難以超越、難以替代的。寬泛說來,孔子對堯、舜、禹、周文王等都有贊美之詞,如稱贊堯“則天”、稱贊舜禹“有天下”、稱贊文王有盛德,這些稱贊都比較高,但如果相比周公,顯然周公才是孔子的“理想”人物。
孔子傾慕周公,稱周公“仁且智”(之才之美),以之為理想人物,也被后世所認可了,后世經常出現了“周孔”并稱或類似的表達。如《孟子》中就有“悅周公、仲尼之道。”如嵇康的“非湯武而薄周孔”“以周孔為關鍵。”唐太宗講“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在韓愈這里,周公與孔子的密切聯系得到了儒學的理論支撐,即著名的道統論:“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道統論的提出使得周公與孔子并稱變得理所當然,由此在韓愈這里,周孔并稱(多數時候是“周孔”、有時也用“孔周”)也就經常可以看到。“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平生企仁義,所學皆孔周。”總之,無論是“仁且智”的理論結構、“夢見周公”的自我表白、還是“周孔”并稱的后世表述,說孔子以“仁且智”為理想人格、以周公為理想人物,想來可以成立。
二、孟子與“由仁義行”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且智”、理想人物是周公,那孟子的理想人格與理想人物是延續孔子、還是有所調整呢?這相對有些復雜,需要細致分析和多方面比較,才有可能得出較為穩妥的結論。在《孟子》中有段著名的話:“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我們現在多認為人禽之異在于道德(仁義)、并且認為道德行為應該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這應該與孟子大有關系,此處本文不打算全面展開,主要關心的是:什么是“由仁義行”、孟子為何說是“舜”由仁義行?對于這段話,筆者開始多有迷惑、后來才有所理解,在此求教于大家。
孟子講人禽之異在于道德(道德在孟子這里多運用了仁義的表達),進而就要在理論上把真正的道德行為解釋清楚、并應把(他所認為的)道德典范提供出來。
一方面,孟子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應該是“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由仁義行”說明了道德行為必須具有自覺性、主動性、持久性,或者說只有自覺、主動、持久的道德行為才是有意義的,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否則蒙昧、被動、暫時的道德行為(“行仁義”)是沒有意義的,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為此,他借用“有源之水”和“七八月間雨水”來比喻,指出“由仁義行”如同“有源之水”、是“有本”的行為,會自覺、主動、持久,而“行仁義”則如同“七八月間雨水”、是“無本”的行為、雖喧囂一時、然終歸于沉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以有源之水和七八月間雨水來進行比較,十分形象,有很強的說服力;孟子希望人們取法有源之水(“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實際上反映了他希望人們自覺認可并積極踐行這種“有本”的“由仁義行”的道德行為。
另一方面,如果把“由仁義行”當做是標準的、甚至唯一的合理道德行為模式的話,那么誰“由仁義行”就應該把誰當做道德典范、理想人物;道德模式必須有人來完美踐行,而道德典范(理想人物)就是道德模式的完美踐行者。在孟子這里,孟子列出的人物是舜、認為舜“由仁義行”,即在孟子這里,他認為舜是道德典范、理想人物。客觀說來,說“由仁義行”才是標準的道德行為模式,這爭議不大、甚至可以說會得到絕大多數的認同;而要說舜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肯定會引起不小的爭議,就是筆者自己剛剛推出這一“奇怪”結論時,也嚇了一跳、有點不相信自己;好在這不是筆者先前的預設、不是憑空的無端猜測,而是順著孟子的思維順序“推”出來的、也是孟子自己講的,雖然奇怪、但并未立刻放棄;并且,當帶著這一奇怪的結論再反復讀《孟子》時,才發現“舜由仁義行”、“孟子以舜為理想人物”在《孟子》中是相當重要的問題,是得到了大量材料支持的,是大體上能夠成立的,在此不妨略加陳述,希望方家指點。
首先,舜“明于庶物”與“由仁義行”有何關聯,使得它們能夠放在一起?單獨來看,解釋清楚不容易,但《孟子》中還有一段話恰恰提供了相關解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可以說,單獨來看這些話,也覺得有些奇怪、突兀,但如果與此前的話放在一起,兩段話就能得到合理解釋:前者“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與舜“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可以互通;仁義可以理解為道德、理解為善,“由仁義行”可以合理解釋道德的自覺性、主動性,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則能說明向善的巨大決心和勇氣,與道德(由仁義行)的自覺性、主動性可以互補;加之孟子所講人物都是舜、都講人異禽獸、都講幾希,如此可以說,本段話不奇怪、不突兀,而是對舜“由仁義行”的有力支持。
其次,就完整的“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來說,舜何以是“察于人倫”?人倫與仁義有何關系?“人倫”一詞在《孟子》中有幾處表達值得注意:“規矩,方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指出,為君為臣都應效法堯舜(因堯未曾“為臣”、說“為臣”效法堯可能為虛指,故實際上說“為君為臣”效法舜更為恰當),堯舜之道為政取十分之一、由君子治理且人倫融洽,在中國是最為合理的,不如是都會有所局限。在此,堯舜對于和諧融洽人倫關系的建立與維護的重要性不難看出。由此可知,孟子講“舜察于人倫”也不是隨口而說,而是多次提及的。通過對“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的逐一展開,我們可以發現孟子說“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絕不是孟子偶爾言之、絕不是無足輕重,而是多次言及、非常重要的;并且,在其中我們頻頻看到舜的提及,而其它人如孔子、大禹等與之基本無關,看來其中還有很多內容有待繼續思考。
除此之外,孟子的仁義思想也經常涉及舜。在孟子這里,仁義可以說是善,孟子講舜與人為善。“大舜有大焉,善于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對仁義的討論當然涉及性善,在人性平等上,孟子講“堯舜與人同耳”、“人皆可以為堯舜。”在人性差等上,孟子講“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在義利關系上,孟子讓舜與盜跖進行比較。孟子曰:“雞鳴而起,孽孽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孽孽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在政治上,孟子以堯舜之道為仁政,自己勸說君主的就是堯舜之道。“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抽象的道德原則(即仁義)還轉化為具體的倫理規范(即仁與義),孟子對仁與義的現實解釋是:“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
在現實倫理規范中,孟子認為只有仁與義有實際內容,而仁與義大體有兩種解釋:狹義上,仁與義指向“親親”與“敬長”;廣義上,仁與義指向“父子”與“君臣”。當仁與義指向親親與敬長時,孟子指出堯舜之道就是孝弟,也就是仁義之道;當仁與義指向父子與君臣,并且當父子與君臣可以得兼時,舜(在現實中)既是孝子又是天子,而當父子與君臣不可得兼時,孟子(在理論上)讓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這可以說明孟子雖然知道舜既是孝子又是天子,但是孟子似乎更重舜是孝子的一面,孟子是以舜為大孝的典范的。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還有,當別人對舜有所懷疑或批評時,孟子總是積極為舜進行辯護,反映了孟子力圖維護舜完美形象的良苦用心,反面上也說明了舜的形象完美對于孟子是十分重要的。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可以說,作為一個現實人,舜的言行有時不能十全十美是正常的、受到懷疑或批評也是正常的,但孟子極力進行辯護、美化,使人覺得舜就是完美無缺的、或只有舜才是完美無缺的,如此舜與孟子的關系真可謂非同一般。
除了對仁義與舜的種種展開和辯護,孟子如同孔子一樣也有明確的自我表白,顯示了他對自己理想人物的期許。“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把自己與舜進行比較,指出舜可以為法于天下,而自己則處境尷尬,他公開自己的志向是“如舜而已矣”,并且當做一生的追求(“終身之憂”)。總之,不管是抽象的理論層面(舜“由仁義行”),還是現實倫理規范(舜是“孝子加天子”);不管是人性層面還是義利、政治角度;不管是被動的辯護還是主動的表白,孟子對仁義的一再重視、對舜的屢次提及是非常明顯的。《孟子》中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宋代程子曾說:“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三字經》也總結為:“《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現代學者在研讀孟子思想時也有很多看到了仁義對于理解孟子思想的重要性,如張岱年先生講“孟子哲學的中心觀念則是仁義”。看來如果要討論孟子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由仁義行”和“舜”的重要性頗值得考慮。
三、幾個關聯問題
說孔子與周公統一于“仁且智”,爭議相對不大,而要說孟子與舜統一于“由仁義行”就有不少問題,雖然前面對“舜”與“由仁義行”有所論述,但相關問題仍需要解釋一下,此處以孔子、墨子、大禹與舜的關聯為角度來進行些比較,希望方家指教。
(一)最大的疑惑是孟子也曾稱贊孔子、并以私淑弟子自居,如何合理處理孔子與舜在孟子思想中的地位
孔子是儒學的實際創立者,孟子是儒學重鎮,對孔子的稱贊、推崇自然很多、很明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稱孔子“圣之時”、“集大成”、“金聲玉振”,自稱“乃所愿則學孔子”、以私淑弟子自居(加上宰我的“賢于堯舜”、子貢的“生民未有”、有若的“出類拔萃”),可以看出孔子在弟子(包括孟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弟子(包括孟子)對孔子的稱贊也是發自肺腑的,這些對于維護孔子形象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到《孟子》中諸多對孔子稱贊的同時,也可細究一下:對孔子的一部分稱贊直接來自于孔子親傳弟子,如子貢的“生民未有”、如有若的“出類拔萃”,孟子對“生民未有”表示了認可,對宰我的“賢于堯舜”能否贊成就值得懷疑?換一提問,孟子是否會認可孔子“賢于堯舜”的說法?換一角度,孟子對孔子進行稱贊是把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進行比較,認為孔子高于他們;然而,如果把孔子與舜進行比較,孟子還會認為孔子高于舜嗎?這雖然不是直接出現的問題、而是間接推出來的問題,但對于這個新問題,恐怕會讓孟子很為難。
另外,舜在孔孟這里的評價雖然都不低,但孔孟對舜的評價內容并不盡相同。在孔子那里,舜被稱為“有天下”、“無為而治”,但孔子基本沒有提到過舜的孝、并且孔子還兩次說過“堯舜其猶病諸”!即孔子認為在“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和“修己以安百姓”上堯舜做得可能還有些不夠,因此在“圣”上多少有些問題;而在孟子這里,舜涉及到諸多方面、在孝上是大孝至孝、是圣人(“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是完美無缺的。在次數上,據楊伯峻《論語譯注》統計,《孟子》中舜出現的次數是97次,孔子才81次。在結構上,“堯舜之道”、“堯舜之世”、“堯舜之仁”、“堯舜之民”、“堯舜之治”、“堯舜之澤”、“堯舜之知”等在《孟子》中屢屢可見,而有關孔子的表達則要少很多。在問題上,孟子不但講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而且在其它方面如人性平等上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在人性差等上講“堯舜之道不遍愛人,急親、賢”,在義利上讓舜與盜跖比較,在家國一致時舜自然是孝子加天子,在家國不一致時讓舜“樂而忘天下”,如此等等,我們固然不能說孟子不提孔子,但在如此眾多的重要的問題上孟子多是讓舜來代言,這是不難看到的;孟子有時也讓孔子來為他代言(如仁政、王道),但在涉及問題的廣度和問題的重要性上與舜相比是有明顯差距的。孟子對孔子與舜都有所稱贊,如果讓孟子選擇兩個理想人物,應該是孔子與舜;但如果要優選、只選一個作為孟子“最理想”的人物,無論是涉及的廣度、還是推崇的程度,很可能孔子就要讓位于舜了。
(二)墨子重禹與孟子重舜
孟墨對立、孟子辟墨,眾所周知。墨家倡“兼相愛”,希望“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孟子則講“堯舜之道不遍愛人”;墨家講“交相利”、以為“義,利也”,而孟子開篇就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還讓舜與盜跖進行善與利的比較;墨家講“三患”、看到現實利益對于人的重要性,孟子則講“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墨子講“禹兼”、相對突出了大禹,孟子就講舜孝、相對突出了大舜。從寬泛角度可以說,儒墨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比較推崇,但相對而言,墨子突出大禹、孟子突出大舜是比較明顯的。就孟子而言,孟子相對突出舜這種做法,很難說直接來自于孔子,恐怕主要應來自于對立學派的墨家對大禹的推崇;墨家相對推崇大禹,作為對立的學派,直觀上就很難延續對立學派的基本立場,而是推陳出新、樹立了一個新形象,并且在樹立的同時也進行了些論證、辯護、補充的工作,使得舜在孟子這里的形象既高大又完美。也可以看出,舜的突出很可能主要是為了與墨家重禹相區別,而主要不是與孔子進行比較;在孟子這里,舜的突出也就不存在對孔子故意貶低的問題,抬高舜是學派對立的需要、推崇孔子是儒學自身的需要,在孟子這里,兩種角度都是必需的。
(三)孔孟對禹“仁”與“智”的態度
孔孟對禹都比較重視,但重視程度有些不同。孔子對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十分贊賞,因而兩次稱“禹,吾無間然矣”。按照孔子“克己復禮為仁”的結構,孔子很有可能會給予大禹以“仁”的稱號。而在《孟子》這里,禹的基本稱號卻是“智”:“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寬泛說來,智與仁都各有特色、都很重要;但細致說來,智低于仁、稱某人是“智者”相對就不如稱某人是“仁者”更具有積極含義。“智者樂水”、水與智相通,在孟子這里稱禹為“智者”是很有可能的,而禹在孟子這里能否被稱為“仁者”恐怕就成了問題:在孟子這里,“仁之于父子”,仁涉及家庭、涉及孝道,舜是孝子、甚至為了家可以不顧國,而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看來沒有直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禹的行為當然有重要意義,但與孟子(舜)高度重孝的結構里顯然有些不協調、不統一。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墨子講“兼即仁”,禹的行為在孔子和墨子那里很可能會獲得“仁”的稱號,但在孟子這里要想獲得“仁”的稱號可能性就不大。孔孟對禹的評價差異還表現在,如在《論語·泰伯》有句孔子共同稱贊舜與禹的話:“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而在《孟子·滕文公(上)》就沒有了禹,變成了孔子只稱贊舜:“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可以說在《孟子》中的確存在對禹的故意忽略。這種對禹的故意忽略不太符合孔子意愿,但對禹的忽略卻十分有利于孟子對舜稱贊的需要;如此在孟子這里,禹的地位相對降低了,舜的地位就相對突出了。對于智,孔孟也有比較重視的一面,如孔子講“智者樂水”、如智是孟子性善四端之一;智通賢,孔子講“舉賢才”、孟子也講專家治國。另一方面,孔孟也有對智消極面的提及,在孔子那里,“仁且智”固然體現了仁與智結合、且仁優于智的可能,但也存在著仁與智分離、智而不仁(及仁而不智)的可能,這種脫離了仁指導的智不但不有利于仁、反而經常會害仁,如此就應對智采取審慎的態度。在道家老子那里則公開對智(或賢)進行了批評:“不尚賢,使民不爭。”“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墨子則極力提倡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因此不管是繼承孔子、借鑒老子,還是對抗墨子,孟子對智(或賢)都會有自己的獨特立場:既講“信賢”又講“慎賢”。“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對智(賢)的這種復雜態度表明,在孟子這里,智雖然重要、有一定地位,但不會是核心詞匯、不會居于首要位置;這也許意味著孟子明明知道孔子重視“仁且智”,但孟子的重心還是轉向了“仁義”,隨之理想人物也就出現了相應調整。孟子這種調整不是無的放矢、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綜合時代各種學派、各種立場的結果,具有理論合理性和時代必然性。
就理想人格而言,從仁智到仁義(或由“仁且智”到“由仁義行”)的轉變根本上是理論及時代問題的展開使然。當然,二者的轉變不簡單表現為截然對立、非此即彼,而是有所繼承、也有所轉折。從繼承的角度,儒學重視道德、關注家庭、呼喚仁政的努力得到了延續;從轉折的角度,孟子對道義論的突出、對家庭的高度重視、對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物的調整都帶有了孟子的印記。從消極意義上說,從仁智轉向仁義,雖然具有了孟子特有立場,這一特有立場雖然具有自己的特色、也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亦是不完美的,如仁義的突出使得道義論得到了系統論證,但對功利論的處理并未盡善盡美,如仁義的提出使得對家庭與國家的重視得到了理論支持,但孟子對家庭與國家不可得兼的處理還并不盡如人意,雖然孟子突出了舜使得孝道的重要性大為突出,但對禹的相對貶低也應看到其局限。從積極意義上說,儒學思想畢竟要不斷發展變化、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有新鮮活力,如從“仁智”轉向“仁義”就是看到了“智”有消極因素而力圖對之有所解決,雖然解決也未必盡善盡美,但意識到問題并力圖解決就多少有些進步;“仁智”與“仁義”,既有變化出新、也有互通交融,如“仁智”影響下有“德才兼備”、“做人做學問”等表達,“仁義”影響下有“仁至義盡”、“大仁大義”等表達,它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有交融,共同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就理想人物而言,理想人格上從仁智到仁義的轉變就表現為理想人物上從周孔到孔孟的轉變。可以說,時代的變化、問題的轉向必然帶來理想人物的變遷,這種變遷具有一定必然性,只是這種理論上的必然如何在現實中得以實現、新舊理想人物在變遷的同時是否還有新舊交融的可能等,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就儒學理想人物而言,在唐代中期以前,周孔并稱比較普遍,但在唐宋之后隨著孟子地位的上升,孔孟并稱越來越成為共識。以韓愈為例,其著作中既有多次周孔并稱、又有孔孟并稱:“孔子傳之孟軻”,韓愈講孔子把思想傳給了孟子,這為孔孟并稱提供了理論可能,并且韓愈就有把孔孟(“丘軻”)放在一起的表達。如“柄任儒術崇丘軻”。對于儒學理想人物從周孔到孔孟的轉承,從消極角度上說,孔子、周公、孟子、舜,諸多人物各有特點、各有側重,如何體現一貫性不易掌握;現實人物都有局限,如何合理突出人物優點及合理解釋其缺點以使其成為“理想”并非易事。從積極意義上說,儒學不是抽象的理論教條、不是靜止的死水一潭,而是本身就含有不同方面內容,不同人物也有不同側重,時代還有不同需要,從周孔到孔孟、從仁智到仁義,理想人物及理想人格的次第展開就使得儒學的不同人物得以豐富,儒學的不同內容得到深化,時代問題也得到解決,從而使儒學呈現出多維互動的發展態勢。
[1]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孟子[M].北京:中華書局,1999.
[3]老子[M].北京:中華書局,1999.
[4]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朱熹.四書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韓愈.韓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萬光軍.孟子由仁義行發微[J].國學研究,2010,(26).
[8]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9]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0]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1]戴明揚.嵇康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