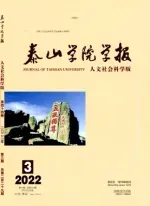萬里在推動農村改革中的政治智慧
郭德宏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091)
萬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帶頭人和卓越領導者,早已是人們的共識,很多論著對此已經加以論述①。他之所以能這么做,除了正確的思想路線,處處從實際出發的務實精神,群眾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大改革家的氣魄和膽識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對于這個方面,一直論述不多,只有趙樹凱的《萬里與農村改革中的“政治”》[1]一文,談到了這個問題。下面,就談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一、要認清什么才是“好的政治”、“最大的政治”
政治,是誰也離不開,但很少有人能說清,每個人都時常感到困惑的問題。上個世紀40年代末,毛澤東有一次問他的秘書田家英:什么叫政治?聰明睿智的田家英竟沒有答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對他說,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令敵人越來越少,令同志越來越多[2]。在與敵人生死搏斗的革命年代,毛澤東的回答當然是正確的。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和中外政治學家也都曾作過各種各樣的解釋,下過各種各樣的定義。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人們心中的“政治”似乎只剩下兩條:一是是不是符合領導人的指示;二是是不是符合領導人提出的某些理論、原則。而正是這兩條,不知束縛了多少人的手腳和創造精神,甚至使無數人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萬里1977年6月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后,也碰到了這個棘手的問題,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阻力。1978年安徽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大旱,廣大農民生活更加困難。為了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萬里支持一些災害嚴重的地方采取“借地度荒”、“包工到組”、“包產到戶”等辦法。可是,這些措施受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對,并被扣上種種嚇人的政治大帽子。為了破除這些政治上的阻力,萬里對政治做出了新的解釋。
首先,以民生為標準,把政治分為“好的政治”和“壞的政治”。1978年秋,在一次省委座談會上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時,有人說那里的農民并不是因為生活困難,而是因為有討飯的“習慣”。萬里氣憤地指出:“胡說!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么習慣?講這種話的人立場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他還會去討飯。”“共產黨不代表人民利益、不關心人民生活,算什么共產黨?要你這個黨干什么?哪個擁護你?我就不擁護那種讓人要飯、餓死人的黨。”“我們共產黨人怎么可以不關心群眾的吃飯問題呢?誰不解決群眾吃飯問題,誰就會垮臺。”“我們說共產主義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褲子,吃不上飯,老百姓去不去呢?”他反復地強調,“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3]
其次,明確指出四個現代化建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1978年秋他在省委座談會上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時,已經明確指出這個問題,他說:“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4]1979年12月25日,他在安徽省人代會上關于農業問題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基礎。只有把生產搞好了,改善了人民生活,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更好地發展其他事業。這兩年我們始終把恢復和發展生產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堅持以生產為中心。這樣做,順民心,合民意,對我省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許多同志在實踐中體會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確實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國家的鞏固,社會的安定,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終都取決于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取決于生產的發展。”[5]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萬里講的都是一些非常簡單的生活常識,從群眾要吃飯,要生活,闡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什么才是最大的政治,從而顛覆了那些政治上的大道理,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的正當性建立在了現實生活層面上。“可以說,這是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安徽農村改革突破的理論基礎”。同時,這也是“關于農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動員”,以生活常識啟動了思想的解放。[6]
如果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鄧小平等人已經提了出來,以民生為標準,把政治區分為“好的政治”和“壞的政治”,則是萬里首次提出的。這種區分,確實打破了那種對政治的空泛概念,使人們知道政治有好壞之分,而區分其好壞的標準,不是領導人的意見和他們提出的某些理論、原則,而是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也就是要以民生為根本標準。這個標準,和生產力標準、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等理論、原則完全是一致的,對于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今天和以后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要正確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在傳統的意識形態中,政治卻可以脫離經濟,經濟反過來要為它服務。一些人反對和指責萬里在安徽進行的改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搞清楚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為了破除政治上的阻力,萬里1980年7月28日在總結30年的教訓時,指出過去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正確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他說:“馬克思說過,經濟是基礎,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就會促進生產的發展;不適應,就會阻礙生產的發展。多少年來,只抓‘政治’,不講經濟,不斷搞‘階級斗爭’,搞‘窮過渡’,批‘唯生產力論’。什么‘大批促大干’,成天割‘資本主義尾巴’。哪有那么多資本主義尾巴!由于這些錯誤的方針,經濟工作、科研工作一直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環境來保證。……什么‘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政治搞好了,經濟自然會上去’,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權利放在第一位,這叫不叫政治?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7]
這樣,萬里就清楚地闡述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正確地說明經濟才是最根本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民主權利才是第一位的,政治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為提高人民的生活,增強人民的民主權利服務,而不能妨礙經濟建設,不能妨害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民主權利,從而抽掉了那些不顧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空頭政治”、“壞的政治”的立腳點,進一步為農村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石。
三、要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但是習慣于把自己確定的某些原則、做法認定是社會主義的,而把不同于這些原則、做法的東西,不管是不是有利于生產,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統統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是要不得的。因此,是不是搞所謂的社會主義,成為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原則,也成為加在人們頭上的一個緊箍咒。萬里在推行農村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了這樣的指責和非難,認為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從而使很多人對這些改革措施產生疑慮,甚至望而卻步。為了破除這個緊箍咒,萬里從幾個方面闡述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
首先,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讓人民富裕起來,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1978年秋,他在省委座談會上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時就說:“社會主義還要飯,那叫什么社會主義,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還這么窮,社會主義優越性哪里去了。無產階級是因為受窮才革命,革命不是為了受窮,要是為了受窮,還革命干什么?我們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來換取‘社會主義’,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絕不是讓人民挨餓受窮,而是讓人民活得更美好。”[8]
1979年6月5日,他在定遠縣藕塘區和風陽縣調查時的談話中再次指出:“農民是注重實際的,社會主義好不好?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就好;說得再好,生活天天下降,什么主義都不好。只有能增加生產,對國家多貢獻,集體經濟壯大,群眾收入增加,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看過鳳陽一個生產隊的材料,解放三十年了還不如解放初期。如果所有的隊都這個樣子,共產黨領導三十年了還是貧窮,那么社會主義還有什么優越性呢?這個問題是個大問題。黨委一定要千方百計把生產搞上去,讓群眾生活富裕起來。”[9]
其次,指出不能按收入的多少來劃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應該使群眾生活改善得越快越好。
1979年12月25日,他在安徽省人代會上關于農業問題的講話中,就針對有些干部看到社員收入多了一點,擔心“資本主義抬頭”,會“削弱集體經濟”,會“兩極分化”的情況,闡明了這個問題,他說: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問題兩個文件所規定的各項政策,是符合廣大農民群眾利益的,是同目前農業生產力的水平相適應的,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但是,極左思想的流毒還沒有肅清,有些干部看到社員收入多了一點,就擔心“資本主義抬頭”,會“削弱集體經濟”,會“兩極分化”,等等。這是不對的。“是不是資本主義,不能按收入的多少來劃分”。“林彪、‘四人幫’搞的是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而不是我們黨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只要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收入越多越好,群眾生活改善得越快越好,這樣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只能用辦好集體經濟,使農民從集體經濟的發展中得到實際利益的辦法,來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用損害農民利益的辦法,來強制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10]
從1978年開始,鄧小平就在考慮怎么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萬里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論述,與鄧小平的探索是同時進行的,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指明社會主義的本質,但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正如有的評論所說:萬里所進行的論證雖然不是“引經據典的嚴密論證”,而是“樸素的論證”,但這是“最有力量的論證”,是“最高層次的理論論證”,它“解決了根本的理論問題”,從而打破了那種“用自己建構出來的‘社會主義’理念來裁奪生活”,“包括規制人民群眾的行為和活動”的荒唐做法。[10]這在當時極左思潮還很濃厚的情況下,確實是振聾發聵的,從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農村改革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
四、充分肯定農業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的
由于“左”的思想的長期影響和禁錮,很多人認為只有集體干活、堅持三級所有等等原則,才是社會主義的,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的,從而使農業生產責任制在推行過程中遇到重重阻力。為了接觸這些思想禁錮,破除這些阻力,萬里不僅從理論上作了闡明,而且針對一些人指責和非難,對一些關于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具體問題做出了明確的回答,指出幾個人干活,幾級核算,都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標準,充分肯定農業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的。
1979年6月5日,他在定遠縣藕塘區和風陽縣調查時的談話中,針對有人認為包產到組不符合社會主義的三級核算,是搞資本主義的指責,明確指出:“有人不承認包產到組是四級核算,我認為包產到組實際是四級核算,多一級就不是社會主義了?只要能增產,五級核算也可以。每家都核算才好呢!就怕不核算,不核算,平均主義,糟糕得很。你們可以開個農民座談會,討論一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如何發財致富得快些的辦法。”[11]1979年12月25日,他在安徽省人代會上關于農業問題的講話中,針對有的干部看到作業組劃小了,就擔心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的情況,再次指出“這是不對的。是不是資本主義,不能按收入的多少來劃分,也不能按勞動組織的大小來劃分”。[12]1980年7月28日,他在關于抓好農業區劃工作的講話中,又針對只有集體干活才是社會主義,個人干活就是資本主義的說法,進一步指出:“有一種說法:‘個人干活就是資本主義,集體干活就是社會主義’。不能這樣簡單地劃分。集體生產也可以少數幾個人在一起干,適合單獨操作的農活就得個人干,這不是資本主義。要敢于實踐,肅清極左流毒,沖破精神枷鎖。”他認為,“根據作物情況,可以包產到人、到組,聯產計酬,也可以獎勵到人、到組。所有制不變,出不了什么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有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包產到戶不同于分田單干。如果說分田單干意味著集體經濟瓦解,退到農民個體所有和個體經營的狀況,那么,包產到戶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它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13]
正是在萬里等人的推動下,中共中央1982年1月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14]至此,家庭承包等責任制終于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承認,取得政治上的決定性勝利,從而迅速推廣到全國農村。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萬里在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過程中體現出的政治智慧,對政治的有關論述,不僅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改革的進行,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注 釋]
①見吳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新道路——<萬里文選>讀后》,《人民日報》1995年11月2日;吳象《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步——讀<萬里文選>關于安徽農村改革部分》,《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劉以順《萬里和安徽的“大包干”》,《黨史縱覽》1996年第3期;劉明鋼《東風第一枝——萬里與安徽農村改革》,《黨史天地》1997年第9期;劉秀蘭《萬里抓農村改革的四個第一》,《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3期;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安徽農村改革實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溫雪勇《沖破堅冰——萬里與中國農村改革》,《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吳象《胡耀邦與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炎黃春秋》2001年第7期;安熠輝《改革風云中的萬里與鄧小平》,《黨史博采》2002年第10期;安熠輝《萬里——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福建黨史月刊》2003年第4期;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張廣友、丁龍嘉《萬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王立《萬里與農村改革》,《黨員文摘》2007年第4期;聶皖輝《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的智慧和膽略》,《黨史縱覽》2008年第9期;黃德雙《萬里農村改革思想探析》,2008年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黃禹康《安徽原省委書記萬里拉開農村改革序幕》,《老人世界》2009年第1期;先安順《論萬里安徽時期農村改革思想的理論貢獻》,《中共銅仁地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2期;丁龍嘉《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的三大貢獻》,《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先安順《論萬里安徽時期農村改革思想形成的基本歷程》,《中共銅仁地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5期;何健雯、趙慶海《1978年前后萬里農村改革精神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9期,等。
[1][3][4][6][8][10]趙樹凱.萬里與農村改革中的“政治”[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2).
[2]丁學良口述.人的解放:改革開放的第一步[N].南方周末,2008-12-24.
[5][7][9][11][12][13]萬里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三農”工作中的十個一號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