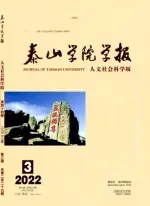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生存環境與策略
趙強
(泰山學院 漢語言文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大多舉步維艱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998年是文學期刊運行最為艱難的一年,許多著名的文學期刊在這一年宣布停刊。《昆侖》、《漓江》、《小說》等雜志相繼停刊,在業界被稱為“天鵝之死”。其他尚未停刊的期刊也在通過改版、改名在苦苦支撐,但其生存依然步步荊棘、四處碰壁。與許多全國性的期刊相比,很多省級文學期刊則更是難以為繼。就以山東為例,當其興盛之時幾乎各地市都有發行量較大的文學期刊,而山東作協主辦的《山東文學》和《時代文學》更是影響巨大,不僅銷量可觀,而且在整個山東當代文學乃至全國文學的發展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推出了像張煒、矯健、尤鳳偉、趙德發、劉玉堂這樣具有全國影響的作家,也有李存葆、王潤滋等各具特色的作家。一時之間文壇魯軍可與當時的陜軍、湘軍相抗衡。而這一切無不與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的發展和繁榮有巨大的關系。這些作家們最初的成長和發表陣地幾乎都是山東本土的文學期刊。他們在印證山東當代文學繁榮的同時也見證了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的繁榮與發展。但很快隨著全國文學期刊生存艱難的大趨勢的到來,山東文學期刊也迅速凋零。很多地市級期刊因經費困難而停刊(后來有些地市在拉到一定贊助時就不定期地出一期,文學期刊變成了文學不定期刊),而原先影響較大的幾份刊物也被讀者越來越疏遠。隨著文學期刊的萎縮,其影響也逐漸減小,其推介作家的能力也自然弱化,反過來又自然影響到其發行和生存。和全國的大環境一樣,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的生存也面臨著兩個關鍵的要素,一是大眾文化背景下文化產業化的生存環境;二是大眾文化背景下文學邊緣化的事實處境。這是不管從業者喜歡不喜歡、愿意不愿意都必須接受的事實。因此,要想更好地尋找生存的策略和機會,首先必須要面對這樣的生存環境,理性地對待這種生存環境,要正視而非逃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尋找到生存之道。
一、生存環境:挑戰與機遇并存
大眾文化背景下文化產業化的生存語境是文學期刊必須要面對的挑戰。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文化現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市場化、世俗化以及它的文化形態——大眾消費文化的興起成為一種普泛性的社會文化現象。有關大眾文化的定義有多種,其中陶東風等編著的《大眾文化教程》對此定義比較簡單明了。他認為:“我們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范疇,它主要是指隨著現代大眾社會興起而形成的,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進行大批量文化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大眾文化具有多種特點和功能,如商業性、娛樂化、文本的模式化和復制性等。大眾文化一般包括流行小說、商業娛樂性的影視、流行音樂、廣告文化等形態。”[1](P18)這個大眾文化的定義中已經包含著重要的產業化信息。如大工業生產,大眾傳媒、批量化、商業性娛樂化等都預示著經濟因素的存在。因此緊隨而至的文化產業化也就成為一種必然。1980年初,歐洲會議所屬的文化合作委員會首次組織專門會議,召集學者、企業家、政府官員共同探討“文化產業”的涵義、政治和經濟背景等問題。“文化產業”作為專有名詞從此正式與其大眾文化母體脫離,成為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文化-經濟”類型。這一概念雖是借自西方,但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又有著具體的內涵。正如陶東風等人所指出的“文化產業所包含的幾個基本要素:第一,文化產業是以文化內容作為獲取商業價值的手段的,這里的文化,不僅僅是已有的文化知識,它更強調的是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或想法,即以富有創意為特征;第二,文化產業以服務為目的,這里的服務不僅僅是提供商品的形式,更提供商品所附帶的文化內涵,向消費者提供精神性的服務;第三,文化產業的發展也與技術密切相關,與商業相連,這是其工業化商品化的體現。”[1](P20)王穎在《2005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綜述》里也指出:“對文化商業價值的認同,使文化成為產業;對文化服務性的強調,使文化產業更多地被歸入服務業的范疇;對文化創造性的重視和高新技術的運用,意味著文化產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P183)從以上內涵的界定中,不難看出文化產業的特殊性就在于把傳統上認為純粹精神產品的文化商品化和產業化了。而文學期刊則既具有大眾傳播媒介的一般性,同時也具有當代文學生產載體的特殊性。因此文化產業化的沖擊對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最大的影響就在于其生存方式的改變。眾所周知,從“十七年”一直到80年代初期,文學期刊尤其是由各級作家協會和文聯主辦的純文學刊物,依靠政府撥款維持運轉。即其生存和發展經費都是由政府投入,與其發行量及市場營銷沒有任何關系。而其在體制上屬于事業型單位,特別是一些省級文學期刊,他們的人員配置是服從于上級主管部門,期刊編輯部本身在人員配置上沒有多大權力,因此期刊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也無法得到有力保障,更無法接受市場的檢驗。而當代文學期刊生存艱難的出現主要就出現在經費來源的改變上,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國際文化產業的興盛,政府對于傳統的自己供養的文學期刊不可能繼續維系,因為政府的職能也在發生變化,將期刊及文化出版業推向市場就是一種必然選擇。當政府的經費供給結束之后,一個文學期刊要想生存就必須靠自己的實力在市場上養活自己。就是說曾經以清高精英自居的文學期刊(因為很多文學期刊編輯者是看不起哪些所謂的綜合性期刊如《女友》、《家庭》、《讀者文摘》、《特別關注》等)突然間被市場化了,淪落到和上述他們認為品味和格調都有差距的那些刊物共同爭奪市場的地步,更加可悲的是居然沒有競爭過那些期刊,一本小小的《遼寧青年》的發行量,都讓許多文學大刊汗顏。因此眾多文學期刊從業者感覺特別失落,這也是文學期刊產業化轉型的必然。離開了過去的衣食無憂一變為自己去跑發行,找贊助和廣告,出現不適應是正常的。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其中也包含著積極的因素,使文學期刊終于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架子,開始考慮市場和讀者的需求,真正具有了市場意識和讀者意識,這對文學期刊的發展自然是有積極作用的。
另一方面則是從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層面看,文學的邊緣化已經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賴大仁認為:“‘文學邊緣化’實質是文學性的危機,即:在市場化與消費主義的策動下,雖然文學的某種形式與名義依然存在,但其‘文學性’已經在整體性的娛樂化中被消解或轉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學的危機,是‘文學性’的危機,是‘閱讀’的危機。當‘讀者’變成了‘觀眾’,‘閱讀’轉化為‘觀看’,‘審美’蛻變為‘消費’時,也就意味著‘讀者死了’,閱讀消亡了,于是真正的文學也終結了。”[3](P155)雖然這樣的表述有點絕對和悲觀,但的確也道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學和文學期刊的輝煌讓很多從業者的回憶充滿了甜蜜和陶醉。當時,普通文學期刊發行量有四五十萬份,知名刊物的讀者更是數以百萬計。作家能夠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這樣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可謂“一舉成名天下聞”。不但作品廣為傳頌,而且也成為作家名氣和地位的象征。但是現在還有多少人關注文學和文學期刊呢?著名作家莫言也說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商業社會,文學作為代言人的角色也逐漸變得模糊,甚至完全消失。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多種傳播媒體層出不窮,娛樂方式也變化多樣,再加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和日常生活中政治的淡化,使得小說變得脫離社會,它遠遠不及舞蹈、音樂和其它藝術形式所引起的反響。一篇小說在全國引起轟動的時代已經遠去了。雖然也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作品引起一陣騷動,但那只不過是流行或消費的問題,和它本身的文學價值沒多大關系,跟一種新樣式的衣服或舞蹈引起一陣流行風是一樣的,文學不再為社會負責或負有為人民說話的責任。我覺得這種情況佷正常。就像在法國產生的‘新小說’一樣,那些作家只是把小說當作藝術品,他們去研究小說的創作,而不考慮它的銷售及社會影響。自然,這樣的結果也導致了閱讀群的縮小。”[4]莫言從文學功能的轉變及作家創作的角度指出了文學邊緣化的事實,作為作家他完全可以不考慮銷售和影響,但被市場化的文學期刊則不能不重點考慮這個問題。加之當代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多媒體共生的傳媒社會。廣播、電視、網絡等便捷的視聽方式、豐富多彩的形式、不斷變幻的視覺效果對紙面閱讀的沖擊是強大的。相當數量的人每天看電視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閱讀時間大為減少,正如楊葵指出的:“雜志與書籍,區別在這里,書是有頭有尾,要你一行一行念;雜志不同,都是翻來翻去,嘩嘩響,很少有人把一本雜志從頭讀到尾……現在奇缺的,不是知識分子,當個知道分子在社會上更吃香。所以網絡就應運而生,它能讓你在最短的時間獲取大量的信息。網絡具有明顯的雜志特點,鼠標滑輪刷刷轉,五湖四海大千世界奔來眼底,拉洋片似的。”[5]這恐怕道出了一般讀者的普遍心態。即便還有讀者愿意在紙質雜志上閱讀,其閱讀對象也發生了變化。相對于閱讀節奏的加快必然對閱讀內容和閱讀習慣有所改變,因此文化快餐式的文摘、選刊更為暢銷就是這樣一個事實,相反的以關注心靈為特長的文學成為時代的棄兒,相應的文學期刊的讀者群就逐漸萎縮,一些知名文學期刊定數的下降,也說明了這一點。《花城》的定數好幾年都沒能超過3萬,《收獲》每期也就10萬份左右。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遍布全國的省級文學期刊就更不用多說了。當然讀者遠離文學的問題,單靠文學期刊的魅力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把讀者重新拉回來的,這是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包括讀者文化層次提升的一個整體工程,非朝夕所能見效。在抱怨文學生產外部環境的同時,文學期刊自身存在的問題也不得不引起足夠的重視。當外部環境的改變無法掌控時,通過對文學期刊自身的改變就成為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革手段。
二、期刊自身:優勢與不足并存
在談到文學期刊的質量問題時,有讀者就說:“我疏遠文學期刊,并不是我不喜歡文學了,也不是更多的娛樂媒體在我心中超過了文學期刊,而是因為我對當時刊登的文學作品看不上眼了,覺得那里大部分作品都是無病呻吟。”[6]真正遠離文學的人,文學期刊拉不回來,但僅有的讀者群如果由于文學期刊自身質量的低下而再次流失,那文學期刊還能靠什么來生存呢?因此必須正視文學期刊自身存在的問題。具體到山東當代文學期刊,其代表是《山東文學》與《時代文學》,但這幾年其發行量、影響度都在逐步下降。其他地市級期刊更不用說。關起門來自己辦刊物是無法發現自己的不足的,只有通過與名刊的比較才能發現自身的不足。當代文學期刊中《人民文學》自然是領航舵手,通過山東文學期刊與同時期《人民文學》的比較,才能發現差距和自己的特色,從而實現對山東主要當代文學期刊的準確定位。
比較一下2001年第6期《人民文學》的目錄和同期的《山東文學》、《時代文學》看其中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從欄目設置看《人民文學》共設有:“留言”、“現場”、“圓桌”、“小說”、“新小說”、“輝煌十八年”、“專欄”、“新散文”、“視聽”、“十二月”、“記憶”、“萬象”、“天下”、“漢詩”共14個欄目,“留言”是讀者和編者交流的欄目。這個欄目在2000年的《人民文學》中就存在,就有讀者就刊物的內容形式提出的意見。如河南永城的吳彥先生寫道:“翻閱改版后的雜志,總的感覺有新意。因為我太喜歡《人民文學》,提三點建議:一、《人民文學》創刊以來莊重、大方的特征和風格不能丟棄;二、增設新欄目固然好,但不要減輕刊發高品位小說的分量;三、插圖不要太多太草率,字體的選用也要講究。”[7]而編輯方接著予以回應:“對于改版后的刊物在內容、版式、插圖等方面的缺陷我們已在11期和12期逐步改進,我們希望明年第一期的雜志能讓你們更加滿意。”[7]“留言”也可以成為編輯推介自己期刊的陣地,如:“明年第一期我們將推出史鐵生的小說新作,還將以較大篇幅推出《2001年的愛情》專輯,我們相信明年將是更精彩的一年,我們期待著與你們明年再見。”[7]因此這個欄目的設立表明了編者對讀者意見的重視,這首先是一種姿態,其次才是一種策略。而《現場》欄目更是以直面當下現實為己任,作者寧小齡曾多次關注百姓生活中最具現場感的文學事件,比如北京的的哥的姐的生活以及本期刊發的關于民間博彩市場的起伏故事,具有真正的現場感。而小說則主打名家精品,本期刊發王祥夫一組小說,而“新小說”重在推出文學新人。其他欄目也多為名家訪談、隨筆回憶,如韓石山、崔衛平、陳祖芬等皆為名家名品,顯示出《人民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第一期刊的規格和品味。《時代文學》2001年第6期共設有“時代廣場”、“中篇擷英”、“短篇選萃”、“書齋探幽”、“時代風采”、“時代詩壇”、“名家側影”、“小小說世界”等8個欄目,其中的“中篇擷英”、“短篇選萃”、“小小說世界”兼顧到不同的小說類型,可謂面面俱到,但缺乏特色。“時代廣場”帶有反映當下時代的意識,本期刊發的《東方蘑菇云騰空之迷》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反映了中國核事業的發展。作品有一定分量,但時效性不強,且屬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而《人民文學》所表現的的哥的姐,還有那些靠賣身養活自己的底層女性的喜怒哀樂,都是百姓身邊的人和事,其親和力、影響力自不待言。在中篇小說作品中,只有胡學文的《魚兒為什么浮出水面》算小有名氣,其他如汪淏、顧冰、李紀釗等都非名家,當然地方文學期刊要推出新人、本土作家,但是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名家名作作為刊物的支撐,那么刊物就容易成為新作家的試驗田,其藝術水準就不能達到較高的水平。“書齋探幽”作為隨筆欄目除李洱外沒有其他大家。只有“名家側影集”中圍繞著多產作家范小青,組織了一批其身邊的親人及相關名家對其進行集中推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其推介的作家還是江蘇作家,地域特色不顯。其他欄目比較泛泛,缺乏創新和品味。同期的《山東文學》小說中有段玉芝的《摯愛無言》、凌可新的《陽光故事》、劉慶祥的《裸體問題》等,但均缺乏名家之作。本期山東文學卻刊發了多篇紀實性的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如許晨的《巍巍“泰山”——山東魯能泰山足球隊奪冠紀實》;王雷的《走出歷史的驚蜇期——劉寶斌特寫》;趙進斌的《祥飛之路——記山東省富民興魯勞動獎章獲得者、山東省十大青年企業家、山東祥飛工業集團總經理費守祥》;王昌黎的《鏗鏘的腳步——山東省諸城市公安局強警興局之路紀實》。從題目就能看出幾乎全是帶有宣傳性質的有償報告文學。其他都是本省作者的游記、散文等,拿到這樣一本刊物能不讓真心喜歡文學的讀者寒心嗎?誰會花錢去買一本這樣的文學期刊,里面還有文學嗎?文學期刊要生存,需要企業贊助,需要廣告宣傳但是文學期刊文學的特色不能丟,不能為活著而活著。《人民文學》也給茅臺集團寫報告文學,但其分量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疇內,加之這樣的報告文學也多是名家筆墨,就更避免了赤裸裸的金錢氣息。因此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看出山東主要文學期刊與《人民文學》這樣的國內名刊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讀者意識不足。期刊編輯者只盯著作家和能給錢的贊助商,忘記了作為一個文學期刊其最根本的是大量普通而平凡的讀者。《人民文學》這樣的大刊,都可以放下架子和讀者平等交流,把刊物的編輯理念展示給讀者。如2000年第10期編者的話:“這是第10期。當你翻開它的時候,在我們心里、在想象中,我們注視著你年長或年輕的面孔:你喜歡嗎?改版之后的《人民文學》仍然屬于你的雜志嗎?從上半年起,我們就籌劃改版。在雜志社的每次討論和爭辯中,總有一個不在場的聲音指引著我們,那是讀者的聲音。你們的喜悅和困惑、鼓勵和期望,是我們對雜志作出調整和變動的根本依據。”[8]當編輯在討論改版時,始終在傾聽著那個不在場的讀者的聲音,這就是刊物的讀者意識。一個不把普通讀者放在心中只考慮刊物怎么生存的編輯是注定被讀者拋棄的。遺憾的是我們在《時代文學》和《山東文學》上我們都沒有找到任何和讀者相互交流的文字。在《時代文學》2001年第6期上只有一個通知性的文字:《本刊再獲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只有沾沾自喜地自我夸耀,沒有任何感謝讀者支持的話語,這就是讀者意識的缺失。
其次是品牌意識不強,缺乏特色。《人民文學》的“留言”、“現場”、“記憶”等都已經形成一種品牌,每一個品牌都有其特定的讀者群。“現場”以其時效、真實贏得讀者,而“記憶”則以其對過去的點滴追述中,喚起一些老讀者對那個年代的溫馨回憶和共鳴。而《時代文學》、《山東文學》幾乎沒有具有特色的品牌欄目。其實欄目的品牌化,這也是現代傳媒發展的必然,對傳播受眾的精細分類和定位是當代傳媒發展的新趨勢。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為受眾提供服務。如央視的《同一首歌》就是用音樂懷舊,其收視人群是相對固定的對那個年代的歌曲有共鳴的人。文學期刊也應該如此。作為山東的文學期刊卻沒有一個反映齊魯特色的品牌欄目,缺乏特色就是必然的。
再次是缺乏名家戰略,沒有解決好推新人與堅持高品味的關系。《人民文學》的各欄目作者,包括小說作者都是在文壇或知識界有相當名氣的作家或學者。推文學新人的欄目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名家名作至少保證了刊物的高質量(當然不是所有名家的作品都是名作,這就需要編輯的把關)。當然因為刊物級別的差異,名家自然愿意把自己的優秀之作交給《人民文學》這樣的大刊物,但大刊物的容量畢竟是有限的,省級文學刊物并不是沒有機會,關鍵是編輯不能坐在編輯部里擺架子、打電話,應該走出去去找名家約稿。好的編輯總能組織了來好的稿子。有的編輯在觀念上并不認可名家,認為你已經功成名就了,我再發你的稿子只給你錦上添花罷了,還要去求稿,殊不知如果沒有名作支持刊物,如果編輯一份沒有讀者的刊物,你把版面都留給新人了(說不定還有很多不夠發表水平的新人),沒有讀者去閱讀,你的新人永遠都是新人。讀者的認可是最重要的,而這一切都必須有高質量的作品支撐。在此基礎上才能有計劃地推出文學新人。完成對新人的培養目標和計劃。
另外,相對于《人民文學》而言,山東的兩份文學期刊在宣傳上缺乏意識、手段和力度。比如《人民文學》在2000年的改版舉措,除了刊物自身在期刊的發行中不斷宣傳之外,還充分運用了大量高規格的報紙的宣傳。當時《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學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等許多國家級大報都報道了《人民文學》改版的消息。《人民日報》指出:“《人民文學》力求把堅定的文化承擔和對讀者的尊重細致地結合起來,在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寫作和閱讀中,包容創新和創造,理想和激情。”[7]《北京晚報》指出:“雖然文學期刊改版是家常便飯,但最近《人民文學》的又一次改版,依然被圈內人士稱為一次革命性之舉。此次改版,是一次面向市場、面向讀者、面向變化了的文化環境的選擇。”[7]可見《人民文學》這次改版宣傳力度之大。但山東的這類文學期刊則沒有在山東省內的主要報紙上進行相應的宣傳,其影響自然有限。
三、生存策略:特色與多元共舉
面對文學期刊生存市場化的環境,面對文學邊緣化的事實,面對山東文學期刊與國家級文學期刊的巨大差距,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的生存之路何在?這是必須要面對也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面對文學期刊的市場化生存,單靠文學期刊自身的魅力是不足以度過難關的,依賴政府的投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去完成一種文化資本在金融資本市場的運作,這是國家體制改革和研究者需要做出的回答。文學邊緣化的事實,也不是某一個文學期刊通過改版就能完成的。那只能是就現有的文學讀者做出文學期刊自身的努力。或許正如莫言所說的讓文學徹底回到文學自身,文學自身的魅力必然不會讓文學消亡,自然也不會讓發表文學作品的載體——文學期刊徹底消亡,當務之急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大做強,先把自己變好,再等待時機完成真正的涅槃。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的自身改變,必須要堅持特色與多元并舉,具體生存策略如下。
首先要確立讀者為中心的意識。建立良好的編、寫、讀信息通道。可通過隨刊物附送的問卷調查,了解讀者想讀到什么樣的文學作品,他們真正的閱讀需求是什么,他們對于我們自己的文學期刊有什么建議和要求。充分調動讀者的參與意識與參與熱情,謀求改版以滿足讀者的需求。并將讀者信息溝通設為固定欄目。現代文學發生期的《新青年》就專門設有編輯與讀者的通信欄,每期都有編輯就讀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意見予以公開答復,形成了良好的編讀互動,也為刊物擴大了影響,甚至可以采用商業化手段調動讀者的參與熱情。建立讀者中心的意識和觀念后,具體的操作手段自然會多種多樣。
其次要打造齊魯文化品牌,構建文學山東。山東是齊魯文化的發源地,但山東的文學期刊居然沒有任何打造齊魯文化品牌的意識。以齊魯文化為主題和品牌,固定地長期地發表以齊魯文化為表現和形象塑造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山東當代文學期刊當然的使命。上世紀80年代,王潤茲的《內當家》表現了齊魯兒女的仁義和大度。張煒《古船》中的隨抱樸所體現出的堅韌,《九月寓言》所表現膠東大地特有的民間信念和民間文化,趙德發、劉玉堂對沂蒙大地上所籠罩的齊魯文化都曾淋漓盡致地展現過,但是我們沒有打出齊魯文化的品牌。我們在山東的文學期刊上要以此為總主題和表現域實現山東文學的新的創造,用期刊品牌引導創作,既然《闖關東》能夠構建影視中的山東文化和山東人,作為山東主要的文學期刊為什么不能以構建文學的山東文化與山東人形象呢。這就是特色,作為歷史豐富的齊魯文化不可能孕育不出新的作品與文壇新人。關鍵在于要發揮文學期刊的引導作用,只有立足本土特色,才會走出自己的生存之路。
再次,建立文學作品快評機制,以引導熱點、指導閱讀、培養讀者。長期以來文學作品的發表和批評家的批評總是各自為政,互不相干。作家自以為是,不屑于批評家的批評,批評家堅持自己的獨立,對作家的創作作有意識的忽略。因此就造成大量作品無人評,大量評論脫離創作實際的局面。讀者的閱讀就是盲目的和隨機的,所以文學的關注度持續走低。要想吸引讀者,必須引進評論,最好是有爭議的評論(而不是那種抬轎子式的評論)。在每期發表的文學作品(重要的)后面就附上爭鳴式的評論文章,刊物的發稿總是有提前量,編輯可充分利用山東省內充裕的高校資源,山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都有大量的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每期都可以組織他們對所發作品進行評論,也可刊發有特色的對當期其他名刊所發作品的尖銳大膽的批評,評論占所發作品篇幅的五分之一即可。每期都有熱點和評論,自然會吸引讀者的注意。同時又利用了高校的學術資源,解決了學院派批評脫離作品實際的弊端。
第四,要建立文學期刊組稿編輯發行過程的專業的創意和策劃團隊。在當下這樣一個傳媒時代,文學期刊首先要進入文化消費市場,因此它的市場定位、目標消費人群以及自身在組稿選題策劃方面都要有適應市場變化的專業團隊來負責。具體到山東當代文學期刊,其市場份額自然是立足山東,面向全國兼及海外(主要是港、澳、臺等華人文化區域),同時根據不同時期的消費文化需求調整編輯策略,一旦時機成熟,可以通過自己的策劃,找準市場和文學期刊的結合點,通過某種集束式發表同類型的作品,打出山東文學期刊自己的品牌,從而實現引領文學思潮和市場潮流的可能。1989《鐘山》雜志集中策劃并推出的“新寫實小說”聯展,就相當成功,不但打響了《鐘山》雜志的品牌,同時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樣的創意與策劃就是市場與文化的雙贏,當然這個過程也并非十分簡單,因為此后很多刊物也嘗試過此類的策劃。但是這些兒玩意并沒有獲得文學消費市場和中國當代文學界的認可,因為既沒有找準時代的脈搏也沒有對文學作品的準確理解和定位,而是為策劃而策劃,其失敗也是必然的,因此這個策劃團隊的專業水準是相當重要的,以山東文學期刊的地位和吸引力,組建這樣的團隊有難度,但也必須要嘗試,因為這是文學期刊市場化的必備武器。
最后,應該構建立體宣傳平臺,加強對文學期刊的宣傳力度。從《人民文學》改版時的宣傳力度看。一份文學期刊只是在自己刊物上作宣傳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對本刊所刊發的作品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和推介。對發行量巨大的報紙要予以充分的重視,現代廣告借助大眾傳播媒介對普通讀者的引導和影響作用是相當巨大的。山東當代文學期刊要充分利用山東的《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甚至可以建立相對穩定的宣傳欄目,比如《時代文學》、《山東文學》將要刊發的重要作品,可先在《齊魯晚報》上以摘要或片斷的形式先期與讀者見面,以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也可在媒體上重點推介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形成報紙和文學期刊的定期聯動。其效果值得期待。同時,要注意充分利用網絡媒體,加強對文學期刊辦刊思路及所發作品的宣傳,建立自己的網站,并將每期作品中部分作品設為在線閱讀,以吸引讀者的關注。并可定期設立編輯在線與網友交流,就文學,就刊物本身都可交流,全方位宣傳刊物及作品。從而建立起立體化的宣傳平臺。保證文學期刊的知名度和適當的關注度。
總之,山東當代文學期刊與全國大部分文學期刊一樣,都面臨著文化產業化后的被市場化處境,都不得不面對文學逐漸邊緣化的事實。因此,拋開資本運作的不可操控因素,最關鍵的是改變刊物自身的定位、辦刊思路以及刊發作品的品質,真正提升自己的品味。相信文學雖然邊緣,但并不會消亡,文學期刊自然也不會消亡。山東當代文學期刊更應該認清當前嚴峻的現實,立足本土,打造齊魯文化品牌,加強宣傳,綜合利用山東充裕的文化資源、真正為山東當代文學期刊找出一條合適的生存之路。
[1]陶東風.大眾文化教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2]王穎.2005年文化理論研究綜述[J].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06,(4).
[3]賴大仁.圖像化擴張與“文學性”堅守[J].文學評論,2005,(2).
[4]杜特萊.莫言談中國當代文學邊緣化[J].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2).
[5]楊葵.雜志心態[N].深圳商報,2006-06-30.
[6]祝孝成.文學期刊的反思[J].文化觀察,2004,(3).
[7]編者.留言[J].人民文學,2000,(12).
[8]編者.留言[J].人民文學,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