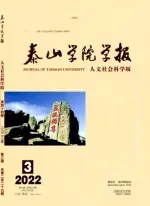2010年魯迅作品研究述略
崔云偉,劉增人
(1.山東藝術學院 藝術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2.青島大學·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中心,山東 青島 266071)
在歷年來的魯迅研究中,有關魯迅作品的研究總是異彩紛呈,創意不斷。本年度的魯迅研究自不例外。筆者在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的基礎上,特意從中概括、梳理出有關魯迅作品研究的幾個景觀。現述評如下,以與學界同仁共同探討。
一、《吶喊》、《彷徨》研究
與《吶喊》研究有關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孔乙己》、《藥》。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1]認為,魯迅的《孔乙己》是對芥川龍之介的《毛利先生》的模仿與創造。魯迅在執筆《孔乙己》之前應該讀過《毛利先生》。魯迅在第一人稱的回憶這種敘事方式,以及由對中年男子輕視轉向產生共鳴的少年心理變化這種故事的基本結構上模仿了《毛利先生》,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與大正時期東京的毛利先生在時空上有很大差別的清末時期小鎮上的孔乙己。指出《孔乙己》的借鑒與模仿源自何處,是這篇文章的出彩之處,但也謹防得出魯迅的文學創作不過如此的結論。魯迅是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但影響歸影響,魯迅的文學創作還是來自自身的真實感受,《孔乙己》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小說。
李宗剛[2]注意到《藥》中一個細節:夏瑜的父親不在場,而華小栓的父親在場,認為夏瑜正是由于父權的缺失才確保了其能夠接受革命理論,并在走向變革社會的實踐中完成了對信仰的以身相許,從而昭示出思想啟蒙和社會變革的希望所在,而華小栓的人生悲劇則主要體現在父權在場對其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抑制與扼殺上。通過如此鮮明的人生對比,魯迅從中彰顯的是以夏瑜為代表的“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從而顯示出相當的思想深度。該文創新之處在于,第一次從父權缺失的角度對《藥》進行解讀,從而賦予這篇小說以一種新的闡釋。這對于理解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父權缺失問題也是大有助益的。
與《彷徨》研究有關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傷逝》、《祝福》。
《傷逝》被公認為是魯迅小說中最復雜、最引起歧義的一篇。李今[3]以獨具特色的敘述學眼光與結構主義視野,指出反諷是《傷逝》的一個結構原則。魯迅是以一種反諷的觀點來觀照和講述涓生與子君故事的。魯迅或者并置其自相矛盾的意見,或者以言行不一、表象和事實的對比構成反諷性事態,使敘述者的講述反而成為嘲諷自己的來源。通過辨析“講述的與被講述的涓生”、“雙重被講述的子君”中隱含作者與涓生敘事的分裂,李今揭示出文本中的兩種聲音、雙重意義,從而突現出《傷逝》的復調特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魯迅所具有的反諷世界觀,從而得出《傷逝》中的反諷并非特例的結論。此外,該文在具體論證過程中,始終浸透著李今在閱讀魯迅作品時的那種獨特、幽微的個人體驗。這也是特別重要的。
顧農[4]對于《祝福》的解讀頗為耐人尋味。他認為《祝福》所寫的事,就在當下,并非清末。證據就是“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這真是一語提醒夢中人。《祝福》中有半幅對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在閱讀時最易匆匆越過,顧農卻從中悟出玄機。指出魯四老爺一方面是講理學的老生,一方面卻經常發火,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此真所謂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該文還頗具現實感。如顧農在批評小說中的“我”時,這樣說:“不是用先進文化去向群眾啟蒙,而是用世俗的見解、傳統的觀念去敷衍塞責,不肯有任何擔當;最后則決心一走了之。實際生活中的‘新黨’,這樣的人很不少。”魯迅筆下對于“新派”知識分子弱點的剖析,也是讀魯迅的人最值得反躬自省的地方。
二、《故事新編》研究
“油滑”是《故事新編》研究中的一個關鍵詞。魯迅對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但近年來的《故事新編》研究卻將之提高到一個全面肯定和高度褒揚的地步。馮光廉[5]認為,從“油滑”來高度評價魯迅的創造力,固然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即因為高度評價“油滑”的創造性,而將《故事新編》的總體成就置于《吶喊》、《彷徨》之上。論者再次重申了他多年之前的一個觀點,即:“就魯迅(自述)語言文字的分量、真實情感的分量看,他對《故事新編》的肯定、欣賞和重視的程度,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在《吶喊》、《彷徨》之上的。”這就需要我們重視對于魯迅創作自述的研究,把握魯迅創作自述中的辯證性和分寸感。論者繼而認為,應該充分認識魯迅后期小說創作所面臨的深重矛盾和危機,從多重矛盾中深入分析魯迅后期《故事新編》的創作成因、思想藝術特點以及價值成就的高度,針對《故事新編》“藝術上的某種不成熟性”展開深入的研究,這對于全面準確地評價這部歷史小說集將大有好處。
《鑄劍》是《故事新編》中的精熟之作。姬志海、李生濱[6]認為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去解讀《鑄劍》似乎更為契合。《鑄劍》可以說是魯迅結合了當時黑暗中國的時代現實,將西方精神分析理論的要領渾然天成地雜糅在其近乎哲思類的敘事話語中,以極具實驗色彩的不羈文筆,為我們揭示了這樣的深刻哲理:和具體的個人一樣,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整體,整個人類社會也同樣具有“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個層面。如果三者之間的關系失控,將會帶來既定社會秩序的失衡、錯位乃至傾覆。只有當社會結構中的“自我”在象征著自律、規范和理性的“超我”的指導下對構成自身的“本我”進行有效的克服,整個社會機體才會重獲穩定、和諧與統一。
程麗蓉[7]認為,《不周山》的創作是魯迅人生感知方式和思考角度漸變的集中顯現,他更多地從日常生活的個體生存體驗出發去感知和思考歷史人生,并痛苦地發現分裂性存在是人的基本處境和困境。這一哲理性體悟反復重現于《故事新編》,并輻射到其他眾多文本之中,成為魯迅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之一,進而影響到他的敘事態度和藝術選擇。該文不僅指出了彌漫在《故事新編》中的那種分裂性存在,而且進一步點明了《不周山》對于整部《故事新編》創作的啟動意義,對于后者,在以往的《補天》研究中還不曾有人提到過。
對《故事新編》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埃及]李哈布的《塔哈·侯賽因的<山魯佐德之夢>與魯迅的<補天>對比研究》[8]等。
三、《野草》研究
與去年相比較,本年度《野草》研究又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汪衛東近年來一直致于力《野草》研究,本年度又有兩篇力作出現:《<野草>的“詩心”》[9]和《“淵默”而“雷聲”——<野草>的否定性表達與佛教論理之關系》[10]。
在《<野草>的“詩心”》中,汪衛東認為,實證的、象征的和哲學的解讀,對走近《野草》都做出重要貢獻,但與《野草》的“詩心”,尚有距離。《野草》,不是單篇文章的結集,而是20年代中期陷入第二次絕望的魯迅生命追問的一個過程,是他穿越致命絕望的一次生命的行動,《野草》中存在一個自成系統的精神世界,《野草》研究的客觀性,依賴于對這一精神結構的把握。《野草》的寫作,起源于1923年的沉默,此時魯迅矛盾纏身,積重難返,陷入到自厭與自虐的情結中。進入《野草》,魯迅試圖擺脫矛盾狀態,做出最終的抉擇,在《野草》中,他把自身的所有矛盾袒露出來,并推向極至,歸結為生與死的難題。出生入死的追問卻最終發現,所謂矛盾背后的真正自我,并不存在,而就在現實的生存中。通過《野草》,魯迅終于確立了其后期的反抗式生存。《野草》所顯現的由虛無到反抗的艱難掙扎,展示了中國現代轉型的痛苦肉身。
該文與論者的《<野草>與佛教》[11]在論述理路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同時也吸納了他的《魯迅的又一個“原點”——1923年的魯迅》[12]中的精華,從而顯得更為成熟和豐滿。論者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心解”魯迅,多次指出魯迅與佛教的精神關聯,卻未對魯迅與獨具特色的中國佛學:禪宗發表意見,從而引發了筆者的一些思考,茲亦略記如下:
禪宗講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致力于去除人(參禪者)與佛(參禪對象)之間的所有障礙,其中包括理智束縛以及一切語言文字的障礙。如果說,應當擁有怎樣的“詩心”才能與我們心中的“佛”——魯迅的《野草》產生對話,那么禪的回答必定是“無”,或者干脆無可奉告。然而,生活在理智世界中的我們,卻又不得不運用概念、邏輯、判斷、推理等諸如此類的法則,否則我們便無法將我們從中“悟”到的東西告知別人,以便和他人形成交流。可是,這在禪宗初祖達摩那里,是得不到認可的。當達摩決定西歸印度時,要試驗一下他在中國的幾個徒弟的悟性如何。一名叫做道副的弟子說:“依我的看法,我們不應執著于文字,也不應舍棄文字,因為文字乃求道的工具。”達摩只是說:“你得到我的皮。”也就是說,在達摩的幾個徒弟中,道副的悟性是最低的。由此看來,禪最厭惡依傍,尤其是語言文字這種極不可靠的中介。禪所給予的是心靈的完全自由,任其自我展現。佛與非佛,人與非人,這一切都不過是文字游戲,沒有真實的意義。你只要是你自己,則你將虛如太空,自由如空中鳥或水中魚,你的精神必將充實完滿,也必將明澈如鏡。禪的意旨即在于使我們得到完全的解脫,擺脫一切無名的枷鎖和自造的煩惱。精通佛教經典的魯迅未嘗沒有這樣想過,尤其是在他遭受重大挫折的“沉默的十年”之中。而一旦他再度遭遇絕望,他由于積習終于形諸文字,也就是創作出《野草》這樣的高度個人性的作品時,他真的就此就解脫了嗎?事實證明,魯迅沒有。以禪宗眼光視之,借助于任何語言文字都不可能達致涅槃,即成功的彼岸。魯迅也不例外。筆者認為,這也是魯迅最終放棄類似《野草》般的文學創作,而專心著力于雜文般的實踐的一大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在《“淵默”而“雷聲”》中,汪衛東著重探討了《野草》的否定性表達及其思維方式與佛教論理之關系。他將佛教否定論式大致歸納為雙邊否定、空空邏輯、即非邏輯和中觀派“四句論式”。認為《野草》中存在著大量的雙邊否定;通過無窮否定最后抵達類似于“空空邏輯”的超越性立場的行文邏輯,在《野草》中比比皆是,并顯現了“四句邏輯”的旨趣;而把《野草》作為一個整體來觀照,也顯現了同樣的否定邏輯,即:非生——非死——非非生亦非非死。《野草》所現具體否定方法與佛法思維之相似既已揭示,此時驀然回首,則其借由否定而達成的解脫之路,在整體上與佛法理路的相似性,頓時卓然可見。這就是:所謂自我,即非自我,是為自我;所謂因緣,即非因緣,是為因緣。這一探究,不僅在影響層面上揭示出佛經對于《野草》的深層影響,而且也進一步證明了在共同的東方文化蘊藏中,魯迅與佛陀這兩位大智者在人生最為關鍵之處終于不謀而合了。
楊劍龍、陳衛爐[13]認為,《野草》形而上地展示了魯迅的靈魂,以其詞語的悖反、母題的悖論等顯示出悖論式的思想。它增加了魯迅散文詩的藝術張力,使散文詩《野草》成為中國現代散文最具內涵的藝術精品。作為個體獨特生命情境與民族特定歷史進程相伴而生的藝術結晶,《野草》將魯迅在“五四”時期苦悶激蕩的心理真實,含蓄而形象地化為外在表現形式,在悖論、反諷中,作品形成糾纏沖突而非整合、流動不居而非靜態的文學張力空間。正是在這個空間中,魯迅富有獨創性地通過“悖反”營造出一種新的時代美感,它超乎日常語言的“陌生化”而生成,讓讀者在真切的閱讀體驗中獲得靈魂的淬煉與美的享受。
對《野草》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孫玉石的《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14]、王彬彬的《<野草>修辭藝術細說》[15]、吳翔宇的《<野草>的張力敘事與意義生成》[16]等。
四、雜文研究
雜文這種文體,在魯迅而言,是一種“無體的自由體式”,它使魯迅的創作才能得到了最為有效的發揮。這種文體的形成有一個不斷成熟、不斷完善的過程,陳方競[17]對之進行了細致的考辨。他認為魯迅是在“短評”基礎上產生“雜感”,又是在“雜感”基礎上產生“雜文”的,梳理“雜文”的這一形成過程,可見其有“短評”和“雜感”不具備的特征。這種情況更主要體現在魯迅前期創作中,后期雖有所延續,但三種不同文體各自的特色在他的雜文中又常常融為一體得到表現,這在他1933年雜文文體創造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魯迅30年代中期為“雜文”正名,與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存在認識上的差異,針對的又是其時京、海派聯手在文壇上掀起的“小品熱”,由此而有他對雜文功能和作用更為確切的定位。
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直以來被視為“左聯”的一篇綱領性文獻。黃健[18]認為,魯迅雖然認為構建“左翼”話語,激進的變革態度、方式是需要的,也是必須的,在精神上需要“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的精神,但在策略上、方法上則需要“韌性”的精神。“左翼”話語不應是一種標語口號,不是一種空泛的吶喊,而應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話語權利和譜系的建構,其內核應具有鮮明的思想、觀念、意識,乃至人格的意蘊和涵義,其獨特性仍然是要喚起廣大民眾的覺悟,推動“五四”新文化思想啟蒙的縱深發展。
“阿金”實有其人,還是魯迅的虛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問。李冬木[19]認為阿金是虛構的,陳迪強[20]則認為阿金實有其人。陳迪強逐條剖析了李冬木的四條理由,認為都不成立,在論證上有欠周詳。論者指出,李冬木的重大推斷:日譯本《支那人氣質》中關于“異人館”廚子的描寫是“魯迅敷衍《阿金》的一塊模板”是極具啟發意義的,但是不能將《支那人氣質》的影響絕對化,我們不能忽視魯迅對中國社會歷史的體察及概括。關于《阿金》的文體,論者亦有己見,認為是散文,而不是如李冬木所言是小說。《阿金》在魯迅文章中難稱出色之作,據此展開論爭亦堪可引起相關關注。
王學謙近年來一直致力于魯迅與道家文化研究,本年度再度推出力作:《面對死亡的“魏晉風度”——魯迅臨終散文 <死 >的道家文化意蘊》[21]。文章認為,魯迅臨終前寫的散文《死》是一篇“師心”、“使氣”的“魏晉文章”,具有濃郁的道家文化精神。《死》將豐富的知識與社會、人生的觀察、體驗融為一體,語調從容舒緩,娓娓道來,卻又不乏尖銳、透辟。在對中國社會庸常的有鬼論進行嘲諷、批評的同時,也表達了魯迅面對死亡的“隨便黨”態度。這種“隨便黨”死亡觀,是和中國傳統無神論的道家死亡觀一脈相承的,也是魯迅蔑視世俗社會,追求獨異的個人精神的寫照。
對魯迅雜文研究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吳康的《歷史同一性的現代輪回:革命與反革命——魯迅雜文研究之二》[22]和《“火”的歷史:殺戮、酷刑與監獄——魯迅雜文研究之四》[23]以及陳方競、楊新天的《魯迅雜文與<故事新編>關系考辨》[24]等。
五、魯迅作品整體研究
以上文章著眼于魯迅作品各分集及文類研究,本年度還有一批論文(專著)是從各種視角和層面對于魯迅作品的整體透視研究。較具代表性的有:
馮光廉《中學魯迅作品選篇及編排問題之切磋》[25]從中學語文教學視角出發,認為關于中學魯迅作品經典性的理解和篇目的選擇,要注意的問題有:有突出疑問的篇目是否應該入選;選篇的類型可否再多樣一些等。繼之,論者分析了造成魯迅作品難懂難學的幾大原因,其中筆者最感興味的是:教學觀念教學方法不恰當。論者認為,中學生通過自己的閱讀和老師的講解,只要能夠大體理解魯迅作品的大意,能夠把握魯迅作品的基本內容要點,能夠熟悉魯迅作品中最深刻、最精煉、最重要的句子段落,就可以了。關于中學魯迅作品編排的原則和方法,論者認為應當注意以下二點:初中與高中選篇的比例應該如何掌握;如何編排各類文體的結構系統。其中第二點涉及到了文體問題。這正是當代中學生最為匱乏和薄弱之處,理應引起充分注意。在此基礎之上,論者提出了他對于中學魯迅作品選篇的設想,并對新增篇目《立論》、《過客》等作了具體而細致的講解。文章在當下有關魯迅作品教學的激烈論爭中,增添了一種來自學界的理性和平和的聲音,其所具有的學理性和建設性的思考都是可以引起魯研界與教育界的密切關注的。
靳新來《“人”與“獸”的糾葛》[26]是對魯迅筆下動物意象的獨特分析。該著的創新之處在于:第一,首次將魯迅與其筆下的動物意象研究提高到一個學理性的高度。在具體論述過程中,將魯迅筆下的動物意象視為一個象征、隱喻系統,指出它背后隱含著的話語其實是一個“人的世界”。第二,在此基礎上,把魯迅筆下的動物意象大致分為二類:一類是狼、貓頭鷹、蛇、牛等,象征那些首先覺醒的現代知識分子;一類是狗、羊、蚊子、蒼蠅、細腰蜂等,象征那些維護傳統和現實的現代奴性知識分子。對照魯迅的精神世界,這種分類是相當準確到位的。第三,對魯迅與蛇發表了頗為精彩的議論。認為從蛇這一意象,我們可以看到魯迅不同流俗的獨立人格、制敵于死命的刻毒以及冷酷的自審意識等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素質。這一看法,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第四,其所采取的視角或學術理路:從一些看似“小”或“歪”的思想或藝術細節,深入鉆研下去,力求“小題大做”、“歪打正著”,亦堪可引起注意。
袁國興《魯迅小說和“雜感”類“文章”的文類體式互侵》[27]從文體視角出發,認為辨識魯迅小說和雜感類文章的文類體式互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魯迅小說為什么都取“短篇”形式。在論者看來,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似乎存在著一個“小品小說”潮,這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文化生態有關,與這些作品作者的文化修養有關,與中國現代文學初期的“小說”和文學“創作”理念有關。通過辨識也能夠使人充分理解魯迅文學創作成就的不可取代性。魯迅和他的同伴們處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一個特殊時期,其文學特質和無法取代性,就在于別人缺少其特定的“缺陷”和優勢,無法“復制”出他們所處的歷史現場。離開了這些去認識魯迅,去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的文學特質,不論是拔高還是貶抑,都不能完全切合實際。
趙延年《畫說魯迅》[28]是對魯迅作品木刻的完美展現,其所作《狂人日記》38圖、《阿Q正傳》60圖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趙刻《狂人日記》第2圖:“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為例。作者運用平刀和斜刀鏟刻的獨特技法,以大塊面的黑白造型,通過深色的門窗,對比出門外皎潔的月光。狂人沐浴在清輝之中,好似大海里的一葉孤舟,孤獨而無所依傍。這喻示著狂人如果要想反抗,就只能依靠他自己。“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易卜生名言在這里得到了絕好的體現。尤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于狂人背影的刻畫。其傳神的姿態和表現的力度,正與同樣以刻畫背影而著稱的珂勒惠支相同,而后者也正是魯迅所激賞的。
從整體上對于魯迅作品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丸尾常喜的《“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29]、鄭蕾的《“大眾化”實踐與 <阿 Q正傳>——<阿Q 正傳>插圖研究》[30]等。
[1][日]藤井省三.魯迅的《孔乙己》與芥川龍之介的《毛利先生》——圍繞清末讀書人和大正時期英語教師展開的回憶故事[J].上海魯迅研究,2010(春).
[2]李宗剛.父權缺失在場對比下的人生價值——魯迅小說《藥》新解[J].魯迅研究月刊,2010,(4).
[3]李今.析《傷逝》的反諷性質[J].文學評論,2010,(2).
[4]顧農.閑話《祝福》[J].書屋,2010,(11).
[5]馮光廉.魯迅研究若干問題之我見[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0,(1).
[6]姬志海、李生濱.在“藝術復仇”的故事背后——再讀《鑄劍》[J].寧夏大學學報,2010,(5).
[7]程麗蓉.魯迅《故事新編》的啟動及其意義[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5).
[8][埃及]李哈布.塔哈·侯賽因的《山魯佐德之夢》與魯迅的《補天》對比研究[J].東方論壇,2010,(5).
[9]汪衛東.《野草》的“詩心”[J].文學評論,2010 (1).
[10]汪衛東.“淵默”而“雷聲”——《野草》的否定性表達與佛教論理之關系[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1).
[11]汪衛東.《野草》與佛教[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1).
[12]汪衛東.魯迅的又一個“原點”——1923年的魯迅[J].文學評論,2005,(1).
[13]楊劍龍、陳衛爐.論魯迅《野草》的詞語悖反、母題悖論及其藝術張力[J].學術月刊,2010,(4).
[14]孫玉石.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5]王彬彬.《野草》修辭藝術細說[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1).
[16]吳翔宇.《野草》的張力敘事與意義生成[J].浙江社會科學,2010,(8).
[17]陳方競.魯迅雜文文體考辨[J].中山大學學報,2010,(4).
[18]黃健.構建獨特的“左翼”話語譜系——重讀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J].中國文學研究,2010,(4).
[19]李冬木.魯迅怎樣“看”到的“阿金”?——兼談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系的一項考察[J].魯迅研究月刊,2007,(7).
[20]陳迪強.“阿金”是虛構的嗎?——與李冬木先生商榷[J].上海魯迅研究,2010(夏).
[21]王學謙.面對死亡的“魏晉風度”——魯迅臨終散文《死》的道家文化意蘊[J].吉林大學學報,2010,(6).
[22]吳康.歷史同一性的現代輪回:革命與反革命[J].魯迅研究月刊,2010,(1).
[23]吳康.“火”的歷史:殺戮、酷刑與監獄[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4).
[24]陳方競、楊新天.魯迅雜文與《故事新編》關系考辨[J].福建論壇,2010,(5).
[25]馮光廉.中學魯迅作品選篇及編排問題之切磋[J].魯迅研究月刊,2010,(10).
[26]靳新來.“人”與“獸”的糾葛——魯迅筆下的動物意象[M].上海:三聯書店,2010.
[27]袁國興.魯迅小說和“雜感”類“文章”的文類體式互侵——兼及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的“小品小說”問題[J].魯迅研究月刊,2010,(4).
[28]趙延年.畫說魯迅:趙延年魯迅作品木刻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29][日]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M].秦弓,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30]鄭蕾.“大眾化”實踐與《阿Q正傳》——《阿Q正傳》插圖研究[J].魯迅研究月刊,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