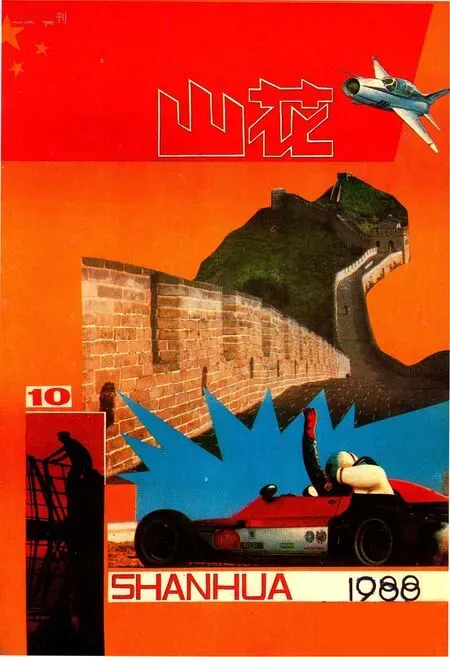社會邊緣階層的邊緣化思想——淺析皮克拉悲劇的必然性及其寓意
高江玲
社會邊緣階層的邊緣化思想
——淺析皮克拉悲劇的必然性及其寓意
高江玲
1993年,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其作品想象力豐富,富有詩意,顯示了美國現實生活的重要方面”。她善于運用黑人傳說和神話來增添作品的藝術魅力,作品關注黑人在美國社會的生存困境,揭示種族歧視對黑人的精神摧殘,寫白人的價值觀念給黑人人性造成的扭曲,也寫黑人社會內部對自己種族的排斥和傷害。她寫人的精神世界、心路歷程,內心的創痛、騷動和渴求,寫對自我的尋找和對自己文化之根的追尋。黑人要實現自身的生存價值,要找回尊嚴和獨立的自我,必須保持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從而才能有真正的生活。
和常見的社會觀察家不同,莫里森非常排斥那種“小說A比B或比C好,因為A寫的更像大多數黑人的真實情況”的觀點。她另辟蹊徑,努力探究社會邊緣階層的邊緣化思想,“我個人對那些特殊的人著迷,因為我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適用于普通人的特征”。
1970年,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最藍的眼睛》發表。小說敘述一個年僅11歲的黑人少女皮克拉·布萊得拉夫因皮膚黝黑、相貌難看而令周圍人(主要是黑人),甚至家人厭惡,于是心情郁悶,生活壓抑,她十分渴望獲得一雙美麗的藍眼睛,來獲得人們的喜愛和祝福,但卻由此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淵,最終神經錯亂。小說以兒童的視角來揭示皮克拉的心路歷程,敘述者克勞蒂亞·麥克蒂爾是一個黑人小姑娘,比皮克拉小兩歲,是皮克拉唯一的朋友。作者以“秋、冬、春、夏”作為小說四個部分的標題,秋天,皮克拉月經初潮,發育成熟,因缺少一雙藍眼睛而成為人們攻擊和譏諷的對象;冬天,皮克拉遭受父母毒打,眾人輕蔑;春天,皮克拉被她的生父強奸,慘遭摧殘;夏天,皮克拉早產生下一個很快就夭折的嬰兒。故事在夏天結束了,但四季還在循環,生活仍要繼續,暗示皮克拉式的悲劇命運將會重復上演。
莫里森的小說直面非洲裔美國人的復雜性、恐懼和生活中的愛。雖然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是一個禁區,但現實中黑人要實現自己的美國夢非常困難。他們既反對白人文化,為了生存又認同白人主流文化;他們處于文化的邊緣,但又夢想進入他們所反對的主流文化的中心。他們身上充滿了悖論和矛盾。皮克拉的悲劇與黑人長期所受到的壓迫、剝削和精神文化上的奴役是分不開的。長期以來,他們視白人價值觀念為圭臬,盲目否定自我;逃避家庭責任,冷漠勢利,缺乏道德約束,皮克拉的悲劇實質是黑人心靈文化迷失的悲劇。
一、民族傳統文化的泯滅
著名的布萊德利效應揭示了美國社會存在的種族暗流,由于歷史的原因,白人文化在美國始終占據統治地位,處于社會邊緣階層的黑人接受和內化了白人的審美觀,并按照膚色深淺將人劃分等級。這種內在化的潛意識認為白人至上而黑人卑劣的種族文化觀,是皮克拉走向自我否定與自我毀滅的悲劇種子。
皮克拉以白人文化的“藍眼睛”來界定美丑、觀察和評判世界、確定自身的價值,最后只得在幻覺中掩蓋生命的枯竭。藍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線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藍眼睛卻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標準,因為美意味著“金色的頭發,白色的皮膚,而最重要的,是藍色的眼睛”。顯而易見,藍眼睛是白人強勢文化的象征。皮克拉對藍眼睛的祈求說明她已內化了白人文化意識,喪失了族裔文化之根。
黑人傳統文化的淡漠與泯滅于種族的社會邊緣化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個體是如此渺小,如同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潮流并非自己的航向,獨立前行需要極大努力,稍有懈怠和放縱,就只能隨波逐流。聚居使人產生認同感和安全感。小說中有三個“富于同情、寬容、忠誠”的黑人妓女形象,分別為“波蘭”、“中國”與“馬奇諾(防線)”。故事發生的1940年正值“二戰”前夕,這三個女人的名字因而具有弱小但頑強抵抗強權而生存的深意。皮克拉從她們那里得到一定的溫暖和關愛,也暫時忘卻了精神的創傷。在這個充滿自我否定、自我放逐、敵視與冷漠的環境中,始終有一些固守自我與傳統文化本位的黑人在抗爭,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使黑人文化與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得以延續。
人從本質上是群居動物,只有在相同或相似的族群內才能獲得認同和安全感。文化的發展只能是漸進式的,首先要有歸屬感,跳躍性前進只能形成斷層,使人迷失。當然現實中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是悲劇人物,成功的黑人比比皆是。但掙扎在族裔文化意識淡薄的氛圍里,我們無法苛求所有的人都能樂觀和堅強。
二、家庭責任感的喪失、道德約束的缺乏
人們心理因文化的畸變而產生扭曲,他們不但仇恨自我,而且把這種仇恨蔓延到自己的配偶、子女身上。小說對一些黑人家庭的陰暗面作了大膽而犀利的揭露和剖析。
小說有一個引子,內容是美國著名啟蒙讀本“迪克和簡”的節選,描述了兒童心中理想家庭的生活畫面:一個小女孩住在一幢美麗的房子中,有慈祥的父母、可愛的小貓和小狗相伴,還有小朋友過來與之玩耍嬉戲。而這恰恰與皮克拉的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表現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
皮克拉生長在一個充滿爭吵和自卑的家庭,他們的姓為布萊得拉夫(Breedlove),意思是“孕育愛”。但愛卻是這個家庭最為稀缺之物。父親喬利是個“絕望、放蕩、欺負弱小”的酒鬼,漠視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職責;母親波琳是白人家里的理想傭人,對主人家庭的關愛遠遠超過了自己家;哥哥山姆十四歲時據說已離家出走不下二十七次。正是在這樣的家庭中,皮克拉才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及對自己的否定。
家庭責任感的喪失、道德約束的缺乏具有遺傳性。喬利的父親因不愿承擔責任,拋棄了懷孕的母親;當他尚在襁褓中時,母親便把他遺棄在鐵軌邊;十四歲時與一位黑人姑娘發生了性關系,擔心姑娘會懷孕,他也像當年的父親一樣偷偷地跑掉;歷經千辛萬苦找到親生父親,父親因忙于賭博而拒絕與他相認,殘忍地嘲笑和當眾羞辱他。面對冷酷的現實,喬利崩潰了,“他再也沒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只剩下他自己的感官和胃口,他感興趣的只有這兩者。”他變成了行尸走肉,追求各種生理的刺激和快感,家庭責任和道德對他只是幻影。
波琳在隨著喬利從南方來到北方后,環境的改變使其孤獨、空虛、備受他人歧視,甚至“她們因為她沒拉直頭發感到驚奇”。她從電影中尋求慰藉,潛移默化中,文化根基薄弱的波琳接受了電影中所宣揚的白人審美觀。一方面,她對白人社會極端崇拜和向往,近乎苛刻地忠誠執行著自己的職責,對主人家傾注了全部的愛和柔情,把這個家庭收拾得井井有條。另一方面,她卻越來越瞧不順眼自己的丈夫、兒女和破陋的小屋。對白人的崇拜和白人生活的向往使她對自己的家和孩子產生了強烈的排斥和厭惡,淡化和忘卻了作為妻子和母親應有的柔情和愛心。當皮克拉不小心打翻了熬果醬的鍋時,波琳對她先是一陣拳腳相加,接著又把她打翻在地,并補上了幾個耳光,隨后卻把被她的行為嚇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懷里給予安慰。丈夫和孩子成為他實現自己幻想價值的累贅和障礙,絲毫得不到她的溫情。
與皮克拉冷漠的家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敘事者克勞蒂亞的家庭,克勞蒂亞曾滿懷深情地回憶母親深夜為自己蓋被子的情形:“愛,黏稠,濃厚得像阿拉加牌糖漿一樣,悠悠地滲過開了裂的窗戶。”雖然同樣清貧,同樣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如給孩子們的糖果包裝紙上印的是白皮膚藍眼睛的白人形象,圣誕節禮品也都是藍眼睛、黃頭發、粉皮膚的洋娃娃,但家人的關愛給克勞蒂亞姐妹樹起了自信與自尊,使她們在這個“對金盞花滿是敵意”的社會中保持了健全的心理與人格,也正是他們家庭幸福、女兒健康成長的源泉,使她們身處逆境時不放棄期望、信仰和信任。
三、社區責任感的缺乏
面對與白人文化的不相容,黑人社區本應是諸如皮克拉般弱小群體的遮蔽容身之所。但小說中的黑人社區卻充斥著弱肉強食的殘忍和冷漠,鮮有溫情。
并不富裕的南方農村,人們互幫互助、其樂融融。喬利出生僅四天就被母親拋棄,姨婆吉米將他撫養成人;姨婆吉米生病期間,人們都來看望和照顧;死后,人們為她舉行社區葬禮。“在南方,與黑人社區的緊密相連,讓那時的喬利和波琳擁有穩定的人格”。
北方的洛蘭鎮則充滿敵意,黑人之間缺乏應有的關愛和幫助,他們鄙夷弱者,諂媚強者。社區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都對皮克拉表現出明顯的憎惡感。在學校里,皮克拉受到老師的歧視、同學的嘲弄;在糖果店里,皮克拉受到老板的蔑視。皮克拉成了社區里的替罪羊,丑陋的外表和令人內心恐懼的黑皮膚成了皮克拉一個人的缺點。人們將屈辱、怨恨傾泄于皮克拉身上時,她的貧窮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富足,她的丑陋使他們感到自己的美麗,她的不幸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幸福,她的沉默給了他們指責他人的機會。
皮克拉的父母同樣不幸。在自己的膚色、口音,甚至穿著打扮成為婦女的笑料的洛蘭鎮,無法獲得認同的波琳只好向電影尋求寄托,卻一步步被白人文化所同化。在“一個要求他必須有能力在經濟上維持家庭,但他又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世界”里,失業的喬利垮了下來。喬利那從沒完善過的人格在短暫的“正常”后又墮入了可怕的“自由”狀態。他喪心病狂地燒掉了自己的房子,又禽獸不如地強奸了自己的女兒皮克拉。
還有小說中克勞蒂亞家的房客——亨利·華盛頓,竟趁主人不在,公開宿妓,甚至猥褻克勞蒂亞的姐姐弗里達。另外幾個黑人男性,不管是貧民喬利,還是中產階級艾利休都恣意放縱自己的肉欲。群體的劣根性也不容忽視。
當皮克拉因被強暴而懷上父親的孩子時,鎮上的人并沒有給予小皮克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人們對這感到厭惡、可笑、驚訝、憤恨甚至興奮。我們希望聽到人們說‘可憐的孩子’或是‘可憐的寶貝’,可是大家只是搖搖頭而已。我們希望看見人們皺起眉頭表示關懷,可看到的臉都毫無表情。”
皮克拉一家的悲劇是對造成其人生悲劇的“社會土壤”的控訴。從一定意義上說,社區黑人從總體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寬容的笑容,也是造成皮克拉及其一家凄慘結局的一個原因。
結束語
小說接近尾聲時,皮克拉以為自己真的擁有了一雙最藍的眼睛,然而,這雙“最藍的眼睛”不僅沒能拉近她與周圍人的距離,相反,它蒙上了皮克拉的眼睛,皮克拉再也無法準確地看世界,她在人們的眼中也變得更加微不足道。
克勞蒂亞姐妹倆深深同情皮克拉的遭遇,她們希望奇跡會出現。為此她們寧愿放棄買自行車的兩美元,同金盞花種子埋在地下,希望能長出美麗的花。但是象征希望的金盞花到底沒有長出來。克勞蒂亞最后悲傷地說:“在這片土地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長的,某些花籽得不到土壤的養分,某些植物在這片土地上結不出果實。當土地決意封殺時,我們大家對此默許,認為受害者無權生存。”這片土地其實就是克勞蒂亞、小皮拉克、和托尼·莫里森成長的整個黑人群體。
托尼·莫里森曾說,寫這部小說的動力是要去描寫“在文學中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未曾認真對待的人物——那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小女孩。”以一個天真而不斷遭受凌辱的黑人女孩為主人公,寫出她的不幸與悲哀、天真與無知,這表明莫里森關注的不僅是黑人,也不僅是黑人女性,而是她們中的最弱勢群體——年幼的黑人女孩。
《最藍的眼睛》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向世人展示了當年美國黑人生活的辛酸與內心的痛苦掙扎,小說已不再僅是一種對黑人民族苦難外在因素的抗議,而實際將人們引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與探索。作為被邊緣化的群體,美國黑人被主流社會所排斥,長期處于失語狀態,其種族意識在種族主義文化暴力的壓制下被削弱、被淡化。托尼·莫里森不無感慨地指出,黑人民族要想生存下去,除了擁有政治權利和經濟獨立外,還必須保留住黑人文化。
分析他人,回顧自己。今天很多中國人談起傳統就深惡痛絕,恨不能跟祖宗一刀兩斷。在遠離了“五四”狂潮的今天,我們是否應當更冷靜地對待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帶著理性、帶著自尊、帶著理解和寬容,平允公正地評價我們的祖先和自身?這值得所有人思考。
[1]泰勒·格思里.托尼·莫里森訪談錄[M].克林頓: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1994:88,88,88
[2]Hariprasanna,A.“Racial Discourse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Femin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ed[M].R.K.Dhawan.New Delhi:Mehra Offest Press.1996.119
[3]莫瑞森著,陳蘇東,胡允桓譯.最藍的眼睛——托妮·莫瑞森長篇小說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103
[4]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0.94,34
[5]Page,Philip.Dangerous Freedo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5126
[6]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妮·莫里森與美國二十世紀黑人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0,40,26
[7]莫瑞森著,陳蘇東,胡允桓譯.最藍的眼睛——托妮·莫瑞森長篇小說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120,134
高江玲(1974—),女,河南省洛陽市人,河南科技大學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英語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