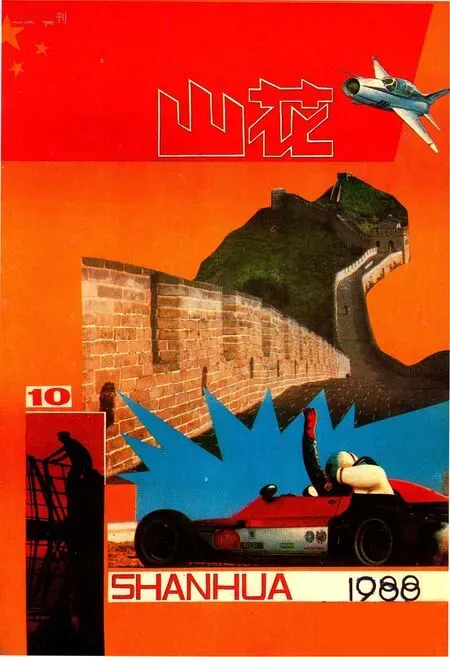月橋會
史雪坤
月橋會
史雪坤
芽月掛在樹梢兒,亮得如剛鍍過金的鐮刀。夜出奇的靜。她來到橋頭等他,瞧他來的方向——沒有。垂頭望橋下清澈如鏡的小溪,長發(fā)滑過肩頭,散落胸間。一陣風,很細,輕輕揉搓著黑黝黝的發(fā),她身寒了一下,畢竟至季深秋。
她生得溫文爾雅,考大學時因家貧瘠無條件地自退。她不怨,任命,為養(yǎng)生,在村辦工廠打工,很出色,廠長器重,安排到廠辦公室當會計,從未閃失。廠長的兒子很無聊,看她長得出色,又跟自己歲仿,時常挑逗。她只是低著頭,紅著臉,羞澀地笑,讓著他,他是廠長的兒子,是這個廠給了她出路。有時實在煩得沒法,便說有事走出去。長此以往,廠長的兒子鬼,看穿她遮攔的心,就直言不諱:……嫁給我,有吃、有穿、有車坐……廠長的兒子愈來愈吝色,她只好退避,向廠長說家有事——不來上班。
廠長不錯,得知是兒子亂來,當面訓斥。兒子是狗的化身,翻了臉,隨手拎起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操在頸下,恐嚇:……再管,抹脖子……廠長膽怯,讓了步。他是家里的獨苗,怕出事,斷了香煙,由了他。
是夜,廠長兒子去她家找她,門閉,一腳踹開,響聲打破這靜默的小院兒。她爹早逝,家里僅有她娘和她,體弱多病的娘見此驚愕,他道明來由,娘回話遲緩,他惱怒,一腳踢翻椅子,撞到迎面墻上,動靜很大,嚇壞了娘,她要喊人,娘攔住不要……只得應從。
她哭了整個夜,淚打濕了花花的枕。娘過來勸:……都是娘無能,擺脫不了“魔”……遠走吧!有娘這把快入黃土的老骨頭頂著……她聽后,抱住娘山崩地裂地慟。
她偷偷邀他出來,他是她先前要好的人。是家人的一點隔閡,拆散了這對露水鴛鴦。他去年結(jié)婚時她偷著到街頭去看,新娘子是鄰村的,長得不耐看,挺老相,化了妝的,簡直是個老巫婆。是他爹占她家的地位,她爹是村長,是位很有領導“風度”的村長……她回到家倒在床上,淚打滿面,思念她倆往日的美好……
芽月滑過樹梢兒,有一桿子高,她仔細望了,還沒來。她的心跟身子一樣,涼了。
彷徨間,雜碎的腳步聲,打散了她滿目的云。他來了,拖著跳動的影兒,喘著粗氣。忙道歉:對不起,你等久了,有事來晚了,女人快要生了,我脫不開身……她夜眸中閃爍著委屈的淚,一頭撲到他懷里用拳輕輕擊打著他透骨的胸。啜泣著:……你救救我,我不想嫁給那畜生……那夜,娘沒在家,他去了,要強暴我,是鄰居救了我……咱走吧!我沒有破身子,干凈著呢……外面的天很大,那里有咱倆的容身……他無奈地勸:別哭、外人聽著,我、我走不了了,女人快要生了,要當?shù)耍阆腴_點兒,任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她聽后頓停,拋開他懷,瞪掛滿淚痕的眼看他,他忽像她眼中素未相識的人。倏地,他看著她縱橫的淚,可憐了,掏出手帕,遞過去。她不接受,委屈地打掉了。手帕像只受傷的蝙蝠跌落橋下。他去撿,還好,丟在溪邊干枯的草枝間。走上來,見她,嗚咽著去了。遠處,月丟給他一個完形背影。他木雞般呆滯,一時間,腦海里晃動她剛才的淚。往日的情……心生痛楚……決定,跟她去。
剎那間,風來了。路旁的一棵老樹枝上掛著一只廢棄的塑料袋,被風一吹,叫出噼噼啪啪的響聲。墨藍的天宇飄來了無數(shù)塊云。一塊云挺大,不隨風走,緊緊地抱住芽月。月脆弱,甩不掉堅實的云。
夜暗下來,他木然在橋頭,完整的身影變成一團模糊的影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