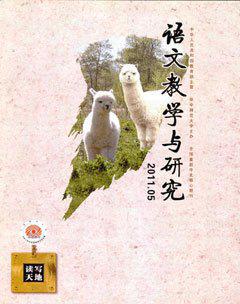秋天的聲音
羅偉章
秋天的聲音是風(fēng)的聲音,是莊稼成熟的聲音,是農(nóng)牧民滿懷喜悅收割的聲音。
我老是有個顛倒因果的錯覺:大地上的北方和南方,不是以緯度劃定的,而是以風(fēng)劃定的。這次出行,更讓我有了實感。通遼以北,風(fēng)以蠻橫的姿勢警告你:注意,寒冷的季節(jié)就要來臨!華北平原的風(fēng),總忘不了提醒你一聲:同志,這是秋天了。長江中下游及江南丘陵地帶,風(fēng)的語言則含糊其辭,它從你臉上拂過,卻不讓你知道。早聽人說:“北方的風(fēng)不進門。”我當時想,北方的風(fēng)真是有情有義,去了才知道,北方的商廈店鋪及私人住宅,這時節(jié)都關(guān)門閉戶,風(fēng)想進也進不了。由于此,外面冷冷清清,根本看不出里面正在營業(yè),正在生活,直待推門而入,才見熱熱鬧鬧。這似乎鑄就了一種性格。特殊的地理,總會鑄就特殊的性格,特殊的性格,又會鑄就特殊的人生。
風(fēng)在大地上游走,聲音美麗動人,尤其是在蘆葦蕩,風(fēng)起蘆梢,似溪水流淌,如鳴佩環(huán),又像徐徐展開的綢緞,綿密、寬闊,你覺得,自己簡直可以躺到那聲音上去。風(fēng)捋動著莊稼,鼓點一般催促它們生長和成熟。我在加格達奇等車的時候,跟一個大興安嶺的農(nóng)人閑聊,他說到他們那里的豆莢,說得很有意思:豆秧見風(fēng)就長,今天牽藤,今天就得搭架子,否則,一夜過去,藤蔓便四處亂竄;緊接著,它們麻利地開花、結(jié)實、干漿。因為它們知道,如果不抓緊時間,霜期到來,自己就只能以豆秧的模樣枯萎,永遠成不了豆莢。這是它們的命運。由于這緣故,佳木斯以南的種子,都不適應(yīng)大興安嶺的氣候——那些種子在溫暖的環(huán)境里待慣了,懶洋洋的,往往是花還沒開出來,就被凍死。
九月中下旬,各地進入秋收。這是分外忙碌的季節(jié)。“秋忙秋忙,繡女也要出閨房。”秋收不是收,是搶。跟太陽搶,跟雨水搶。除了收,還要搶晴耕翻,準備小麥和油菜的播種。秋收、秋耕、秋種,謂之“三秋”。這是一年莊稼的終點,也是下一年莊稼的起點。
如果把各地秋收的聲音合成一處,該是多么壯闊!深綠色的聯(lián)合收割機,在田野上駛過,大豆、玉米、稻谷,被收割機“吃”進儲備倉,儲備倉裝滿,再停車放糧,農(nóng)人牽著口袋,把糧食接住,便是很干凈的籽粒;隨后,他們將口袋搬進村莊,搬進家里,一年的辛苦,便有了沉甸甸的回報。
收割機一天能割三坰多地,比人工要快十數(shù)倍,但不是所有農(nóng)人都愿意用它。他們情愿多流些汗水,手工操作。這其中有個道理:收割機都是把殼攪碎揚在田里,但農(nóng)人希望把稈子留下,冬季喂牛。收土豆更是依靠人工,用鋤頭挖,遇到松軟的土地,逮住梗子一帶,又白又大的土豆便破土而出。農(nóng)民們說:“土豆是個寶,天天離不了,怎么吃怎么好。”大荒之年,一季收獲的土豆就可以讓所有災(zāi)民活命。土豆和玉米、大豆、稻谷等農(nóng)作物一起,為人類的生存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牧民同樣要收割。我們可以把秋季牛羊出欄當成一種特殊的收割,這種收割,和農(nóng)作物以及蓖麻、葵花、甘薯、煙葉、紅干椒等經(jīng)濟作物的收割一樣,是直接見到效益的。但他們真正意義上的收割,是打草,打草機把草割下來,圓捆機再扎成捆。每捆足有千斤。草捆東一垛,西一垛,如放牧的牛羊。這些草捆,牧民儲存起來,作牲口冬季的飼料,有多余的,便用大車拉出去賣掉。呼倫貝爾和科爾沁草原的草捆,還遠銷韓國和日本。跟收割莊稼一樣,人們依賴機器,卻也防備機器,機器打草傷根,而且,銷到國外去的,對質(zhì)量要求嚴格,機器打草和捆扎,難以保證質(zhì)量的統(tǒng)一。
我本來很想看看如何收割蘆葦,但大面積收割的季節(jié)尚未到來,要等蘆葦葉被秋風(fēng)掃凈,只剩下光溜溜的稈子,濕地也結(jié)冰之后,機器才會開進蘆葦蕩去。蘆葦用途廣泛,可造紙,可蓋房,可送去磚廠,可用于制造裝飾掛件,還跟草垛一樣行銷國外。
秋天的聲音是如此盛大,每一種聲音都與勞動有關(guān),與農(nóng)人有關(guān)。農(nóng)人與生養(yǎng)我們的土地保持著最為密切的聯(lián)系,最懂得“勞動是上帝的教育”(愛默生語)。正因為農(nóng)人樸拙的勞作,大自然才對他們倍加贊許,獎勵他們整整一個秋天。勞動創(chuàng)造充實的生活,也創(chuàng)造大地的美。
(選自《文學(xu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