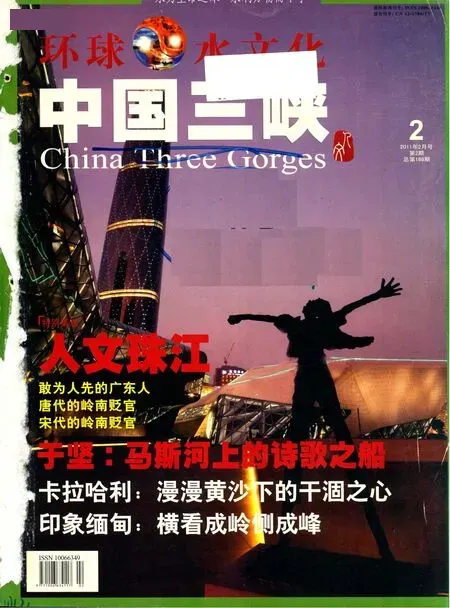于 堅 :馬斯河上的詩歌之船
文/于 堅 編輯/任 紅

1996年建成的伊拉斯謨斯大橋位于鹿特丹市中心,橫跨馬斯河,高139米,長800米,是鹿特丹新的標志性建筑。攝影/胡煒/CFP

于 堅:
1954年生于昆明。1984年畢業于云南大學中文系。1985年與韓東等人合辦詩刊《他們》。1986年發表成名作《尚義街六號》。1994年長詩《O檔案》被譽為當代漢語詩歌的一座里程碑。于堅是第三代詩歌的代表性詩人,曾獲《人民文學》詩歌獎、《聯合報》十四屆詩歌獎、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著有《棕皮手記》、《人間筆記》、《麗江后面》、《云南這邊》、《老昆明》等。海外著作有《0檔案》(法文版),《飛行》(西班牙語版),《作為事件的詩歌》(荷蘭語版),《詩72首》(英文版),《元創造》(比利時版)。另有紀錄片《碧色車站》(2004年參展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攝影/都市時報/CFP
馬斯河在流,舊時代的流速,前方是大海,船上坐著各國的四代詩人,年齡最大的是墨西哥的Sabines,生于1926。相貌威嚴的老人。最小的是新西蘭的Ranger,13歲的美麗女孩。法國的大詩人Robaud坐在我后面,眺望河岸上的歐洲塔,就是他為我們念了印第安人的《云》,一首這次詩歌節每個人都記住了的詩。原籍南斯拉夫移居美國的詩人Simic,高貴而親切,充滿智慧而謙和,他處于船桅的陰影中,他的詩歌已經穿越兩個大陸的語言。詩歌之船。沒有斗爭,沒有先鋒派和保守派,沒有過招式的強詞奪理的饒舌。這條船滿載的是各種美麗生動的富于神韻的語言,它們是河流,滔滔不絕。世界小了,最后的遼闊在各種母語和它的詩人中間,在詩人們的舌頭后面。
我僅僅是詩人,一個對母語的魅力的無可救藥的迷狂者
世界的飛機場都是一樣的,灰色的水泥建筑,尾蛇在城市的郊區,密封的玻璃墻,護照、海關、免稅店……從一個機艙進入另一個機艙,從B747到A300;世界的機艙是一樣的,安全帶、空姐式的笑,猶如罐頭中的罐頭,吃著統一配制的食物,在預定的時間中,從出租車的鐵門出來,進入機場的玻璃門,進入飛機的鋁門,在曼谷機場的玻璃密封大廳中待六個小時,然后通過一個管道從另一個鋁門進去,再從另一個鋁門出來,鉆進另一輛豐田汽車,停止的時候,你已經離開象形文字的故鄉,站在嵌滿字母的歐洲。
世界已經如此之小,如此缺乏細節,等我緩過神來,翻翻地圖,才發現在十多個小時中,我已經飛越云南高原,越過瀾滄江、湄公河平原,已經越過印度次大陸和中東、越過了地中海……越過了社會主義、聯邦制、資本、議會、原教旨主義……如此遼闊的歷史和空間,我看見了什么?金屬的管道、電視屏幕上的好萊塢電影、小窗口外面沒有溫度的天空,像一位印第安的詩人寫的那樣“云,變了”。
世界已經變得如此之小,鹿特丹猶如欣欣向榮、高樓成群的昆明,公司、購物中心、水泥街道、汽車、茶色的玻璃摩天大樓,映出另一座寫字樓。鹿特丹被稱為荷蘭的小曼哈頓。鹿特丹人并不喜歡這樣,他們解釋說,沒有辦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人的飛機炸毀了一切。
他們重建了鹿特丹。但昆明,經歷了什么大戰?令一個千年之城成為廢墟。瞧啊,一座新城,水泥,玻璃,瓷磚,自動電梯,我幾乎以為我是回到了昆明。世界確實小了,參加詩歌節的三十五位詩人,來自遙遠的墨西哥、新西蘭、來自非洲、伊拉克,來自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來自波黑,不同的語言,完全不同的對詩歌的理解,但幾乎人人都會講英語,英語已經成了通行世界的“普通話”,一個法國詩人,要進入世界,他得通過英語,一個拉丁詩人,他要進入世界,要通過英語。

停泊的海港,船只與桅桿。 攝影/CFP/CFP
于是生來講英語的美國詩人在晚餐的時候,一邊切面包,一邊用母語問候所有的詩人,講美國式的笑話。我們開始通過翻譯交談,關于美國你知道什么?我說惠特曼、弗羅斯特、基斯哈林、藍調、阿什伯里、瓦爾登湖……關于中國你知道些什么?李白、杜甫、毛、北京。老天,要么是古代的中國,要么是革命的中國,他是否具備了解一個國家的常識?在革命之外,在古代之外,具有普遍性的是什么?他是否知道中國世界的啤酒瓶蓋、鍋燒肉、茶、生兒子以及體會日子中的詩意。隨后他自然而然地,就像問今天為什么下雨那樣通過翻譯問我——一個只講漢語,終身用漢語寫作,并且是云南方言的中國詩人:你為什么不學英語?他并沒有居高臨下的口吻,他只是問問,問得那么自然,那么親切。他的晚餐位于荷蘭,他在另一類詩人的母語中,但他沒有一秒種想過要學荷蘭語。
我說:你為什么不學漢語。美國人聳聳肩,大概以為我太不國際化,太民族主義。不對,我只是詩人,我只是用漢語寫作,我太專注它,太熱愛它了,我沒有工夫再去注意另一種語言,這令我落后于時代嗎?這令我不能與世界接軌嗎?如果是這樣,我寧可在沉默中而落后。我僅僅是詩人,一個對母語的魅力的無可救藥的迷狂者,如果不是由于這一點,我們干嗎和他們坐在一起?這個世界上會講英語的人多的是,用卡車裝。我立即失去了與這位美國詩人談話的興趣。想起只說法語的薩特,如果來訪者不會講法語,他就放棄交談,他不需要什么與世界的溝通,于是世界只得垂下來,聆聽這個家伙說了些什么。

海鷗與少年 攝影/CFP/CFP
我對墨西哥的那位老詩人有好感,他一言不發,他的每一句話,都要經過翻譯,即使他說的是僅僅是“No”,他保持著神秘的原聲。我不太喜歡那位黑皮膚的詩人,他喋喋不休,“講一種愚蠢的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的混合物”,講純正美式英語的詩人鄙夷地告訴我的說荷蘭語的翻譯。我奇怪,他以什么語作為詩人?

鹿特丹城市上空亮起數百道光束,美化了夜晚的馬斯河。 攝影/UPPA/CFP
詩人是一條河流,一群詩人卻是一群美麗的麋鹿
世界性的詩歌節,頗有些像中國文人的筆會,大家住在一個旅館里,在旅館的大堂聊天,握手。修長的詩人與笨拙的詩人、害羞的詩人與人見人愛的詩人,冷傲的詩人與喜歡合影的詩人。不談詩,更不恭維別人的詩。這一點和中國一樣。談論尼德蘭變化無常的天氣。去同一飯店吃飯,喝紅葡萄酒、咖啡和茶。在午后兩點集合于碼頭,乘船游覽馬斯河。
馬斯河從鹿特丹市中間穿過,兩岸,堆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集裝箱,紅紅綠綠。看不出河岸一詞原在的含義。我們是另一種集裝箱中的詩人,船上流通的自然是英語。但不久,富于外交效應的英語就被忘記了,詩人們回到各自的母語中,神秘而遼闊的沉默。
學生從入學學習中醫伊始,就每日清晨利用30分鐘時間誦讀,感受經典的古韻,提升中醫人的行為素養。期間的中醫基礎理論及中醫診斷學學習中也會涉及《內經》原文的出處,由于每日誦讀,自然會加深印象;當時學生不一定能夠理解其義,只覺朗朗上口,隨著年齡的增長,學業的深入,自然會深入理解,銘記于心。這期間教師要注重在閱讀方法上給予指導,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學期末可以以誦讀比賽的形式激勵學生,既可以作為形成性評價的一部分又豐富誦讀的內涵。
法國詩人Tarkos坐在我旁邊,我們通過翻譯進行交談。因為詩歌節的主題之一是法國詩歌的四代人。我不免問起他四代詩人之間的關系,他說,我們之間相處得很好。他指的不是故意要相處得很好,而是為什么要有不好的關系。我們沒有聽到預料中的那種輕視、譏諷,或者壓制與仇恨。算起來,中國也該有四代詩人的,我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革命與批判。彼可取而代之。造反。唯我獨尊。超越。“他過時了。”難道不是嗎?是什么令中國的詩人們在十多年間就跑到了后現代,就打倒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和六十年代,新詩永遠從新一代開始嗎?
馬斯河在流,舊時代的流速,前方是大海,船上坐著各國的四代詩人,年齡最大的是墨西哥的Sabines,生于1926。相貌威嚴的老人。最小的是新西蘭的Ranger,13歲的美麗女孩。法國的大詩人Robaud坐在我后面,眺望河岸上的歐洲塔,就是他為我們念了印第安人的《云》,一首這次詩歌節每個人都記住了的詩。原籍南斯拉夫移居美國的詩人Simic,高貴而親切,充滿智慧而謙和,他處于船桅的陰影中,他的詩歌已經穿越兩個大陸的語言。詩歌之船。沒有斗爭,沒有先鋒派和保守派,沒有過招式的強詞奪理的饒舌。什么是知識分子寫作?讓魚去討論這種令它們鱗殼掉光的問題吧。
這條船滿載的是各種美麗生動的富于神韻的語言,它們是河流,滔滔不絕。世界小了,最后的遼闊在各種母語和它的詩人中間,在詩人們的舌頭后面。每個詩人是一條河流,一群詩人卻是一群美麗的麋鹿,高貴、雅致、靈敏,垂聽一切的耳朵,洞察秋毫的視力。當此船經過時,鋼鐵和獅子,護照和制度,都變成了波浪的手。海鷗、忽明忽暗的太陽,照耀著黃色的詩人、黑色的詩人,白色的詩人。云,變了。
一位詩人像祭司那樣,很輕地把這行被覆蓋著的詩揭開
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創立于1970年。是荷蘭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活動之一。詩歌節主要在詩人們中間具有影響,今年是第28屆。它的經費三分之二來自荷蘭政府,三分之一來自贊助。

變幻莫測的海天 攝影/Imago/CFP
國際詩歌節的常設工作人員只有四人。新任的主席泰加娜女士是通過報紙上招聘詩歌節主席的廣告應聘的。她并非詩人,她以前是阿姆斯特丹一個文學組織的工作人員,她有豐富的文學活動組織經驗。一個詩人可以在詩歌上德高望重,但并不保證他同時就有操作文學活動的能力,這一點,在我國往往搞錯。
泰加娜31歲,她熱愛詩歌和詩人,她愿意為詩歌的傳播工作,她是一個風一般行走,清楚工作的所有細節,并決定一切的主席。詩歌節的會場在鹿特丹城市劇院,二樓的一個休息大廳是工作室,猶如一個指揮臺,電腦、傳真機、文件、連成一長排的寫字臺。詩歌節聘請了二十多人為它工作,這些人很多是志愿的,沒有報酬,或只有很少的報酬。他們從四月份就開始工作,為了六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六天完美地進入詩歌。
泰加娜有許多研究各國詩歌的顧問,他們很多人都是翻譯者。他們向她推薦詩人,然后她親自閱讀這些詩人的作品,并決定邀請誰,在邀請上,它的宗旨主要是邀請那些在荷蘭尚不為人知的外國詩人。其實我可以把這一段略過不提,我可以省略所有細節,只說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詩歌節,讓其中的暗示令某些整天在大使館附近汲取“世界性靈感”以接軌的詩人們聽了心痛,讓讀者模糊地以為參加這個詩歌節就是“接上了軌”,或者具有了國際影響。但事實僅僅是,有一到五個關心中國詩歌,并懂漢語的荷蘭人喜歡我的詩歌,他們相信,可能還會有兩百到五百個住在鹿特丹附近的荷蘭人喜歡我的詩歌(一本詩集在荷蘭最多可以印五百本左右),于是我接到了邀請。
詩歌節的會場經過精心的制作,富于詩意的暗示。詩歌節的標志是一根紅色的羽毛。從門廳到舞臺放置了很多廢紙處理廠制造的巨大的廢紙磚,在這些廢紙做成的磚塊中間,掛著所有詩人的照片。詩歌朗誦的舞臺上也有一座廢紙搭成的墻,后面則是幻燈片打出的一片荒原。放置麥克風的臺子是一個角焊接的鐵架,其中放著中國燈籠、牛仔褲、舊電話、玻璃瓶等什物。詩歌節的活動主要是詩歌朗誦,也有關于詩歌起源的討論,關于某國詩歌的專題討論以及詩歌譜成的歌曲的演唱,也出售各式各樣詩集和印有詩句的圓領衫。

荷蘭鹿特丹港口 攝影/ChinaFotoPress/CFP
活動有兩個劇場,一個可容納七百人,另一個可容納一百五十人。主要的活動在大的劇場進行。活動每天下午都有,免費。主要的活動是在晚上,參加晚上的活動要買票,每張票是17.5盾,小孩或老人減價5個盾。休息大廳里放著一部電腦,里面儲存著詩歌節的各種檔案,包括詩人的檔案,觀眾可以自由調閱。

海鷗在優雅的環境里繁衍生存,看上去很美。攝影/濱海之光/CFP
詩人受到公爵般的尊重和禮遇。每天晚上,城市劇院都擠滿了人,珠光寶氣、衣冠楚楚、雞尾酒、葡萄酒、咖啡、老太太、青年、美婦人、男子、知識分子、教授、作家、中產階級……在雷諾阿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那種文化沙龍似的場景。
詩人不是大眾的譏諷對象,也不是大眾的卡拉OK,更不是脅肩諂笑于御前的侍者,而是倍受尊崇的古老而新鮮的智慧。不是附庸風雅,不是施舍,不是好奇,不是對事件的渴望,也不是光臨指導,純粹的欣賞。尊重詩歌和詩人是一種常識,也是普遍的教養,已成傳統的一部分。詩歌在這里從未有過類似我國的經驗,一下是全民打油,一下又成了少數人自我神化、自我戲劇化的工具。
我習慣于在詩人和他們的批評家眼中被視為“非詩”,在正統眼中被視為“異端”,在人群中被視為窮人、自作多情者甚或精神病人,我親耳聽到過這樣的話,“你們看,那邊那個就是詩人,像不像神經病”,或者,在酒足飯飽之后,“我們這里有個詩人,站起來朗誦一首,啊!”在這種場合,所有的人彬彬有禮為詩人讓路,要求你與他合影,拿著你的荷蘭語版的詩集請求簽名,那么崇敬地看著你,猶如看著誤入人群的神使。我確實很陌生,有些受寵若驚。
我習慣了由于寫詩而被人們嘲笑和輕視,我從不指望什么“挺住就意味著一切”,我指望的是別來煩我,讓我自言自語吧。我從未想到,還有人會把把詩看成一種圣體,“所有的事物中都有一雙眨著的眼睛”,詩歌節的一個活動,是在鹿特丹城市劇院的外面,在一群表情莊嚴的讀者簇擁下,由一位詩人像祭司那樣,很輕地把這行被覆蓋著的詩揭開。
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它與人生、大地是一種親和的關系
參加詩歌節的詩人都有半個小時的念詩的節目,詩歌節為此付給詩人報酬。我聆聽了法國詩人Tarkos念他的詩,法語非常好聽,戲劇化的音樂感。這不是由于他戲劇化的朗誦的結果,他僅僅是念了這首詩而已。是詞的力量使他的念出現了戲劇性的起伏。朗誦總是虛假的,如果詞本身沒有說話。翻譯告訴我,他念的詩叫做《牛奶》,其中說道,這個詞,這個詞撒謊,這個假詞。我非常喜歡這首詩的言說方式。如果說真有什么可以接軌,我以為這就是接軌。這個世界已經被普遍地升華了,詩歌是一種穿越謊言回到常識的運動。
我的節目是在閉幕這一天。主要大廳坐著大約五百左右的聽眾。我站在臺上,后面高懸一面屏幕,當我念時,我的詩的荷蘭語譯文會同步出現在屏幕上。下面鴉雀無聲。他們指望我念些什么,朦朧而神秘的東方,孤芳自賞的佳人,一片凈土,或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我知道中國當代的那些出口的詩歌已經給他們留下了這種印象。又來了一個憤世嫉俗的,繃著臉隨時準備就義的。
我開始念,《啤酒瓶蓋》。我堅信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它與人生、大地是一種親和的關系,它不是為了你死我活的斗爭,也不是為了從世俗人生中向偶像升華被創造出來的。它的自然、樸素、親切、溫和、優雅、幽默感和人間化是普遍性的,可以被任何一種聽覺感知。下面開始微笑,開始大笑,開始笑得前仰后合。我有重聽的耳朵都聽見了他們在笑。我知道我的詩歌已經生效,我為他們展示了一種僅僅需要常識就可以理解的生活,一種來自日常世界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幽默,這種幽默遍布世界,只要人們打開一瓶啤酒。我不敢說我的詩有多么好,但我敢說,我沒有裝神弄鬼,沒有夸大其辭。看啊,在那里。如此而已。翻譯告訴我,他聽見有聽眾說,沒想到中國人還有幽默感。是了,瞧瞧這個世紀,我們寫下了多少苦大仇深的文字。
說話間,黑暗中伸過來一只出版商的有毛的手。“我們很欣賞您的詩,想出版您的詩集,如果同意的話,請與我們聯系。這是名片。”我早已習慣出版社是不出版詩集的或者詩人必須自己掏錢求他們出版詩集的慣例,所以他說了兩遍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猶如忽然聽見一位素昧平生的美女對我說她愛我,我一時語塞。
荷蘭的白天無比漫長,晚上十點半了,天空還在亮著。城市劇院的外面是一個木板鋪成的廣場,對面是杜布倫音樂廳、劇院和電影院。周圍有許多的咖啡店,來自世界各地的樂隊在里面演奏。人們或聽音樂,或看話劇,或在酒吧間里談話,到處可以看到詩歌節的招貼,詩歌之風輕輕地從他們之間穿過,人們并不都去讀詩,但他們感受到生活的詩意,他們也許不熱愛,但他們尊重詩歌。
黑夜終于降臨,云,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