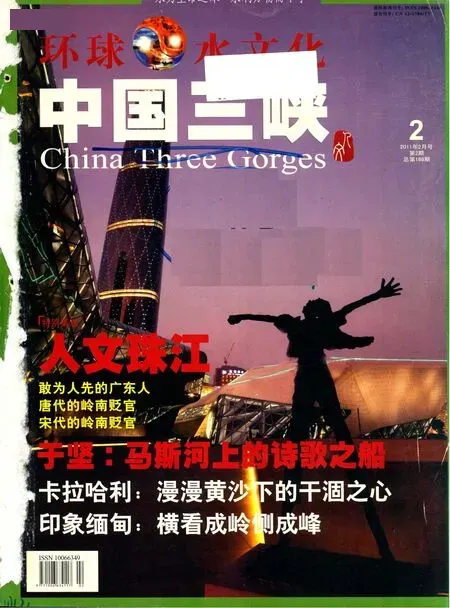敢為人先的廣東人
文/何以端 成有子 編輯/陳 陸

廣州,在西塔頂上遠眺東南方的城市天際線,廣州新電視塔、琶洲廣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珠江啤酒廠等盡收眼底。攝影/吳呂明/CFP
古代邊地之嶺南
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流域之中,唯有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因受南嶺山脈的重重阻隔,進入內地艱難而遙遠。梅嶺古道和珠璣巷分別是不少先民入粵的孔道和重要棲息地。
廣東古為百越之地。至今廣東人的血液中仍含有古越族的成分,粵語中古百越底層核心詞匯依然保持著約15%。百越散處江南廣闊地區,很早便形成稻作文化。嶺南越人長居亞熱帶,善漁獵習水性,喜食魚貝類,尤嗜蛇、蟲、鼠;斷發文身,住干欄式住宅,篤信巫鬼,在商周之交過著比中原遠為蠻樸的生活。越人的一些習性嗜好,與中原風土迥異,至今在廣東人身上依然可尋蹤跡。
秦漢之際,嶺南人被稱為“南蠻”。歷史上中原曾多次大規模移民到嶺南,極大促進了嶺南的社會發展。最早是秦始皇發50萬大軍攻嶺南并留守,再發罪徙等中原居民50萬。秦二世之亂,趙佗建南越國與越人打成一片,大臣多是越族。經過他的長期努力,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完成了第一次大融合。東晉五胡亂華,又導致北方漢人大批南遷。此后的唐、北宋、南宋,每次重大政治變故或危機,均有大規模入粵的移民潮。

廣州珠江新城廣場。攝影/陳瑞光/CFP
這些不同朝代的移民多半有共同之點:不是被貶竄,受打擊,便是憂亡國、避戰亂。他們不少曾是中原社會上層,不乏滿腹經綸之士。但故土失意,容身不得,長途輾轉,才最終得以在遠離權力中心、爭斗尚少的嶺南安身立命。此種經歷處境,感悟會比得意時更深,自然在其意識中打上烙印。看看嶺南各書院、各祠宇所奉祀的先賢,最普遍的是蘇軾、韓愈、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有學者名之曰“遺民教化”,可見對于嶺南民風的影響。
這樣,無意中形成了嶺南文化的一大特色:既奉詩禮傳家,尊華夏正朔,又并不對權力中心亦步亦趨。北方普遍存在的重大社會弊端,例如對權位的阿附追逐乃至合污、對名教的盲目僵化尊奉、濃厚陳腐的官場習氣等等,在廣東向來是相對淡薄的。相反,甘居野樸自食其力的人生觀、唯實不唯名的價值觀、以結果而不以概念判定的是非觀、散淡閑適我行我素的品味觀等等,卻一直存在。
以此觀之,從六祖慧能南來駐錫韶關開啟一代南宗,到始終秉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學術”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的離京謝絕臺、港,甘以羊城終老,恐怕都不是偶然的。
廣東人“訥于言而敏于行”,從容淡定,不太在乎別人的評論,低調而不熱衷于爭“名次”,加上無意中透著一股“我是南蠻我怕誰”的氣概,便構成較明顯的特立獨行意識。
嶺南民系可分為三大塊:客家民系、潮汕民系和廣府民系。客家民系已見前述。廣府民系指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廣東人,廣義的還包括整個西江、北江流域講白話(又名粵語)的廣東人。廣府人通常被看作典型的廣東人,具有性格開放大氣、樂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識重,務實精明、敢闖敢干等特點,很早就在嶺南的經濟文化中大展拳腳。
潮汕民系是指粵東一翼,包括今日潮州、汕頭、揭陽諸地,潮汕話屬閩南方言。其民多自福建移來,故又名“福佬”,向以刻苦耐勞、精耕細作、老鄉認同感極強著稱。近代潮汕人的商貿才能大大激發,極富創業精神,華僑眾多。他們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只要有一點點土壤便能生根,開枝散葉乃至成林。世界華人首富李嘉誠便是其杰出代表。
廣東語言現象復雜。全國七大漢語方言,廣東即占其三:粵、客、閩;而且粵、客兩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廣東。
由于地理及社會生態的相對獨立,這三大方言仍不同程度地保存著大量古漢語的詞、音、義諸元素。例如粵、客語之“粥”、閩南語之“糜”均系古詞,普通話相應的“稀飯”已毫無古意。這類例子甚多。事實上用粵語朗讀唐詩宋詞,無論押韻還是平仄,均遠較普通話為順溜、為鏗鏘,更能體現原作神韻。

廣東開平:正月十三泮村舞燈會。攝影/吳呂明/CFP

嶺南大地。 攝影/Wu Lvming/CFP
含有多達九種聲調及多種尾音的粵語,外人難以掌握,被戲稱為“鳥語”。但粵語其實源于先秦到兩漢的標準語言“雅言”,即宋以后的“官話”;在現代各種方言中,粵語保存雅言元素最多,規律依然清晰,是我國古代普通話的活化石。之所以能如此,全拜長期相對的封閉生境所賜。
相比之下,北方由于凡滄桑必盡歷,受阿爾泰語系諸游牧民族語言的多次沖擊,普通話相對于古漢語,早已“亂了”。
后發的藍色文化
嶺南文化雖然別具一格,清新可人,也出了像陳白沙、陳子壯、黃遵憲、屈大均等具真知灼見的名士,及嶺南畫派始祖居廉、居巢這樣的大師,但它畢竟只是華夏文化的一個支流,長期為正朔主流所忽視甚至歧視。
事實上,遠離華夏文明中心的廣東,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不但學術上總體比較落后,而且相關農耕文明的其他一切,也幾乎無不落后。作為歷朝流徙貶謫的瘴癘之地,廣東長期為中原人所不齒,是毋庸諱言的。直到不久之前,一些北方朋友提到廣東,依然會有“文化沙漠”的印象。
廣東躍然而起,在全國占據一個顯眼甚至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國進入近代史的事。究其根本,是因為以鴉片戰爭為轉折點,使中國面臨“千年不遇之大變局”,耕讀至上的“黃土文化”已碰上致命的海外克星,海洋文化即“藍色文化”優勢突顯。
廣東歷來先行一步的,便是其獨特的海洋文化。
廣東位于五嶺之南,南海之北,域內大都山巒起伏,江河縱橫,平原盆地相對較小,農耕優勢不強;相反因海岸線長、江河出口眾多、江海一體、海洋性特強而成為優勢。粵民世與水居,天熱喜泅,舟楫嫻熟,不憚漂洋過海,尤以沿江沿海世代浮家泛宅的船民“疍家人”最為突出。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廣東已形成通暢的古海道,秦漢就形成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唐代廣州取代了交趾成為南海交通之總樞紐,廣東人率先成批到海外去做生意。到明代廣州已有出口商品交易會了。
廣州同時成為我國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從三國時期起,佛教、伊斯蘭教先后傳入廣州。明清時又傳來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以及近代一系列科學知識。嶺南成為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最早設立學校、醫院、報紙、雜志的地區。
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了衰落時期。但嶺南卻率先形成一些資本主義的工商企業,經濟不降反升,明顯領先于內地。
1757年以后,清政府閉關鎖國,只保留著名的“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更使廣州擁有了無可比擬的經濟優勢,在18、19世紀時其對外貿易達到了歷史的輝煌高度,產生了富可敵國的潘、盧、伍、葉諸巨頭,其中的伍秉鑒更被整個西方稱為“世界首富”。鴉片戰爭前后,嶺南已不僅是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而且率先開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晉徽蘇浙粵五大商幫中,粵商的海洋文化色彩最為強烈。
在老大封建帝國農耕文明屢受列強打擊的日薄西山中,廣東終于以先進生產力及先進思維的閃亮形象,脫穎而出。
最先奔向世界的群體
在廣東禁鴉片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史稱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若以群體而論,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人群,無疑是廣東人。
在林則徐之前,廣東世代與洋人打交道者成千上萬,上至辦賣通譯,下至販夫水手,無不比內地的士大夫階級對外部世界有更多的認識。這自然深刻影響到民風。以林則徐之睿智,抵粵后很快便從中覺察端倪,而從體制內一片“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大中猛醒。
進入近代,嶺南文化史無前例地居于領先地位,對全國產生巨大影響。廣東具有推動歷史偉大意義的文化名人璀璨如星,具有領先全國意義的新思想一浪高于一浪。無論是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康梁戊戌變法,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還是國共兩黨合作及北伐戰爭,都是以嶺南為起點的。這些運動,對推進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均具決定性意義。
廣東民風通達,坐言起行,在抵御外侮、除舊布新的血戰中可以慷慨赴死。從黑旗軍劉永福到致遠艦鄧世昌,從三元里抗英到廣州起義均是如此。近代廣東軍素稱“爛打”(敢打硬仗),如北伐時的“鐵軍”粵軍第一軍、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和滇緬血戰的新一軍,輝煌壯麗的惡戰背后,凝聚了多少機靈勇猛的廣東子弟的碧血。
廣東華僑及港澳同胞眾多。其血肉相連的巨大影響與無私援助,成為廣東近代一個突出優勢。所有重大歷史貢獻和思想創新中,幾乎都有愛國華僑的身影。
晚清民初的廣東,無論是物質建筑還是精神建設,都創造了一連串的全國第一。僅以人才而論:《資政新篇》的洪仁玕、《盛世危言》的鄭觀應、首倡節育優生和鄉村建設的張競生、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者容閎、“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國飛機之父”馮如、“五四”時期“北陳(獨秀)南楊”的楊匏安等,一眾煌煌大家,都是廣東人。首批赴美留學120名勇敢聰慧的幼童中,廣東孩子便占了三分之二,他們回國后為中國的海軍、工業、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開天辟地的貢獻。此外,各藝術領域的不少鼻祖巨匠,如洗星海、馬思聰、黃藥眠、黎民偉、鄭正秋、蔡楚生……也都是廣東人。
成批叱咤風云人物的集中涌現,自必有民氣根基。廣東無疑是藏風聚氣、人才輩出之地。

2009年8月20日,廣東東莞石排鎮塘尾古村落的“康王寶誕”民俗活動由來已久,是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在每年農歷七月舉行。活動的七天里,有康王巡游、千人宴和福燈競拍等活動。攝影/陳帆/CFP
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革命大潮過去,20世紀的中間幾十年,廣東漸漸歸于庸常,人們重新過自己的小日子。
歷史常常是驚人相似。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事實上已走向重新閉關自守;而廣州卻由于每年兩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而又一次成為相當程度上的一口通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持續高壓的萬馬齊喑之中,廣州由于毗鄰港澳的“南大門”地位而仍然維持了一絲慘淡的、珍稀的亮色。
但是歷史的重大機緣再次降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公,將睿智的目光投向廣東。
春天再一次降臨南粵大地,廣東人再一次“生猛”起來。他們迅速創造了一大批新的全國第一,從第一家中外合資酒店到第一臺移動電話,從改版的生活雜志《家庭》到鮮明的政經雜志《南風窗》,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到春節報紙“恭喜發財”。每個“第一”都引來普遍關注和轟動,也引來不少的猜忌與非議。途中盡管有曲折有壓力、有人中箭下馬,但隨著鄧小平“南方談話”在廣東誕生,終于塵埃落定。
廣東人不負所托,30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社會發展成績單,無愧于改革開放排頭兵的稱號。
歷史說明當初這顆棋子,下得真準。
為什么如此重大的歷史機遇能落在廣東?因為她毗鄰港澳嗎?因為她華僑眾多嗎?因為她臨海方便嗎?
或許這些因素都有。但廣東民風之務實靈活、開放創新,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濃厚海洋文化氣息,無疑更是決定性因素之一。鄧公的“貓論”、“不爭論”、“發展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等觀點,在長期極左禁錮下,屬石破天驚之論。在不但敢吃螃蟹還敢吃蛇、貓、龍虱,早就向往港澳人憑本事掙錢的廣東人看來,最對脾胃;執行起來顧忌最小,而且常有發揮。在禁令如林、乍暖還寒的改革開放初期,“遇到紅燈繞著走”便是勇敢的創新之一。
廣東人自然也有一些局限,例如理論性不強,常被嘲為“只懂生孩子,不懂取名”。一些粵諺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無論如何不能錯過好機會)”,潮諺如“識字的捉不到蝦(蝦塘邊寫著嚴禁偷撈呢)”,又常折射出他們濃厚的草莽本色。
只是他們不會停步。廣東,更有好戲在后頭。
文化的傳統與創新
廣東人這30年也變多了。一是在發展的實踐中提高,更多原地踏步的人落伍了;二是新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粵人子弟已嶄露頭角。尤其第三,是多年來“孔雀東南飛”的“新客家人”成了廣東重要社會成分,廣義地還包括大量來粵投資、貿易及工作的港澳、海外人士。這些外省外籍“新客家人”,能量甚高而且融入了這片熱土,與原居民互補性極強,成為三大原住民系以外非同小可的第四家。
廣東的生態環境也發生了巨變。珠三角都市圈已成全球最大都市圈之一,昔日的“桑基魚塘”、“雨打芭蕉”已成稀罕之物。廣東迅速國際化,人財物流天天潮涌,那種化外嶺南的清幽早已不知所蹤。污染堵車快節奏,成了珠三角的另一張名片,廣東人還能灑脫淡定得起來嗎?
傳統嶺南文化正呈現一種大開大合的格局。一面是粵菜、粵語歌、廣東涼茶史無前例地全國開花;一面又是“食在廣州”正受滿街外省外國餐館的挑戰,不少老字號消失,“西關大屋”與老街坊日益減少,粵劇等地方劇種年輕觀眾甚少,廣東音樂慘淡經營,廣彩、廣繡、廣雕已經式微……老傳統正受現代沖擊而被邊緣化,危機是毋庸諱言的。人們大聲疾呼要保留傳統,正是對過度“開發”的一種理性而微弱的抵制。
另一方面,這又是新的機遇。一場現代浪潮沖擊過后,傳統文化的價值常常更加突顯。嶺南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包容性、開創性、務實性是它的根本。這三性決定了它的強大活力。嶺南的古代文化,原本就是融會了中原、百越與海洋諸文化的結果;而近現代嶺南文化,更是貫通中西文明于一體的產物。
兼收而能并蓄,參差所以百態。今天,嶺南文化完全可以融入新的元素,以一種無拘無束、寬廣厚重、創造力旺盛的新姿態,開出更燦爛的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