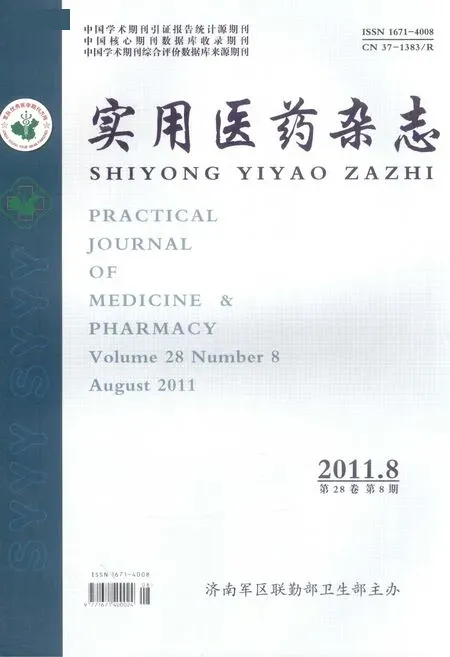方劑辨證論治方法探討
張煒悅,張 彤
辨證論治是中醫的特點和精髓,自《傷寒論》創立六經辨證方法以來,相繼有八綱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問世,這些辨證方法為臨床診治疾病提供了理論基礎,提高了療效。本文僅就方劑辨證論治方法作初步探討。
1 方劑辨證的概念
方劑辨證是將四診收集到的癥狀、體征進行分析、歸納,從而確定屬于某一方證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分析病因病機,確立治法,選擇該方劑,或在該方基礎上進行加減治療疾病的方法就是方劑辨證論治。而方劑辨證論治方法學是研究古今著名方證的癥狀、體征、病因病機、治法、方藥配伍意義、及其加減變化規律的學問。方劑辨證不僅古代有之,在現代更是很常用的辨證方法之一,其實一些著名的中醫臨床醫學家和對古今名方有深入研究的醫務工作者,都在有意無意地使用該辨證方法,只是還沒有形成理論化、系統化、規范化。筆者認為,要想取得較好療效,方劑辨證論治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辨證方法之一,該法簡明易學,以證對方,便于掌握和傳承。經典方劑和古代著名方劑是經過千百年來歷代醫家反復驗證療效確切的,以這些名方為主方,并根據患者不同癥狀體征進行加減,往往要比自己匆忙臨時組方療效更好,故方劑辨證準確與否,常是臨床療效的關鍵所在。
2 方劑辨證的源流
從現存資料來看,盡管在《傷寒雜病論》之前已有《內經》等古典醫籍誕生,但《內經》僅載十三方,所論多不詳細。此外古代醫家有人認為仲景引《伊尹湯液》(或稱《湯液經法》),似此書早于仲景,但已失傳,不得原貌。從現存文獻看,只有《傷寒雜病論》可稱為方劑辨證之祖,在《傷寒論》正文中多處出現“桂枝證”、“柴胡證”等原文,如34條“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101條“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已明確提出了湯證的概念。在通脈四逆湯方后強調“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突出了病癥與方劑相對應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傷寒論》中已經有了方劑辨證的雛形。此后王叔和《脈經》中也經常提到“屬XX湯證’’,這是繼承了仲景方劑辨證的思想。至唐代,著名醫藥學家孫思邈提出了 “以方類證”、“以方類法”、“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原則,發展了方劑辨證論治方法,在其晚年所著《千金翼方》中將《傷寒論》原文重新編次,簡而言之,“尋方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以此三方為綱,將相關條文方藥附于其后,此即桂枝湯類證、麻黃湯類證、大青龍湯類證之意。宋代醫家劉元賓《傷寒括要》突破了六經病篇的框架,取《傷寒論》主要方劑,編次31種證候,均以方名證,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白虎湯證、四逆湯證等。每證名下列出《傷寒論》六經中屬于該方證的原文,然后附上方藥,此乃真正意義上的方劑辨證論治。清代醫家柯韻伯繼承發展了劉元賓的方劑辨證方法,列出了《傷寒論》大部分方證,每一方證后又列出相關類證,如變證、疑似證等,從而使方劑辨證論治方法更加突出[1]。對于后世學習《傷寒論》,特別是運用《傷寒論》的方劑辨證論治方法診治疾病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清代以后這一寶貴的辨證論治方法沒有形成理論化、系統化、規范化,反而有弱化之趨勢,只是近幾年來才有少數學者[1-3]提出這一問題,但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3 《傷寒論》中的方劑辨證論治方法
《傷寒論》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理法方藥比較完備的辨證論治專著,主要是創立六經辨證方法,但在《傷寒論》中也處處體現了方劑辨證論治思想。六經辨證對六經本證的論辨只占《傷寒論》中較少內容,而論中大部分是論述變證的辨證施治,所謂變證就是壞病,即癥候錯綜復雜,變化多端,難以用六經命名者。那么,仲景是用什么辨證方法呢?其實用的就是方劑辨證。盡管在《內經》中已有八綱辨證、臟腑辨證的內容,但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所以仲景并沒有明確地使用這些辨證方法,后世給冠以熱證、虛寒證、以及心陽虛證、脾陽虛證、腎陽虛證等,只是為了學習、歸納方便后加上的。《傷寒論》原文都是先述病因,然后羅列主癥、或然癥,再述方藥及加減,實際這就是方劑辨證。目前,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從五版以后均以方證命名,是比較符合原意的。《傷寒論》中的方劑,已經有了比較固定的藥物組成和適應證,因此論中多次提到桂枝證、柴胡證、大青龍湯證、桂枝甘草湯證、小建中湯、桃核承氣湯證等,仲景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這些湯證的病因病機、主癥、治法、方藥及加減,形成方劑辨證的原型,后世醫家在理論和實踐上采用的“方證相對”(即方劑辨證)法,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傷寒論》六經辨證方法和方劑辨證方法是并行不悖的兩種方法,方劑辨證是對六經辨證的補充,限于當時的社會和醫療條件,常見失治誤治,病情致變復雜,當不能用六經命名時,仲景便采用了方劑辨證方法。實際上六經辯證是綱,進一步選擇何方藥時,還需方劑辨證。僅以太陽病為例,太陽病分為太陽中風、太陽傷寒,分別選用桂枝湯、麻黃湯,這是典型的六經辨證,但是在太陽中風的基礎上,若出現頸項強直、喘、汗漏不止、脈沉遲身疼痛,這就變成了桂枝加葛根湯證、桂枝加厚樸杏子湯證、桂枝加附子湯證、桂枝新加湯證,后者主要是使用了方劑辨證。至于太陽病變證更是使用了方劑辨證方法,基本上“有是證用是方”“方證相對”,在參考病因的基礎上,重點根據所現脈證(即臨床表現的癥候群),確定病機治法與方藥。因此方劑辨證亦為《傷寒論》中的主要辨證方法之一,是值得加以發掘提高和廣泛應用的。
4 方劑辨證與方劑學和其它辨證方法的關系
方劑學是研究方劑配伍規律及其臨床應用的一門學問,主要是研究方劑的藥物組成、功用主治、煎服方法、配伍意義,組方規律、臨床應用等,其中以研究藥物間的相互關系和功效為重點;而方劑辨證則主要研究各方劑的主癥、兼癥及產生的病因病機、治法、方藥加減變化規律和臨床應用,其中以研究主癥、病機、方藥臨床應用為重點。由此可見二者的研究方向大不相同。方劑辨證與其它辨證方法是相互補充、相互為用的關系,臨床上方劑辨證方法既可單獨應用,又可與其它辨證方法結合應用。方劑辨證方法和其它的辨證方法一樣,都有它的適用范圍,方劑辨證中的方證不可能概括臨床所有的病癥,不完備的必須用其它辨證方法加以補充,而其它辨證方法不完備的,也需用方劑辨證補充完善。即使在方劑辨證體系中也離不開其它辨證方法,如對某一方證進行治療時,在使用該方劑的同時常常要進行加減,加減時就要根據其它辨證方法分析兼癥產生的病因病機,然后再選擇藥物,因此臨床上應掌握更多的辨證方法。
方劑辨證論治方法雖然起源很早,至少應和六經辨證同源于《傷寒論》,但這一辨證方法并沒有引起歷代醫家的廣泛重視,故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以至這一簡捷有效的辨證方法面臨失傳。近年來雖有學者相繼提出這一辨證方法,但只是考證了源流,討論了方劑辨證與方證規范化的個人見解,尚沒有具體研究結果。受古代醫家及現代醫者的啟發,筆者認為,首先,方證的選擇應是重要的第一道關;其次,方證主癥兼癥的確定應是重要的第二道關;再次,確立正確的治法是方劑辨證論治方法重要的第三道關。
[1]顧武軍.《傷寒論》方證辨證探析[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5,11(2):20-22.
[2]朱邦賢.方劑辨證與方證規范化之我見[J].上海中醫藥雜志,1997,11(1):2-5.
[3]程磐基.《傷寒論》湯方辨證源流研究與思考[J].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1999,13(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