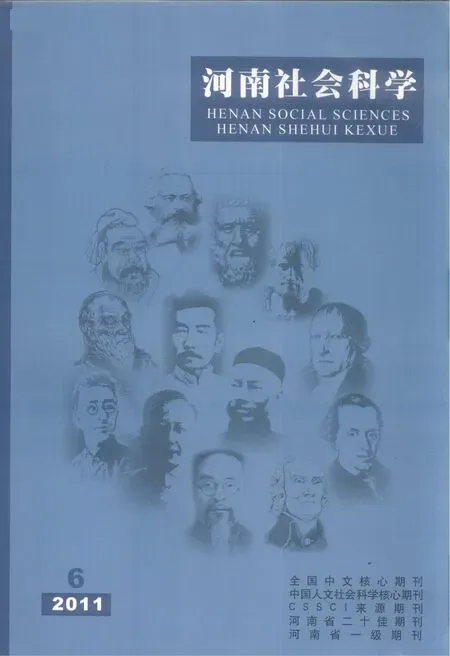客觀的偏至
——從另一角度看現時代新詩研究的特點
龔云普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客觀的偏至
——從另一角度看現時代新詩研究的特點
龔云普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自新詩陷入危機后,現時代的新詩研究似乎特別強調歷史的、客觀的態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轉新詩的不利處境。現時代新詩研究從微觀的視角,即不再像以往那樣從宏觀角度探索新詩本質、發展規律,而是特別注重研究新詩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詩現象,從微觀的視角切入并呈現新詩內部的復雜性、多層次性。告別宏觀研究的另一體現,則是現時代新詩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學術研究范式,靈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詩的歷史與現狀,從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詩問題。現時代新詩研究向宏大詩學體系告別,在重新思考新詩的發生以及新詩典型現象的過程中,也在建構自己的詩學觀念,所不同的是,他們的詩學主張建構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現時代新詩研究運用反二元對立的思維重新審視新詩典型現象,通過回溯新詩的發生以及發展過程,在史料的梳理與辨析中澄清新詩的歷史的、藝術的傳統。雖然沒有正面回答“新詩是不是詩”、“新詩的標準是什么”等本質問題,但在探尋新詩的別樣發生、語言特性與發展過程中,揭示了新詩存在的價值和發展前景。新詩將在危機中迎來新的生機。
新詩研究;客觀;反二元對立;史料;指向
自新詩陷入危機后,現時代的新詩研究似乎特別強調歷史的、客觀的態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轉新詩的不利處境。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盛行的理論批評而言,北京大學推出的幾本屬于“新詩研究叢書”的專著①,則表現出偏至的客觀態度,雖然它們也借鑒理論,但是理論在研究過程中始終居于次要的、輔助的角色。研究者不太愿意進行宏觀層面的詩學研究,而從微觀的角度切入,運用反二元對立的思維重新審視新詩的發生以及發展過程,以期澄清多元的、有效的且屬于新詩的藝術傳統。它們揚棄傳統的、非歷史的本質主義研究范式,雖不直接正面回答“新詩是不是詩”、“新詩的標準是什么”等本質問題,但仍舊試圖展示新詩存在的價值、發展前景,采取“曲線救國”的方式消除新詩的危機。
一、告別宏觀的建構
告別宏觀的建構,就是新詩研究不再像以往那樣從宏觀角度探索新詩本質、發展規律,而是特別注重研究新詩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詩現象,從微觀的視角切入并呈現新詩內部的復雜性、多層次性。我們知道20世紀90年代新詩研究,受“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的影響,出現了建構現代主義詩歌體系和撰寫現代新詩史的高潮。諸如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詩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新詩研究著作20多部先后出版。這些厚實的研究成果極大地促進了新詩研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完整和流暢的體系遮蔽了新詩本身的多樣性、豐富性。
《“新詩集”:中國新詩的發生》(以下簡稱《新詩的發生》)明顯地表達了告別宏觀建構的研究態度。作者在“導言”中以注釋的方式批評了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的宏大敘事,認為龍著“循環著由合—分—合的規律,即肯定—否定—肯定的辯證發展過程”,忽略了新詩發展過程中具體的濃密性與多樣性[1]。以黃河比擬龍著,如果說黃河具有直奔大海的磅礴氣勢,那么《新詩的發生》就僅僅是黃河的源頭,不僅論題小,只考察“中國新詩的發生”的問題,而且范圍小,以1919—1923年出版的個人或集體的“新詩集”為對象。研究者只想以新詩發生為原點,仔細地梳理在這點上縱橫交錯的促發新詩誕生的種種因素,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影響。研究者后來回憶撰寫博士論文的初衷時曾說:“我所要做的其實不是要正面建立什么,也不是想消解什么,而是想通過還原的工作,恢復新詩史的彈性,所謂‘新詩發生的內在張力’這個命題的提出,不過是為了打破一種線性的歷史想象,更多呈現出共時狀態的纏繞與差異。”[2]這說明作者是想將單一性的新詩歷史盡量還原為一幅叢聚著多種可能性的微型畫卷。
考察新詩的發生,如何認識胡適、郭沫若在新詩史中的位置是最復雜的問題,尤其是胡適在新詩發生中的作用。歷來的新詩研究采取就詩論詩的態度,自然很難再發掘出“胡適之體”的重要意義。《新詩的發生》運用文學社會學方法,恢復出由創作、閱讀、出版與批評等多種因素所構成的場域。在這立體的新詩發生背景中,文學史“抑胡揚郭”的秘密由此被揭開:其一源于錢玄同在“序言”中框定《嘗試集》為“白話文運動”工具的定位;其二在于胡適本人編輯《嘗試集》以呈現新詩進化的刻意追求;其三是郭沫若的《女神》順應了時代精神的召喚和讀者的閱讀期待,并以抒情為本的“詩美”風格,扭轉了新詩發生的格局。于是,“幾乎是‘共時’發生的詩歌向度(《嘗試集》與《女神》的出版先后只差一年),拉伸成‘歷時性’的分期”[1],《女神》也就成為通行文學史教材所認可的“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作”[1]。如此看來,關于新詩的發生,胡適于其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胡適之體”作為初期白話詩代表,還蘊涵著理解當代詩歌日常生活化的藝術基因。《新詩的發生》結合胡適留學美國的西方文化背景,從詩學角度揭示了倡導白話詩的“現代性”意義:擴大了新詩“包容歷史遽變中嶄新的事物和經驗”的表意能力。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散文化探索、對現代日常經驗的包容等方案,非但不是工具意義上的過渡,反而似乎是另一條被埋沒的線索”[1]。新詩不只是抒情的單線發展路線,胡適開創的寫實的詩歌,也是新詩發展的重要路向。而且,可以說這一路向正是新詩大眾化詩學的源頭。對它的發掘,有助于理解新詩為何存在純詩化和大眾化兩種詩學的糾結,為何當代詩歌出現以“口語詩”為代表的日常生活化傾向。這與新詩發生時就含有“胡適之體”的基因有莫大關系。
告別宏觀研究的另一體現,則是現時代新詩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學術研究范式,靈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詩的歷史與現狀,從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詩問題。《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以下簡稱《新詩話語研究》)以新詩話語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詩的格律、人稱以及資源等方面問題。盡管研究者的論述偏重現代主義詩歌,并有意凸顯新詩的現代性本質,體現出本質主義思維方式,但是全書以類似“典型案例”的形式,對新詩現象散點透視,雖不謹嚴卻靈活地揭示出新詩語言的歷史問題和當代新詩嬗變的聯系:“語言轉型的不徹底和未完成狀態,為新詩運用語言留下了粗糙、倉促的禍根。”[3]于客觀研究中寄寓著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思考。尤其是研究者對“中國新詩的對應性特征”分析,通過辨析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派和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從詩學氛圍到詩歌觀念、主張和實踐的內在相通”[3],呈現出新詩別樣的、周期性回環的發展特點,打破了以往的單線性、進化論式的新詩發展觀。
現時代新詩研究向宏大詩學體系告別,在重新思考新詩的發生以及新詩典型現象的過程中,也在建構自己的詩學觀念。所不同的是,他們的詩學主張建構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
二、反二元對立的思維
1993年鄭敏先生發表長文《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以下簡稱《世紀末的回顧》),批評胡適、陳獨秀倡導新文學運動態度的簡單、急躁,認為他們缺乏文學改革要在語言具有繼承性的原則上展開的理論認識,而以“簡單化的二元對抗邏輯”處理“白話文/文言文、傳統文學/革新文學”的關系[4],從而導致了20世紀中國新詩成就不夠理想的嚴重后果。此文一出,劇烈地沖擊了現代文學研究界關于五四新文學尤其是關于現代新詩的共識。時隔10年,劉納先生針對鄭敏先生的批評給予了沉穩的回應。她在長文《二元對立與矛盾絞纏》中指出,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的二元對立思維具有并非簡單的“復雜糾纏”,而且二元對立也“不是五四新文學倡導者的發明,也并非西方結構主義者的發現,它有十分久遠的淵源”[5]。這篇論文以宏闊的視野、縝密的辨析,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理論以及歷史流變的復雜性,也為現代文學、現代新詩研究走出“二元對立”思維框框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
新詩問題的實質是語言問題。同樣是在《世紀末的回顧》一文中,鄭敏先生以大篇幅梳理百年中國新詩“三次面臨的道路選擇,而三次都與語言的轉變有緊密的關聯”的發展歷程,以呈現胡適、陳獨秀等“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的負面影響[4]。鄭先生的警示沉重而中肯。它對現時代新詩的語言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一,改變了文白對立的二元對立思維。在《新詩話語研究》中,研究者充分認識到現代漢語源于白話的浮泛性和簡單化,不如古典漢語具有“天然”詩意等缺點,在承認“現代漢語已經成為不可更改的客觀性存在”的前提下,重新審視歐化語言、古典語言與現代漢語的關系對新詩發展的作用。在第一章“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20世紀中國新詩語言問題”,也是全書提綱挈領的章節中,研究者就將白話與歐化、古典與現代、口語與書面語等二元對立的單項,統統整合成現代漢語的語言資源,曾經被視為對立的單項依次成為校正、補充、供給現代新詩發展的重要資源:“歐化”“為先天不足的白話語言注入詩性的營養”,古典與現代漢語的“承續性”有益于新詩的本文建構等[3]。
其二,改變了以新舊論詩的詩歌觀念。在分析“‘四五’詩歌運動的詩學意義”中,研究者從“四五”與“五四”運動具有對應性的特征入手,揭示新、舊詩歌之間對立與承繼性關系:晚清詩界革命之于“五四”新詩,“四五”詩歌運動之于當代朦朧詩,除更迭方向有順逆之別外,都是“舊”與“新”的替代和轉承。在研究者看來,它們暗示了“中國詩歌自我更替的某種特性……中國舊詩內部從‘詩騷’到‘樂府’……詩、詞、曲的嬗變是如此,中國詩歌由舊變新亦應如此”[3]。新詩與舊詩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中國詩歌內部自我更替的表現。
此外,在《新詩的發生》中,研究者突破了文學史對于“新青年”陣營和學衡派的改革/保守、進步/反動的簡單劃界,而從新詩合法性的角度將二者的論爭視為新文學內部的問題,認為胡適等詩人恢復詩歌對現實經驗的關注和“學衡派”注重詩歌普遍性的承傳,實是“新詩發生的基本張力的一種顯現”[1]。
后來劉納先生在總結學界追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特點時如此說道:“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不但‘二元對立’成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貶義詞,而且應該說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組二元對立:反二元對立/二元對立。‘反二元對立’成為這組二元對立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單項。”[6]言語中盡管有些戲謔學術跟風的意味,但它切實地揭示出近些年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突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更全面更客觀地去認識、理解現代文學及其歷史。現時代新詩研究體現了這種發展趨向。
三、注重史料的整理
學術界倡導“論從史出”的呼聲持續不斷,但一直未引起普遍的重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急追先進的西方文化,那時的學界就表現出偏重“以論帶史”的傾向。而今,隨著商品化的邏輯逐漸滲進學術研究的領域,為獲得學術“創新”及其附加的經濟效益,直接套用西方理論隨心所欲地進行文學研究,忽視史料研究的現象就更嚴重了。
中國現代新詩研究也存在著不重視史料研究的問題。劉福春先生在評述20世紀新詩史料工作時就指出:“對史料進行深入研究和進一步開掘的工作還少有人問津。”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所用多為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很少能從原始資料開始”等問題的存在,致使“很多研究總是今天依據一個新材料,明天又靠一個新發現來不斷修補新詩史,沒有詳實的史料占有,研究工作很難游刃有余”[7]。
重視史料對現代文學研究、對現代新詩研究有重大意義。2004年2月《學習與探索》刊發了一組文章,探討“史料建設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義”。參與討論的學者認為,文獻資料的搜集與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工作之一,在此堅實基礎上產生的成果更有可能是較為科學的。秉持客觀的研究態度爬梳、整理史料,“自覺地以自己的努力呈現史料發掘與人的自我發覺的內在聯系,以自己生動的實踐展示‘史’建設之于現代思想建設的一致性……將可能喚起更大范圍里對于歷史遺產的重新認識,從而推動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進一個新的境界”[8]。否則,將致使論文“因缺少‘根據’而造成學術含量的稀薄”[9],甚至將文學研究變成消費各種理論的大生產運動。
2008年出版的《新詩的大眾化和純詩化》(以下簡稱《大眾化和純詩化》)體現了現時代新詩研究重視史料的學術追求。該書選擇新詩詩論為研究對象,抽繹出新詩“純詩化”和“大眾化”兩種詩學線索對立發展的內在邏輯,完全是從新詩史料的重新整理與排列中提煉出來的。對于史料,研究者表現出極端的重視,從第一章“新詩平民化和貴族化論爭”至第五章“40年代大眾化詩學體系的構建和純詩復興”,用了占全書近2/3的篇幅,梳理兩種詩學的夾纏與發展情況。其中所涉及的詩評家及其理論,倘若與楊匡漢、劉福春編集的《中國現代詩論》進行比照,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論從史出”需要證據,需要在“據有”史料的前提下展開“論”,展開辨析。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廣泛搜集史料,觸摸歷史現場只是確保了論述的充分性。研究者還必須整合所有的史料,歷史地、客觀地發掘出其中的邏輯聯系,形成自己的“史識”。《大眾化和純詩化》的“史識”——大眾化和純詩化兩條詩學線索,源于五四初期俞平伯和周作人、梁實秋等關于詩歌的貴族化和平民化論爭,貫穿于現代新詩發展的整個過程。并且,受西方詩學和時代風云的雙重影響,它們相互對立、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研究者正是以此史識審視新詩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現象,才獲得了學術研究的創新。諸如:將梁實秋的貴族化詩學主張和后來的新月詩派,尤其是后者與中國詩歌會的論爭聯系起來,這“是這一場論爭以前不為我們所注意的一個方面”[10]。又如,只有認識到抗戰爆發后,香港的文學氛圍相對寬松、自由,才使純詩化詩學有機會向大眾化詩學主動出擊,才能發掘出梁宗岱提倡純詩理論的詩學史意義及其為文學史家所遺漏的詩學論文[10]。
《大眾化和純詩化》對于現代新詩“內在的詩學邏輯性的概念或范疇進行專題性研究”是具有自覺意識的[10]。它的論述不存在“先入為主,以論代史”的空疏,或者“只及一點,不及其余”的片面。在現時代為數不少的新詩詩學研究著作中,該書展示了新詩史料研究的學術魅力。
四、客觀偏至的指向
上述研究成果雖各有側重,但不約而同指向了新詩為人所詬病的幾個問題:“不定型”、“口語化”和缺乏詩歌的評價標準。其中,“不定型”是新詩存在意義被質疑的最終根源。“直至‘五四’之前,中國歷代詩人和詩評家都不必去探尋詩存在的意義和理由,也不必去追究什么是詩、什么不是詩,而對新詩本體的追問卻貫穿著它自誕生起近九十年的全部過程。”[11]以口語為基礎的白話新詩,拋棄了古典詩歌“無韻則非詩”的定律,同時帶來了缺乏統一的詩歌評價標準的問題。在這問題的背后實則隱藏著以舊詩的標準衡量閱讀新詩的心理。
受時代風氣、審美取向、藝術修養等影響,文學欣賞、批評很難給出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詩歌尤為突出。古語云:詩無達詁。今人則有“了解一個人雖說不容易,剖析一首詩才叫‘難于上青天’”的感嘆[12]。在現時代,“作者/讀者系統的瓦解”已經極大地“改變以往的文學價值體系”,導致權威批評家、權威批評的缺失[13],更加劇了關于“何為新詩”討論的混亂。既然各說各話,那么不如看看新詩的發展歷史。現時代新詩研究偏重客觀態度的動機與意義,也就在于此。
針對新詩能否像舊詩一樣“定型”的問題,上述研究從認識論,從新詩的發展歷史和詩學建設方面,給出了“不能定型”的答案。若以復句形式言之則為:運用白話文寫詩,是為了“要擴大詩歌的表意能力,包容歷史遽變中嶄新的事物和經驗”[1];新詩出現口語化、散文化,則是因為現代漢語強調口語,雙音節、多音節詞匯增多,同時“受到西方語法的影響,現代漢語在句子結構上更復雜”[3]。既然新詩不能定型,它將在大眾化和純詩化兩種詩學的互相影響中呈“鐘擺式”地向前發展;由于詩人創作的著重點不同,“懂”與“不懂”的問題一直存在,因為“不懂”是“現代詩的本質要素,也是其獲致藝術效果的基本條件”[10]。客觀研究表明,新詩不能定型。
另外,新詩研究的客觀偏至態度的意義還在于:通過考察“新詩的發生”,揭示出讀者接受、書局出版等因素的促進作用,提醒我們不能照搬舊詩標準來讀新詩;新詩的“大眾化”和“純詩化”詩學研究,則有助于我們反省當代口語詩的實驗:既要從個體的日常生活中獲得詩意,又要錘煉詩歌的創作技藝。
早在1935年,批評家李健吾就說,新詩“離開大眾漸遠,或許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止”,其“最大原因,怕是詩的不能歌唱”,因為新詩“歌唱的是靈魂,而不是人口”[12]。現代新詩無需“定型”來安身立命,“不定型”或許是它的宿命。新詩將在危機中迎來新的生機。
注釋:
①“新詩研究叢書”是洪子誠先生主編,自2005年4月始由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推出的系列新詩研究成果。本文主要涉及其中幾本著作:姜濤的《“新詩集”: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版),張桃洲的《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版),劉繼業的《新詩的大眾化和純詩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版)。姜著是作者在2002年博士論文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張著雖屬論文集,但是有較強的系統性。有些文章成文于上世紀90年代末。因此,從時間上來說,他們的論著較能體現出從本世紀初至今新詩研究的一種傾向。
[1]姜濤.“新詩集”:中國新詩的發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冷霜,等.討論《“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A].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3輯)[C].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173.
[3]張桃洲.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J].文學評論,1993,(3):5—20.
[5]劉納.二元對立與矛盾絞纏[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4):1—22.
[6]劉納.當下對“五四”的追溯:面對解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1):13—19.
[7]劉福春.20世紀新詩史料工作述評[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3):245—272.
[8]李怡.歷史的“散佚”與當代的“新考據研究”[J].學習與探索,2004,(1):118—120.
[9]劉納.研究的根據[J].學習與探索,2004,(1):111—112.
[10]劉繼業.新詩的大眾化和純詩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1]劉納.新詩的評價尺度與新詩欣賞[J].粵海風,2004,(5):67—69.
[12]郭宏安.李健吾批評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13]劉納.從作者/讀者系統的瓦解談文本的解讀[J].學習與探索,1999,(5):102—106.
I2
A
1007-905X(2011)06-0148-04
2011-07-21
龔云普(1971— ),男,江西吉安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惠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呂學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