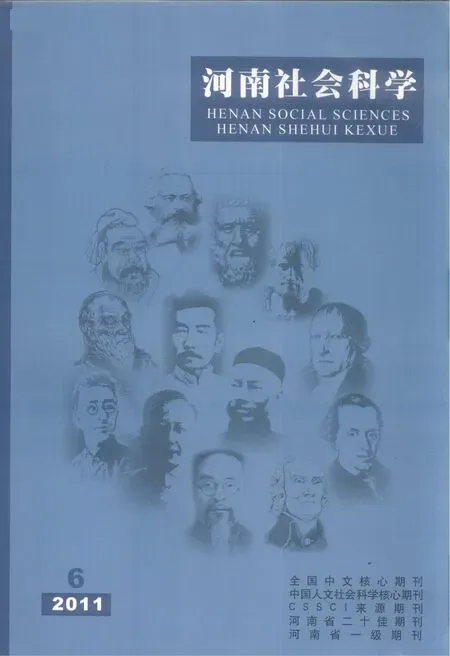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世界工廠”變遷的文化動因
——文化何以主導制造強國變遷
張明之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世界工廠”變遷的文化動因
——文化何以主導制造強國變遷
張明之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全球化的重要貢獻不僅在于推動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在于推動著各國制度的變遷,這些重大變化極大地降低了要素結構、制度選擇與政策體系對不同國家的重大影響,各地區間要素結構與交易成本的差距趨于收斂。但由特定文化所決定的文化終極影響力、本地文化的根植性、文化的信息傳播價值和文化的學習價值的差距卻依然存在,文化成本的差異成為決定區位競爭優勢進而主導制造強國變遷的深層因素。“世界工廠”的變遷歷程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世界制造強國;變遷;文化;文化成本;區位競爭優勢
一、引言:文化是如何改變要素成本與交易成本的?
高波(2004)的開創性研究認為,文化是人們所習得的與遵從的特定價值觀體系,文化成本是人們習得和維持特定價值觀念為核心的文化傳統所放棄的物質上或心理上的最高代價(成本),或者說是文化觀念轉變所付出的代價[1]。據溫特的理解,“文化雖然有著保守的色彩,但卻總是使文化負載者之間進行著競爭,這種競爭成為結構變化的不竭源泉”,“文化包括許多不同的規范、規則、制度,這些內容誘發的實踐活動常常是相互矛盾的”[2]。文化既有內斂穩定的傾向,又易受外力影響而改變文化秩序,更能夠由內部產生新的觀念。不同的文化特質,會影響甚至左右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本地文化環境和信息渠道及由此決定的本地創新和技術變革的力量,是造就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全球化推動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各國制度的變遷,基于市場經濟的規則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同和采納,這些重大變化極大地削弱了要素結構、制度與政策戰略體系對不同國家的重大影響,各地區間要素結構與交易成本的差趨于收斂。然而,由特定文化所決定的文化環境、信息渠道和技術儲備的差距卻依然存在,并成為決定區位競爭優勢的關鍵。亨廷頓對20世紀后期加納和韓國的發展歷程的深入考察也印證了這一觀點[3]。文化成本能夠深層次地和持續穩定地作用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進而決定著波特所謂的“地點競爭力”。
從世界工廠的成長與變遷的規律中可以發現,文化因素發揮著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經濟學文獻始終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但“世界工廠”的經濟含義至少包括:其一,該開放的經濟體較深入地參與了世界分工,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工業制造領域具有競爭優勢和無可替代的國際地位,而并不一定具有唯一性和處于壟斷地位。例如美國經濟的成長主要以國內市場為支撐,在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霸主時,其制造業的世界市場份額也不到20%。其二,該經濟體在制造業領域或該領域某個制造環節的優勢地位,使其成為世界主要制造產業鏈的主要環節之一,與其他經濟體可形成替代或上下游關系。其三,世界工廠是一個歷史的和動態的概念,它必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際分工格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變化。由于國際分工深入發展,世界工廠的內涵已歷史地發生了變化,其制造中心的功能越來越突出。世界工廠形成的基礎在于地點競爭優勢,取決于總成本差異。在全球化與網絡化條件下,要素成本與交易成本的差距逐步得到縮小,而文化成本的差異則成為決定地點競爭優勢的關鍵。
培育和形成以創新與競爭為核心的區域文化,是降低文化成本和提升地點競爭力的主要途徑,具體表現在如下若干層面:一是文化的終極影響力。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主導性文化價值觀通常表現在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及風俗習慣上。主導性文化價值觀對世界制造強國的變遷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它甚至決定了特定時期技術的進步、生產組織方式的選擇和制度的建設。二是本地文化的根植性。本地文化環境決定了企業在特定經濟空間的根植性,即企業運行是嵌入于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之中的。在生產過程中相互關聯的企業聚集,通常在一個產業內,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區。這種文化—制度的一體性組織構架是促成區位競爭優勢的堅實保證。三是文化的信息傳播價值。信息迅捷且低成本流動的主渠道依賴于本地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共同的人文環境產生的信任、理解和相互合作,既能有效地防止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又能促進有價值的信息和知識,尤其是隱含經驗類知識與信息的流通和擴散,這是外地競爭者很難復制的。相互信任和滿意成為區內最有價值的信息資源。四是文化的學習價值。積極的本地文化環境有利于促成一個學習型經濟區域。創新是一種交互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過程,成功的創新需要一種創新文化網絡環境。在技術和市場迅速變化的非線性環境下,企業間的競爭合作具有明顯的學習性和交互性,創新網絡中的各行為主體之間相互學習,密切合作,共同推動區域的發展和企業的持續創新。總體而言,文化因素對特定經濟區位的競爭優勢的影響力在于,對于給定要素結構和制度背景的經濟體來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要素結構、交易成本等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正如波特所言,文化成本反映了人們對待創新的態度。在生產過程中,特定文化所具有的成本狀況最終會反映在產品的成本上,或者說,它通過影響效率和創新而改變了企業總成本狀況[4]。
二、主導性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英國世界工廠衰落的文化因素
英國是第一個公認的世界工廠。英國文化素以正統自居,即英國的主導性文化以維護、宣揚英國的正統文化價值觀為主基調。由于正統,因而謙和、寬容,能夠兼收并蓄,在保證傳統文化基礎上注意吸收改造外來文化、吸納利用外來人口的智慧,從而得以有效降低文化成本,進而改變當地的要素成本與交易成本。但也由于正統,因而固執、保守,不能根據經濟成長調整、塑造出符合社會進步與時代發展的新的核心價值觀,反而束縛了創新文化的發展,成為阻礙觀念更新與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
在產業革命前期,在開放觀念驅動下,英國形成了一個更為寬容的國家結構[5]:一是經濟政策領域中的政府管理實現了現代化。許多著名的學者,如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頓等都參與了公共政策的實際事務,對技術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二是公共財政體系的建立和完善。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并于1696年開始大規模重鑄貨幣。經過一系列的變革后,18世紀的英國已成功地建立起一套穩健的公共財政體系,這與同期法國薄弱的公共財政體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三是資源配置效率通過穩健的公共財政和銀行業的發展也進一步獲得了提高[6]。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不同,國內市場的統一程度通過創建收稅公路和渠道網絡以及海岸運輸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其結果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更有效率的專業化勞動分工。四是社會普遍形成了具有接納性而非排斥性的文化環境,有助于降低的文化成本。隨著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銷,法國有相當多的經管企業的人才流入了英國,尤其是在紡織工業方面。五是貿易政策從重商主義演變為自由貿易。16世紀以來,英國的商業政策受到重商主義思想的支配,認為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是衡量國家富裕程度的唯一標準。從1651年始,英國政府頒布的一系列關稅、補貼及貿易法等政策,形成了一種新的貿易模式,即從殖民地進口的商品大量被用于再出口(將用于出口的貨物先運到英國后再出口)[6],以高額關稅擠壓從屬國的產業競爭力。有學者指出,英國政策在18世紀的勝利,同時也是重商主義的勝利[7]。隨著英國的日漸強盛,19世紀20~30年代,英國的商業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英國政府開始廢除一些除關稅以外的保護性政策,自由主義取代重商主義成為促進經濟增長、鞏固國家權力和安全的主要手段。盡管19世紀末,貿易自由化在歐洲出現倒退,但素以正統自居的英國到1931年仍堅持其自由貿易政策。自從英國于1763年確立了領先全球的軍事優勢后,其統治疆域遍及全球,成為英國民眾的帝國情結的強大支撐。英國商業與貿易政策的成功,與英國強大的海上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軍事力量保障其政策的施行,其政策的成功極大地改善了財政狀況,得以繼續維護遍及全球的防務,以支撐其“日不落帝國”的“榮光”。
隨著在1860年前后英國世界工廠達到鼎盛時期,英國正統文化便日益顯露出固執和保守的一面。早在1851年水晶宮大博覽會期間,已有人注意到了英國不少行業存在著衰弱表現,并指出,19世紀50~60年代的商業狂熱很可能會使“世界的工廠”變成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自滿情緒的搖籃[8]。盡管英國是產業革命的先驅,重大的技術突破總是首先發生在英國,但到19世紀中后期,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總體進步和產業革命在歐美大陸國家的普及,產業技術的一些新的重大進展多發生在新興工業國,主要集中于美國和德國。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個時期的新興產業絕大部分興起于其他國家;并且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新興產業在英國的投資都是由外國人進行的;由此可證明,英國缺乏新人”,這根源于英國文化的固執性與保守性。“總體而言,英國企業家是在等待別人來解決瓶頸問題”,“與發明、創新和高層次的專利相對稱的、意義最為重大的問題或許是不能解決那些在別的地方已經解決的技術問題”[9]。由于英國長期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技術向海外擴散較產業革命初期更為暢通。當時英國在棉紡織、煤炭、鋼鐵(包括鐵軌、屋頂材料使用的鍍鋅鐵片)以及鐵路設備等老工業領域,產品和生產工藝方面的技術改進進展緩慢,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工、電力、汽車——常常要依賴外國企業家[10]。企業家偏愛固守既有的優勢而缺乏技術創新的精神,“缺乏打破已經形成的模式的意志力”[11],是英國產業技術發展停滯的重要原因。當具有競爭力的現代工業在新興國家開始興起,并且產品質量在短期內迅速得以提高之后,英國廠商開始成為模仿者。19世紀80~90年代,英國在許多產業領域,尤其是化工、電器和汽車工業,都成為美國、德國的追隨者和模仿者。
產業革命的一個重大成果便是工廠制這一符合現代生產要求的組織方式得以確立和鞏固。然而,產業革命在歐美的普及推動了工廠制生產組織方式的普及和復制,并且“后發優勢”使得這些國家能在英國工廠制模式基礎上探索更合理的生產組織體制,使得英國迅速從領先者的神壇上跌落下來。在美國,家庭控制的大企業基本上被多單位聯合體所取代,領導者是職業經理人。1871年后,在德國的許多大企業中,雖然以家族為單位的資產所有者仍把持著戰略性決策權力,但企業內部已開始實行優勝劣汰的分組管理,擔任高層領導的通常是那些技術能力強、才識出眾的人,企業的組織管理已趨于有序化。而英國很多工業領域仍是眾多小公司的激烈競爭。英國“幾乎沒有向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離邁進,也沒有向組織等級制邁進”[12],在大多數行業中同整個19世紀一樣,家族制依然占主導地位。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法人企業都未能在國民經濟結構中占據最終支配地位。例如,英國的造船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生產了世界船舶總噸位60%~80%的船只。但英國的造船業只按照自己的標準工作和按訂單生產,不去學習歐洲大陸、美國和日本的“組織更嚴密的競爭方法”,而“使用裝配線的生產方法也已在英國以外的地區取代制造手工藝式的生產方法”,“英國造船業的優勢遂逐漸削弱”[9]。
三、本地文化的根植性:自由主義文化對美國世界工廠興衰的影響
作為制度社會的典型代表,盡管自身也存在著演變發展,但美國自由主義文化倡導在約束下的自由,強調企業運行嵌入于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之中,即企業在特定經濟空間的根植性。由于民族形成的特殊性,美國文化自建國以來就表現為一個開放的、自由的特征:北美險惡的自然條件,培育了美國人頑強拼搏、艱苦奮斗性格;而北美豐富的資源等待著開發利用,培育了美國人開拓進取、敢于冒險的精神;美國歷史較短,沒有更多的歷史束縛,培育了美國人樂于向傳統和先例挑戰的精神。移民造成的種族多樣化之所以能夠對美國產生經濟上的回報,其原因是美國社會能夠吸納和利用各種文化中最優秀的精華[13],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和技術傳播。觀念的自由流動的重要性就在于這一自由促使技術的國際傳播、擴散與外溢。這些彼時的新技術對于美國的成長尤為重要,因為美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后來者,而且處于19世紀技術變革的臨界點上。在自由主義文化支配下,美國人認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把作為美國核心價值觀念的自由和民主觀念向世界推廣。一旦其科技水平與經濟發展超越他國,民族優越感就會膨脹,輸出美國模式就是其必然選擇。
破除傳統的重農主義觀點,確立以制造業為支柱的工業領先思想,是美國制造強國夢想的起點。18世紀的美國,正統的和主流的經濟思想依然是“本土農本主義”①:在所有行業中,制造業創造財富的效率最低,或根本就沒有效率;一個農業資源豐富的國家無需制造業(軍火等必需品除外)。1790年1月,美國眾議院要求財長漢密爾頓起草一份報告,旨在鼓勵和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從而使美國擺脫在某些必需品上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漢密爾頓在《制造業報告》中提出應當發展超出必需品生產的工業化觀點,即發展制造業。使制造業擁有優越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是勞動分工和技術,尤其是機器的應用。這一報告“孕育了現代美國的胚胎:如果要為結局如此變幻莫測,意義如此深遠的進展賦予一個具體日期的話,那么,正是這份報告設想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工業大國的宏偉藍圖”[14]。
自由競爭的文化氛圍和經濟體制成為美國吸引當時歐洲國家資金和技術的重要保證。美國內戰結束后,自由競爭式的經濟制度得以鞏固發展,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列強的資金蜂擁而來,并由此帶來了世界一流的工程和制造技術,以及先進的生產組織方式。早在20世紀初,美國吸引的海外資本就高達67億美元。在大規模地吸引外資,并進而吸引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來看,崇尚自由的文化根基和較為健全的制度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鼓勵創新是美國自由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在美國創新文化影響下,不僅是技術、產品方面的創新,而且生產組織方式的革新日新月異。由于血緣關系,歐美的信息交流十分頻繁,歐洲任何新技術動向都能在美國得到反映,其反映速度之快,往往超過歐洲鄰國。如歐洲人發明了DDT,還沒試產,美國人已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使馬鈴薯產量當年翻番。1837年英國發明電報,第二年美國就推廣使用。當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正陶醉在汽車制造業的技術領先中時,福特公司就設計開發出了T型車,通過大規模的裝配線生產大批量的標準車,不僅大幅度地降低了生產成本,而且極大地開拓了市場需求。在創新文化的激勵下,1850年,美國結束了完全照搬歐洲技術的歷史,走上工業技術創新之路。美國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產生了一大批創新技術,并迅速產業化,成為制造業興盛的主要力量。
美國崇尚自由競爭的文化及由此形成的自由競爭式的市場經濟制度,在美國經濟上升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樣是自由主義的文化,在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之后,特別是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破產后,這一原本是形成美國區位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區位競爭優勢升級的障礙。
本土文化優越感的膨脹導致美國的企業家并不注重文化成本的變動對交易成本、要素成本的影響,這成為二戰后美國制成品競爭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第一,以美國為中心設計全球經濟發展藍圖。產品、服務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是戰后經濟秩序的支柱。但在美國倡導下的不斷自由化,大體是被用來創造一個有利于美國企業的環境。盡管協定的條款是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接受才能執行,并且這些國家又都有各自保護企業的措施,但這些國家內部自由化的舉措,仍然是圍繞為美國企業創造更多機會的目標來制定的。第二,對標準化產品生產的過度依賴。美國企業通過盡可能多地銷售標準化產品來降低生產、銷售和廣告的單位成本以獲取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生產率迅猛提高。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是戰后美國牢牢占據世界領先地位的重要動力,但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經歷了一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人均GDP水平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也顯著提升,企業發展的動力轉變為提供質量更高、性能更佳、個性更鮮明的新產品,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方式已不再是最先進的生產制造模式。在日本推出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LP)方式后,美國依然陶醉于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方式之中②。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科技實力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國,以至“企業以為美國的實驗室是產生有用知識的唯一地方”[15]。這一過于自信和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價值觀和社會文化環境很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汽車工業為例,汽車工業曾經是美國最大的工業類別,但到1987年,進口車占總銷售額的比重從1955年的1%猛增至31%。日本和韓國進口車控制了廉價車市場,歐洲進口車則占領了高檔車市場。美國車在國際市場上的壓倒性優勢已不復存在。第三,不能充分迎合不同文化的需要。兼收并蓄是美國建國時期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當美國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功后,本土文化的優越感大幅度提升,以美國為中心的價值觀念深入美國人心,企業顯然無法也不愿了解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的商品需求和偏好。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更大的問題在于自負,認為美國人的愛好、美國人的經營方式和美國的產品是世界性的(或者應該是世界性的)”,結果,“油老虎般的美國汽車對歐洲人根本沒有吸引力,因為歐洲人必須面對的是較高的汽油價格和狹窄的城市街道”[15]。
政府對企業經濟活動的積極影響減少也是后凱恩斯主義時期美國自由主義文化的直接后果。喬治·斯坦勒曾列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干政府與企業界的關系、政府的角色,說明政府與企業界的相互關系的影響力與復雜性[16],但美國實行的是自由競爭式的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有限政府,減少對市場運行的干預。“美國不習慣于設計國家戰略來幫助其工業在世界各地與(其他國家)主導生產商抗衡”。例如,在微電子領域的所有重大的發明——晶體管、半導體芯片、計算機——都誕生在美國,但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微電子產業的市場份額由于受日本企業的挑戰而急速下降,其原因之一便是松散的小型美國企業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有組織的重量級日本公司抗衡。再例如在民用航空產業,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民用飛機生產商之一,曾經在與政府合作研制飛行器方面獲得巨大利益。但由于在民用航空產業中,軍事技術向民用技術轉移非常困難,公司無法獲取戰斗機和轟炸機的訂單,因而與政府的關系日漸疏遠。而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由于得到了英國、法國、德國等國政府的強力支持,迅速成為世界民用航空產業的主要競爭者。盡管波音公司是世界民用飛機技術的領先者,生產成本最低,但它卻無法保證其在銷售上也占先,因為空中客車公司可以依靠政府的融資向客戶提供優惠和信貸支持,在這方面波音公司無法與其抗衡[15]。
四、文化的學習與信息傳播價值:東亞文化與日本的社會技術環境
日本的文化遺產首先是儒教。在儒教傳統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下,日本社會尤其強調上下等級秩序,強調家庭觀念,鼓勵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鼓勵勤勉,鼓勵學習,鼓勵社會和諧;由此缺乏或不歡迎冒險的個人主義、對權威的懷疑精神。有學者認為,日本文化所造就的社會技術環境,使得日本缺乏原生性的創新,其技術力量主要集中于引進技術的模仿、改良和革新,形成了忠誠、勤奮、服從而有效率的勞動力隊伍[17]。
經過近代“明治維新”,日本已積淀了較為雄厚的工業基礎。開始工業革命時,電力已投入工業和家庭使用,這意味著日本企業“能夠直接從手工業階段跨越到使用電氣設備階段,可以說,繞過了蒸汽機時代”[18]。但受資源所限,工業化及其相關技術多依賴進口。然而在技術引進的發展道路問題上,日本最終選擇了德國式道路,這是符合日本文化的一次選擇。一份發表于1942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的技術合理性促進了專業化機械的高度使用,從而把工資成本降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因此,它們對原材料的使用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毫不吝惜的。而德國的技術合理性則著眼于盡可能地節約原材料,并以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或開發替代產品為對策,從而鼓勵了熟練勞動力的使用,盡管此舉意味著工資相對較高。”[19]顯然,這是日本基于資源短缺但勞動力豐富的條件,符合日本勤儉文化的必然選擇。在20世紀前半期,日本公司雇用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不僅僅參與研究和模仿西方的技術,而且也力圖使這些技術適應本國的需要。并且,“他們意識到,改變生產過程的某些細節能夠降低成本和增加公司利潤”,因此,許多企業建立了自己的但規模較小的實驗室,“只適合于完成引進和改造技術的任務而不適合進行大型基礎研究”[19]。戰后日本所選擇的技術模仿—革新范式在日本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二戰后,日本的技術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后20~30年。日本從引進技術成果入手,并在應用中吸收、提高和創新,建立了本國自主的科技體系和企業制度,僅用15~20年時間就走完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半個世紀所經歷的過程。
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繁榮,日本公司將進口技術與當地勞動力結合起來,獲得了非凡的高增長率。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后期,日本引進的長期技術合同明顯增加,最大數量的技術進口是在快速成長的機械、電子和化工產業領域,技術主要來自美國和德國。日本在實現工業現代化期間,包括引進技術的專利費用、進口成套設備和關鍵部件的費用及對引進技術的研發費用等合計共約500億美元。如果這些技術靠獨立研發,從發明到應用,最少要投入2000億美元以上;并且,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測算,靠國內獨立進行研發,當時一項科技項目從研究到投入生產一般需要10~15年,而從引進技術專利到投產平均僅2.5年。日本通過引進技術專利,大大縮短了日本追趕歐美國家的時間。日本引進的技術之所以能夠被轉化為工業增長的力量,主要在于兩個因素:
第一,引進的技術能夠與本地的改革創新相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日本意識到從模仿進口技術轉向開發獨創技術的重要性。技術引進只能定位于本國研究開發的補充而絕非替代,完全依賴于技術進口將遭受重大挫折,而且極易受制于他國。1952~1958年,日本公司雇用的研究人員數量增加了1倍多;1959~1975年則增加了2.4倍。與此同時,許多相互聯系的小型開發中心遍布全國。以1960~1961年為例,制造業用于研究的投資與技術引進金額相比,前者處于顯著的優先地位[19]。日本對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投入之比是1∶10,從而形成“引進、提高、再引進”的良性發展。以引進發電設備為例,1954年日本從美國引進了7萬千瓦的火力發電成套設備,接著又引進美國22萬千瓦大型發電機組的技術專利,在此基礎上,經過研究和仿造,1961年制造出32.5萬千瓦的大型發電機組。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已經能夠制造70萬~100萬千瓦的特大型發電機組,成為美國同類設備的強大競爭者。
第二,對引進技術的革新通常建立在面向市場的商業化開發基礎上。某種科學或技術上的突破“(的技術障礙)不存在于科學,而存在于工程學”[20]。日本在制造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實際上是其技術創新的產業化和商業化的領先,日本數控機床的成長歷史可以說是最好的詮釋。基于計算機技術的長足進步,日本開始通過計算機來把握和控制其他新出現的技術以及生產組織方式,最典型的是工廠自動化技術。工廠自動化技術與其說是一種技術,還不如說是一種生產組織方式,即圍繞計算機技術而運行的自動化生產體系。這一源于美國空軍與麻省理工學院合作開發的先進技術成果被帶到日本后公開傳播,數字控制技術很快被日本一些公共研究實體所掌握。1956年,富士通生產出第一個數字控制機床模型,此后擺脫了對麻省理工學院思想的簡單復制,一是設計了一個非限制的環形系統,大大簡化了機器的控制裝置,二是將最新的電子開發成果應用到設備中[19]。盡管美國是該項技術的原發地,但美國生產數字控制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軍事需求,其重點是高尖端的硬件和軟件的開發,“很少考慮實際成本問題,也確實沒有鼓勵在機械生產上減少花費以投入到商品化市場中去”[21]。而日本公司從一開始就是帶著明確的商業化目標去革新外國技術的,因此像富士通等公司不僅采用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前沿技術,而且也關注其他有助于降低成本和商業化推廣的相關技術,例如機器工業技術、微電子技術等。到1966年,富士通已成為世界上首家在市場上銷售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的企業。到1974年,日本公司在數控機床上的投資高達近50億日元,為日本的制造業技術能力的提升和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0~1974年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是日本經濟增長也絲毫不遜色,1973年美日的技術差距基本消除,到1979年,日本在主要制造業技術方面已取得了優勢。加入關貿總協定以后,日本在鋼鐵、石化、汽車制造方面引進、發明、應用了大量的新的技術,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到20世紀80年代已經全面地超過歐洲、趕上美國,并在鋼鐵、汽車等重點產業形成了遠高于美國的競爭優勢。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在新興的半導體產業技術方面又超過了美國,贏得了占全球半數以上的市場份額,確立了美國之后新的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特定文化傳統下形成的高儲蓄率成為日本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支撐。相對于美國,制造業對日本顯得更為重要,因為日本戰后造就經濟奇跡的關鍵在于其制造業的迅速崛起。1987年日本的制造業占GDP的29%,而美國僅占20%。日本制造業的地位大幅提升得益于日本政府和民眾的大力支持,其中高儲蓄率對制造業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支撐作用。在1960~1979年間,對日本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投入。而就資本的來源而言,美國的對外投資重點地區在歐洲,日本(制造業)獲得美國資本的數量微不足道,平均不到美國對外投資的3%[22]。這印證了日本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絕非靠外資(美國資本)的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得益于日本長期以來保持的較高的儲蓄率[23]為日本制造業所提供的較低成本的資本投入。日本文化所倡導的節儉勤勉價值觀,使得日本與美國在對待消費或投資上具有巨大差異[24]。
特殊的文化下的雇傭制度造就了忠誠勤勉的勞動者,成為日本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日本奇跡”中,日本公司的終生雇傭制、年序工資制和晉級制成為日本文化下重要的公司規范。日本雇傭制度深受其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在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日本制造業的成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工人的平均任職期比美國工人和歐洲工人的任職期要長得多,與年齡相關的工資增長在日本也要比在其他國家高得多。盡管日本雇傭制度比較死板,但它強化了雇員的自身的適應性,如通過分紅進行可變性補償,工作任務含糊以及工作的經常輪換,即所謂的“靈活的僵化”[13]。這一模式的有效性在20世紀80年代曾令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贊嘆不已,并引起不少歐美企業的仿效。日本雇傭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內部勞動市場基礎上的[25],其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培養員工的忠誠。蘭德斯指出,撇開其他的因素,就日本汽車制造業的強大競爭力而言,“日本人這種團結協作精神,這種個人為團體做出犧牲及超強勞動的精神,與西方體現和維護勞工自尊的勞資對立關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5]。
然而,由日本文化決定的原發性創新的缺失是導致日本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根源。日本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同樣也成為制約創新的重要因素。著名的技術專家大河內正敏在20世紀30年代斷言,日本的研究人員是有能力、有獨創性的發明家,但日本的弱點是不能將新的想法商業化,許多企業并不準備經歷漫長的開發過程,私人企業幾乎都不愿意冒險從事基本的技術創新,而是把精力和資金用于對進口技術進行改造[26]。在一項對美國和日本產業研究開發所作的最新比較研究中,曼斯菲爾德發現,美國企業只把R&D費用的1/3用于改進工藝技術,而把2/3經費用于新產品研究開發和老產品改進上。在日本,這個比例正好相反,大部分資金和精力放在工藝水平的改進上[15]。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整個90年代,日本產業更新的步伐停止了。由于缺乏持續的原發性的創新,日本已開始在諸如無線通信、多媒體、軟件、微處理器、網絡等新興增長領域落后于美國。日本制造業的出口份額在1986年達到頂點,此后即使在那些日本過去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中,比如,電視機、錄像機、音頻設備、照相機和半導體,出口份額也開始下降[27]。
五、結論
從歷代世界制造中心的成長與變遷中可以發現,文化因素發揮著最深層次的作用或扮演著最后決定力量的角色[28]。主導性文化因素決定著對傳統和既定秩序的遵循程度或創新意識,對外來文化的理解、包容、接受和融合,企業或個人的價值評判標準及由此決定的行動取向。文化成本的差異則成為決定區位競爭優勢的關鍵。誠如亨廷頓所言:“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樣式將對貿易樣式起決定性影響。商人與他們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國家把主權交給由他們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經濟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29]盡管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與巧實力概念備受爭議,但這些概念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來思考文化的非物質權力因素的價值。
注釋:
①其淵源為歐洲大陸的“重農主義”,但又強調了美國至上的要義,因而在美國被廣泛接受。
②當然,這與追求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所帶來的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和工作效率提升有密切聯系。
[1]高波,張志鵬:文化資本:經濟增長源泉的一種解釋[J].南京大學學報,2004,(5):104—114.
[2]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4]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5]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安格斯·麥迪遜.世界經濟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7]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8]Church,R.A.The Great Victorian Boom:1850~1873[M].London:Chelsea House,1975.
[9]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0]P.H. Lindert,Keith Trace. Yardsticks for British Entrepreneurs.In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11]Wiener,Martin J.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2]喬萬尼·阿瑞吉.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13]托馬斯.K.麥格勞.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14]里亞·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5]邁克爾·德托佐斯,等.美國制造——如何從漸次衰落到重振雄風[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8.
[16]George A.Steiner.Business Society (2nd ed.,) [M].New York:Random House,1975.
[17]Morishima,M.Why Has Japan“Succeeded”?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8]H.帕特里克.日本的工業化及其社會后果[M].CA: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
[19]苔莎·莫里斯—鈴木.日本的技術變革——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
[20]Mathias,Peter.Skill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from Britain in the 18th Century[R].i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75.
[21]Noble,D.Social Choice in Machine Design:The Case of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Machine Tools[A].in D.MacKenzie,and J.Wajcman,eds.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C].Milton Keynes and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82.
[22]威廉.M.布蘭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趨勢[A].馬丁·費爾德斯坦.轉變中的美國經濟[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2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民核算(第2卷:1974~1986)[M].巴黎:OECD,1987.
[24]加里·杰里菲,等.制造奇跡——拉美與東亞工業化的道路[M].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5]趙增耀.日本的勞動市場體系及其面臨的挑戰和新變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12):75—81.
[26]大河內正敏.新興日本的工業和發明[M].東京:日本青年館,1937.
[27]邁克爾·波特,等.日本還有競爭力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28]張明之.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通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形態的變遷[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3):14—19.
[29]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F11
A
1007-905X(2011)06-0089-06
2011-07-30
200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以來世界財富分配權控制方式的歷史變遷”(09BJL007);全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產業革命以來國際秩序、軍事戰略與大國崛起”(20100471847)
張明之(1970— ),男,浙江象山人,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研究人員,教授,經濟學博士。
責任編輯 姚佐軍
(E-mail:yui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