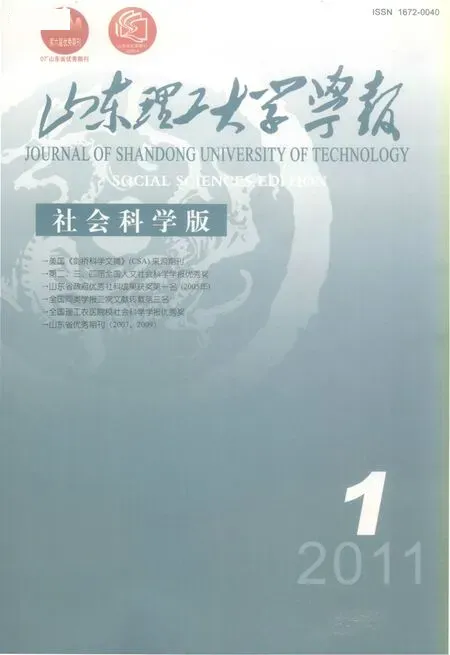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學(xué)科建設(shè)意義
張 玲,蔡梅娟
(山東理工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山東淄博255049)
近代文學(xué)批評,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五四前夕這段時(shí)間的文學(xué)批評,它與中國古典文學(xué)批評有著一脈相承的聯(lián)系。但自晚清以來,西方的哲學(xué)思想、理性精神等紛紛介紹到了中國,對中國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而使近代文學(xué)批評具有了不同于古代的特點(diǎn),它宣告了古典文學(xué)批評時(shí)代的終結(jié),同時(shí)也拉開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序幕,對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有學(xué)者指出中國文藝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始于近代,杜書瀛認(rèn)為從梁啟超、王國維們起,“現(xiàn)代文藝學(xué)的新學(xué)術(shù)范型在對傳統(tǒng)既繼承又革新之中萌芽、生長、成形”。[1]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作為文藝學(xué)下設(shè)的一個(gè)二級學(xué)科,其建設(shè)的起點(diǎn)實(shí)際上也始于近代。近代文學(xué)批評參照西方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理論框架,提倡文學(xué)批評的獨(dú)立地位,在批評思維方式、批評術(shù)語等方面都具備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某些特點(diǎn),并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的批評論文與專著。綜觀近代文學(xué)批評家的學(xué)術(shù)成果及努力方向,他們雖無明確的學(xué)科建構(gòu)意識,還沒有建立一門完備的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但卻在客觀上做著學(xué)科建設(shè)的努力。因此,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轉(zhuǎn)型不僅標(biāo)志著中國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建設(shè)的起點(diǎn),更重要的是為后來的學(xué)科建設(shè)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確立了開放性的學(xué)科建設(shè)方向。
一、近代文學(xué)批評標(biāo)志著中國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建設(shè)的肇始
“學(xué)術(shù)”一般被解釋為“有系統(tǒng)的、較專門的學(xué)問”。近代學(xué)者把文學(xué)批評當(dāng)作一門專深的學(xué)問來研究,在“學(xué)無中西”的跨文化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之上,自覺運(yùn)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進(jìn)行批評實(shí)踐,創(chuàng)造出了一系列新的批評理論,并逐漸形成了理論的體系化,近代文學(xué)批評家的學(xué)術(shù)自覺性標(biāo)志著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建設(shè)的肇始。
(一)文學(xué)批評作為一門專深的學(xué)問
19世紀(jì)末的文學(xué)批評在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肌體上,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可融性因素,兼容并蓄,孕育出具有新的生命力的批評理論。此種語境中生成的近代文學(xué)批評具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自覺性,主要表現(xiàn)為一種理論自覺性,批評家們借用西方的文學(xué)理論來觀照、闡釋傳統(tǒng)文論中某些理論命題,并創(chuàng)造性地得出一些新的理論,它們在“比古代文論更深的層面上展開對文學(xué)自身的性質(zhì)、特征、價(jià)值的認(rèn)識和探求,對文學(xué)活動(dòng)客觀規(guī)律的總結(jié)和把握,用新的觀念評價(jià)和指導(dǎo)文學(xué)創(chuàng)作”。[2]文學(xué)批評走了一條從理論到實(shí)踐再到理論(理論—實(shí)踐—理論)的路子。
一門學(xué)科的誕生、發(fā)展需要多種條件,但大都是從提倡研究對象的獨(dú)立開始的。我國古代文學(xué)史上并未將文學(xué)批評作為獨(dú)立的文學(xué)活動(dòng)來對待,多是“依經(jīng)立義”的教化論批評。近代社會,西學(xué)的輸入使得人們對文學(xué)觀念有了新的認(rèn)識,產(chǎn)生了對文學(xué)本體認(rèn)識的要求,這是一種理論觀念發(fā)展到對自身的省察的表現(xiàn)。王國維在研究康德、叔本華審美無功利論的基礎(chǔ)上,提出文藝“獨(dú)立”說,他在《論近年之學(xué)術(shù)界》中提出,“欲學(xué)術(shù)之發(fā)達(dá),必視學(xué)術(shù)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3]47主張文學(xué)藝術(shù)不為政治、經(jīng)濟(jì)利益所左右。這種超功利的“純文學(xué)”的觀念實(shí)際上是在追求文學(xué)的某種終極價(jià)值,是對文學(xué)批評理解的一種飛躍。
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學(xué)術(shù)自覺性還表現(xiàn)在批評思維方式的革新上。與古代文學(xué)重直觀感悟、整體把握的思維方式相適應(yīng),古代批評多是詩話、詞話、點(diǎn)評等,批評理論在顯示意蘊(yùn)深遠(yuǎn)的民族特長的同時(shí),也顯得邏輯性、系統(tǒng)性不強(qiáng)。近代知識分子認(rèn)識到了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思維方式的不足,有意識地吸取西方的思維方式來彌補(bǔ)之,如嚴(yán)復(fù)就曾致力于介紹西方的思維方法,他翻譯《穆勒名學(xué)》(形式邏輯),系統(tǒng)地引進(jìn)了演繹法與歸納法,試圖為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找到新的參照系。王國維也指出:“西洋人之特質(zhì),思辨的也,科學(xué)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3]41這一認(rèn)識使得他們開始借鑒西方的思維方式來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實(shí)踐。與批評思維方式的轉(zhuǎn)變相對應(yīng)的是批評術(shù)語的運(yùn)用與生成,它是思維方式的外在表現(xiàn)。近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者逐漸使用有界定而內(nèi)容不模糊的批評概念,如《紅樓夢評論》中的“欲”、“優(yōu)美”、“壯美”、“悲劇”等,這些理論術(shù)語的運(yùn)用加強(qiáng)了文章的邏輯思辨能力。
審美獨(dú)立的提倡、批評思維方式及術(shù)語的變革,使得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學(xué)術(shù)成果日漸增多,出現(xiàn)了一些專門的批評論文,如周樹人的《摩羅詩力說》、姚華的《曲海一勺》、章炳麟的《國故論衡》等,這些論著不同于古代文學(xué)批評常見的詩話、詞話和小說戲曲評點(diǎn),大都是比較專深的理論著作,從而“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批評著作形式由語錄條目→單篇論文→學(xué)術(shù)專著的歷史過渡”。[4]420近代學(xué)者以自身的批評實(shí)踐實(shí)現(xiàn)著文學(xué)批評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換,這一理論自覺性為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二)近代文學(xué)批評理論呈現(xiàn)出體系化的特征
體系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各個(gè)部分所形成的整體面貌。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歷史悠久,產(chǎn)生了大量的詩論、文論等,但由于國人輕視抽象思辨的純理論而重視對具體事物的感悟,因此古代很少有能夠集中顯現(xiàn)文學(xué)批評思想體系的專門論著。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有關(guān)古代文學(xué)批評思想,是近代以來的學(xué)者根據(jù)古人散見的論述及其內(nèi)在邏輯演繹歸納出來的。在西學(xué)的影響下,近代文學(xué)批評家注意汲取西方文化來構(gòu)建自己的批評理論體系,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并寫出了多部文學(xué)批評著作,客觀上表明了自己的批評觀念、批評思維方式,文學(xué)批評具備了一定的整體意識。
近代學(xué)者王國維、梁啟超的文學(xué)批評理論都具備了體系性特征。要?jiǎng)?chuàng)建自己的理論體系,首先要確立體系的核心,即批評觀念。王國維提倡審美獨(dú)立論,并圍繞此觀點(diǎn)來構(gòu)建批評理論框架;批評觀念的變化必然要通過思維方式的變革表現(xiàn)出來,他提倡借鑒西方抽象、思辨和分析推理的方式來進(jìn)行批評實(shí)踐;批評術(shù)語是思維方式的外在表現(xiàn),王國維借鑒西方的批評思想與哲學(xué)思想,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批評話語體系。《紅樓夢評論》是其批評體系的重要體現(xiàn),文章擺脫了古代批評以考證索引為主的批評方法,全文縱橫開闔,章法嚴(yán)密,圍繞第一章“人生及美術(shù)之概觀”這一中心而展開推論,結(jié)論經(jīng)過層層推理而得出。以審美獨(dú)立的批評觀念為中心,批評思維方式以及批評話語等構(gòu)成了王國維文學(xué)批評的理論體系。
梁啟超的文學(xué)批評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提倡政治功利性是其文學(xué)批評的核心,在批評思維方式方面運(yùn)用從西方學(xué)習(xí)而來的歸納演繹等注重邏輯分析的科學(xué)方法,對作家作品及其文學(xué)現(xiàn)象做出理性的分類剖析;批評方法上,在繼承傳統(tǒng)“知人論世”說的同時(shí),又吸收了西方從時(shí)代社會、現(xiàn)實(shí)政治、文化思潮等多角度、多層次做分析的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與重思辨的理性思維方式相聯(lián)系的是,梁啟超大膽吸收現(xiàn)代西方文論的名詞術(shù)語如“情感”、“寫實(shí)”、“浪漫”等來進(jìn)行批評實(shí)踐。
二、近代文學(xué)批評為中國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建設(shè)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
理論內(nèi)容構(gòu)成學(xué)科的內(nèi)涵,是一門學(xué)科形成的必要條件,學(xué)科只有以理論內(nèi)容來支撐,才具備成立的可能性。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建構(gòu)是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程,其與近代文學(xué)批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形成時(shí)有幾大支撐性理論,而這些理論都可以在近代批評中找到根源。
首先,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對封建的文學(xué)觀念進(jìn)行了批判,提出建立進(jìn)步的、民主的文學(xué)價(jià)值觀,這與中國近代文學(xué)批評反對脫離社會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在批評觀念上,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文學(xué)革命先驅(qū)者們提出了“人的文學(xué)”、“國民文學(xué)”、“寫實(shí)主義文學(xué)”等批評理論。近代文學(xué)批評雖然沒有直接出現(xiàn)這些明確的概念,但已經(jīng)為該理論的出現(xiàn)準(zhǔn)備了必要的條件。近代社會的動(dòng)蕩與不安使得“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批評觀念得到了空前發(fā)展,文學(xué)為社會人生,文學(xué)批評面向社會,已經(jīng)成為絕大多數(shù)文學(xué)批評家的共識。梁啟超提倡國民性,主張加強(qiáng)“國民意識”,首次提出“政治小說”的概念,并且自己創(chuàng)作政治小說,如《新中國未來記》,希望把文學(xué)引向與生活相結(jié)合的道路。周作人則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shí)論文之失》中,提出結(jié)束封建專制為“一人”的舊文學(xué),提倡“為萬姓所公”的新文學(xué)。這些批評理論對當(dāng)時(shí)的社會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shí)其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與人生的關(guān)系的理論也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觀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其次,在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建設(shè)過程中有一個(gè)重要的理論話題,就是文學(xué)有無功利性,而這一話題實(shí)際上開啟于近代批評。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謂是眾說紛紜,各不相同,王國維從側(cè)重審美的角度來解釋,他認(rèn)為:“美之性質(zhì),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5]298主張文學(xué)創(chuàng)作應(yīng)超越社會的政治斗爭,用文學(xué)的眼光來看待與書寫社會生活。其在《文學(xué)小言》中說:“余謂一切學(xué)問皆能以利祿勸,獨(dú)哲學(xué)與文學(xué)不然。”[3]103這種超功利的文學(xué)觀對充分認(rèn)識文學(xué)及文學(xué)批評的特性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京派文學(xué)批評家更是繼承了這一理論,其代表人物朱光潛主張“純正的文學(xué)趣味”,提倡一種超然于政治功利目的的文學(xué)立場與態(tài)度,厭棄商業(yè)色彩濃厚的文學(xué)傾向。這一希望文學(xué)不受政治的束縛而獨(dú)立發(fā)展的理論觀點(diǎn)對“純文學(xué)”理論發(fā)展影響深遠(yuǎn)。
再次,小說批評的發(fā)展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建設(sh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而這與近代文學(xué)批評提高小說的地位有很大的關(guān)系。中國現(xiàn)代小說批評從五四發(fā)軔起,逐步走向成熟,一大批小說批評家應(yīng)運(yùn)而生。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近代學(xué)者在小說方面的貢獻(xiàn)。在古代,小說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隨著近代文學(xué)觀念的改變,人們對小說的價(jià)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夏增佑發(fā)表了小說專論《國聞報(bào)館附印說部緣起》,文中他指出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yuǎn)’,遠(yuǎn)在經(jīng)史等著作之上”。梁啟超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他的《論小說與群治關(guān)系》一文將小說的社會作用強(qiáng)調(diào)到關(guān)系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認(rèn)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雖然這些理論有些夸大其辭,但卻使得小說逐漸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出現(xiàn)了小說批評繁榮發(fā)展的新局面,涌現(xiàn)出許多小說理論批評家,如吳趼人、李伯元、狄葆賢等。在近代文學(xué)批評理論的影響下,現(xiàn)代作家借鑒西方的理論融入自己的批評實(shí)踐中,當(dāng)時(shí)的許多報(bào)刊如《新潮》、《小說月報(bào)》等都開設(shè)了小說批評專欄,小說批評日益繁榮起來,小說批評理論成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重要資源。
近代文學(xué)批評理論異常豐富,除上述幾點(diǎn)之外,還有不少理論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所借鑒與運(yùn)用,比如中西文學(xué)批評比較方法的運(yùn)用使得批評的視野更開闊,黃遵憲、裘廷梁等人對白話文的提倡促進(jìn)了五四時(shí)期的白話文運(yùn)動(dòng)等等。這些批評理論的出現(xiàn)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形成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三、近代文學(xué)批評為中國文學(xué)批評確立了開放性的學(xué)科建設(shè)方向
處于歷史交匯時(shí)期的近代文學(xué)批評自覺汲取外來的觀念與中國傳統(tǒng)的材料互相印證,形成了開放的觀念和世界意識,從而為中國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建設(shè)確立了開放性的方向,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
(一)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統(tǒng)一
中國近代文學(xué)批評是在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理論基礎(chǔ)上,吸收西方文論思想并加以融合與變通而發(fā)展起來的。許多批評理論的提出與傳統(tǒng)文論有著深厚的淵源,比如“境界”說,這一概念不是王國維首創(chuàng),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理論中的一個(gè)重要審美范疇,但他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己獨(dú)到的見解,使“境界”說進(jìn)一步系統(tǒng)化,并對現(xiàn)當(dāng)代的文學(xué)批評理論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實(shí)踐證明創(chuàng)新是學(xué)術(shù)保持生命力的根本保證,王國維曾說:“古來新學(xué)問大都由于新發(fā)現(xiàn)。”[5]207《紅樓夢評論》是他借鑒西方的一個(gè)重要嘗試,文中他以叔本華的悲劇學(xué)說為基礎(chǔ),將《紅樓夢》與《桃花扇》相比,指出前者是一部真正可以稱為悲劇的作品,并且在批評方法上一改當(dāng)時(shí)極為盛行的考據(jù)之風(fēng),重視邏輯的推演,運(yùn)用系統(tǒng)的哲學(xué)與美學(xué)理論對作品進(jìn)行富有思辨力的分析評論,這種全新的論說形式對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批評研究具有重要的轉(zhuǎn)折意義。
面對紛繁復(fù)雜的外來思想理論,近代學(xué)人們既沒有死守傳統(tǒng)不放,也沒有盲目崇拜“拿來”,而是在繼承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基礎(chǔ)上不斷地創(chuàng)新,這種對待學(xué)術(shù)的態(tài)度與方法為后來古今貫通、中西融合的學(xué)科建設(shè)思路的確立奠定了基礎(chǔ)。
(二)民族立場與世界視野的統(tǒng)一
在近代文學(xué)批評形成的歷史進(jìn)程中,以開放的姿態(tài)面向世界,走向多元與對話是其成功的重要經(jīng)驗(yàn)。近代學(xué)人們主動(dòng)引進(jìn)與學(xué)習(xí)西學(xué),林紓在翻譯外國作品時(shí),不僅注意介紹西方的民主與科學(xué),同時(shí)也希望中國作家能夠打開眼界,從中尋求藝術(shù)借鑒,“合中西二文熔為一片”。[6]面對中西兩種異質(zhì)文化,王國維顯現(xiàn)出了冷靜和謹(jǐn)慎的態(tài)度,他認(rèn)為二者不存在高低優(yōu)劣的對立,都是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他在《國學(xué)叢刊·序》中說:“余正告天下曰:學(xué)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3]240并且要求打破中西學(xué)術(shù)的界線,尋求“世界學(xué)術(shù)”,在他看來,我們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是為了追求真理,并非用它來對抗抵制傳統(tǒng)文化。
追求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世界性并未放棄民族性。1902年,梁啟超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結(jié)婚論”:“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jì),則兩文明結(jié)婚之時(shí)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7]8這種東西文化“結(jié)婚”的論說表明了當(dāng)時(shí)學(xué)者們的開放的胸襟,他們希望向異質(zhì)文明尋求創(chuàng)新,但這必須在尊重保護(hù)本國文化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用西學(xué)來不斷地豐富與完善國學(xué)。有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影響。這種建立在民族性與世界性基礎(chǔ)上的文藝觀將近代文學(xué)批評帶入了一個(gè)新的發(fā)展高度。
(三)面向當(dāng)下與面向未來的統(tǒng)一
近代文學(xué)批評的創(chuàng)作充滿了對當(dāng)時(shí)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探討與對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面對動(dòng)蕩不安的社會現(xiàn)實(shí),他們將文學(xué)批評作為改革社會與宣傳主張的有力武器,強(qiáng)調(diào)以現(xiàn)實(shí)生活為批評題材,如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以書名“鷹”與“英”諧音雙關(guān)來諷刺英國侵略者。批評理論的形成與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也密不可分,面對桐城派的抱殘守缺,陳去病直言他們不過是“空談義理,俚淺不根,浮光掠影,如癡人說夢,囈語滿紙”。在實(shí)踐中他們提出了“博采歐美人之長,薈萃熔鑄而自得”、“以他國文學(xué)之長,補(bǔ)我文學(xué)之短”的主張,這種與現(xiàn)實(shí)密切聯(lián)系的做法使得近代文學(xué)批評獲得了牢固的根基與生命力。當(dāng)下中國文學(xué)批評與文藝實(shí)踐有明顯的脫節(jié)現(xiàn)象,不少批評家不關(guān)注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shí),熱衷于理論自身的工作,甚至僅僅滿足于對西方各派理論學(xué)說的解讀與搬用,“以西釋中、以西注中、以西代中等現(xiàn)象層出不窮”,[8]以至遭遇“失語癥”的尷尬,這一現(xiàn)象需使我們保持警惕,文學(xué)批評脫離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方向,必將失去創(chuàng)造力。
近代學(xué)人對待學(xué)術(shù)的態(tài)度更是對文學(xué)批評的未來發(fā)展具有啟示意義,他們堅(jiān)信只有兼通“世界學(xué)術(shù)”之人才能夠“發(fā)明廣大我國之學(xué)術(shù)”,王國維指出,“異日發(fā)明光大我國之學(xué)術(shù)者,必在兼通世界學(xué)術(shù)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5]379這種寬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與開放的心態(tài)使近代文學(xué)批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對文學(xué)批評具有典范式的學(xué)術(shù)意義。
中國近代文學(xué)批評雖然各方面并不成熟,但它的出現(xiàn)卻開啟了一個(gè)新的文學(xué)批評時(shí)代,它既是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的承續(xù),又是文學(xué)批評走向現(xiàn)代的先聲。盡管近代社會沒有明確提出建立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但是批評家們憑借開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走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自我封閉的體系,在西學(xué)的參照下創(chuàng)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xué)批評理論,標(biāo)志著中國文學(xué)批評理論從自發(fā)走向了自覺,而這在客觀上促進(jìn)了文學(xué)批評學(xué)科的形成。同時(shí)學(xué)者們“當(dāng)今之世,茍非取人之長,何足補(bǔ)我之短”的學(xué)術(shù)胸懷更是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建設(shè)方向提供了啟示,只有以平等、寬容、謙和的態(tài)度理解中西文化,取長補(bǔ)短,才有可能使我們的文學(xué)批評既保持本土特色,又能超越時(shí)間與地理的局限而獲得世界性的意義。
[1] 杜書瀛.梁啟超:中國現(xiàn)代文藝學(xué)的起點(diǎn)[J].文藝爭鳴,2008,(3).
[2] 王群.論中國近代文學(xué)理論批評的自覺性[J].江淮論壇,1996,(5).
[3] 王國維.王國維文選注釋本[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4] 蔡鎮(zhèn)楚.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5.
[5] 王國維著,傅杰編校.王國維論學(xué)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
[6] 李占領(lǐng).論林紓的中西文化觀[J].近代史研究,1988,(4).
[7] 梁啟超著,夏曉虹導(dǎo)讀.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李長中.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轉(zhuǎn)型中的困境與策略選擇的思考[J].文藝?yán)碚撗芯?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