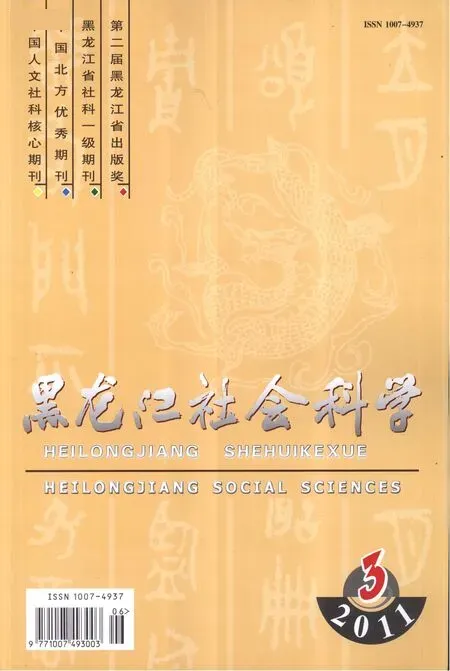從“民族情感論”到“國家利益論”——當代日韓關系新解
隋竹麗
(佳木斯大學,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從“民族情感論”到“國家利益論”
——當代日韓關系新解
隋竹麗
(佳木斯大學,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在冷戰體制下,朝鮮半島是東西方冷戰的重要舞臺,日韓關系研究歷來都是當代東亞區域史研究中的一大熱點和難點。《當代日韓關系研究 (1945—1965)》以二戰后日韓圍繞戰爭賠款及財產請求權、漁業及日本和韓國有主權爭議的水域“李承晚線”、在日韓國人的法律地位等兩國之間懸案問題展開的七次會談為主線,利用日、韓、美新近公布的一手資料,并跨越傳統外交史的局限,以東亞區域國際關系史的視角對1945—1965年的日韓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該書不僅彌補了國內日韓關系研究中的不足,也開辟了基于第一手資料研究當代日韓問題的先河。
《當代日韓關系研究》;日韓關系;“民族情感論”;“國家利益論”
在冷戰思維下,國內外諸多研究當代日韓關系問題的學者大多從日韓之間長期的侵略與被侵略、壓迫與反抗的歷史造成的民族感情沖突的角度把握當代日韓關系,但這似乎并不能理性地、正確地認知當代日韓關系的發展變化。我國國內的韓國研究雖然發軔于改革開放之后,但是直到 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才有了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問世。綜觀其研究,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國內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均基于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二手資料,鮮有利用與韓、日、美等國相關的第一手資料進行的研究。
黑龍江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安成日博士出版的《當代日韓關系研究 (1945—1965)》(以下簡稱《安著》)一書,恰恰彌補了國內日韓研究中的這一不足。該著作以二戰后日韓圍繞戰爭賠款及財產請求權、漁業及李承晚線、在日韓國人的法律地位等兩國之間的懸案問題展開的七次會談為主線,并以東亞區域國際關系史的視角對 1945年二戰結束后到 1965年日韓實現邦交正常化為止的日韓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綜觀全書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第一,《安著》在研究視角和理論上有新的突破,并提出了新的觀點。在國外,有關當代日韓關系研究雖不能說“汗牛充棟”,但也有多部著作問世。不過這些著作多拘泥于“民族情感論”或“美國導演論”,未能深入解析制約或推動當代日韓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因。如美國學者李庭植、韓國學者李元德、日本學者高崎宗司等,把二戰后日韓關系長期處于不睦狀態的原因歸咎于“對朝鮮殖民統治的認識問題”和“民族感情沖突”。他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韓遲遲不能順利解決兩國之間的各種懸案,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拒不承認過去對朝鮮殖民統治的錯誤,這導致了日韓兩國對過去歷史認識上的嚴重對立,兩國民族感情發生激烈沖突,導致兩國戰后處理談判,久拖不決。這些學者在著述中,對日本在過去朝鮮殖民統治問題上的錯誤認識,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1]6其學術研究角度,以“認識 (知)論”和民族主義為視角,注重決策者“認識 (知)”對一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盯住日韓民族仇恨問題,其研究視角基本停留在 20世紀初期的外交史緯度內[2]100。還有一些學者,如李鐘元等力主日韓會談“美國導演說”,把影響當代日韓關系發展的原因歸結為“東西冷戰”和美國的“冷戰戰略”,強調“美國因素”,提出在處理日韓各項懸案以及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中,美國發揮了重要作用[1]6。
《安著》則以國際關系史研究取代傳統的外交史研究,主張破除民族主義狹隘的偏見,強調多國檔案的對比研究,研究范圍由傳統的談判,擴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次的往來,并深入外交決策的內層,如決策過程、壓力團體等內政外交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2]100。其認為:“冷戰”體制是一個大系統,它內部存在東西兩個“相互對立兩大子系統”,并指出“日韓關系是西方子系統內部次元體之間的雙邊關系。”同時“從地緣政治上講,日韓關系是東亞地區鄰國之間的關系;從經濟發展層次的角度來說,日韓關系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從歷史角度來說,日韓關系是殖民國家與被殖民國家的關系。因此,日韓關系既有東亞鄰國關系的特點,又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特點和亞洲侵略國家和被侵略國家、殖民國家和被殖民國家關系的特點。這些構成了當代日韓關系的復雜性和特殊性。”[1]23據此,安成日博士摒棄傳統外交史研究中的“認識 (知)論”、“民族感情沖突論”、“美國導演論”等,結合日、韓、美等國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分析,以“國家利益論”闡釋了當代日韓關系的發展演變根本動因。《安著》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韓兩國之間的各項懸案久拖不決的根本原因,在于“日韓兩國在財產請求權問題和漁業問題上的國家利益的根本對立”;同樣,20世紀 60年代中期日韓會談之所以達成協議、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兩國在‘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國家利益上的相互吸引”[1]6。從而在當代日韓關系研究方面不僅為我們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而且實現了理論上的新突破,得出了新的研究結論。
第二,在歷史研究的觀念上有新的突破。從傳統的外交史到國際關系史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實證史學和理性史學的結合和發展過程。二戰后,美國外交史研究的演變印證了這種轉變過程。二戰后,美國的外交史學發展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說,再到修正學派、后修正學派的轉變。
二戰前的以比米斯、格里斯沃德等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學派強調“人類理性”,主張自由、民主、自決等原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外交決策正確與否的尺度只能是道德標準和國際法[3]92。二戰后興起的以漢斯·摩爾根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學派,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認為用傳統理想主義所訴諸的“人類理性”遠不能說明復雜的國際關系,進而提出“美國的外交行為無須用道德準則和國際公法來規范,而應以是否符合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尺度做出選擇”[3]93。
20世紀 60年代,以威廉斯為代表的“修正學派”(或“新左派”)現代外交史學興起。“修正學派”反對傳統外交史學只描述外交過程的治學風格和方法,也不贊同現實主義學派“只從國際均勢和國家利益的角度研究外交史的做法,改從研究國內社會經濟入手,探尋美國外交的歷史淵源、主流和動力。”但是“修正學派”片面強調經濟因素,而忽視其他社會因素對外交作用,不加區分對立的利益集團之間差異及其對外交政策不同影響的做法也招致了各種批判和挑戰。
20世紀 70年代之后,對“修正學派”的批評之聲逐漸匯集成“后修正學派”。“后修正學派”在外交史研究中總體上強調兩點:其一,主張對“外交進行綜合研究”。“后修正學派”呼吁“從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國家實力、決策精英、官僚體制、企業集團、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思想意識、傳播媒介、公眾輿論、地理環境等視角對外交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其二,“站在美國之外的世界觀察美國的外交”。“后修正學派”還抨擊以往外交史學單純地從國內背景出發“由內向外”地考察外交的方法,“呼吁從外部世界或從國際的宏觀舞臺來俯瞰美國外交”,主張“美國外交史從美國史的一個分支變為‘國際史’”。“后修正學派”“批評傳統史學僅把美國外交作為美國的民族經驗的外延來解釋,他們認為要考察 X國對 Y國的影響最說明問題的材料應到 Y國去找,因此必須從美國以外國家的歷史檔案中發掘材料”[3]95-97。
同樣,日韓關系也需要“進行綜合研究”,要站在“國際史”的角度研究當代日韓關系。《安著》從國家利益入手,以東亞國際關系史的緯度,從日韓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國家實力、決策精英、官僚體制、企業集團、思想意識、群眾心理、傳播媒介、公眾輿論、地理環境等不同的視角綜合考察了當代日韓關系,從而實現了歷史研究觀念上的新突破。另外,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要求作者具有理性歷史觀念。從民族情感到國際關系史中的國家利益,需要突破民族情感的約束,因此,不僅要資料真實,還要從歷史規律的理性角度來認識人和社會,以及認識國際關系,反映出柯林武德所說的:在歷史行動者,歷史事件之上的歷史觀念[4]51。這要求敘事者必須把握好宏大敘事結構和細節傳神之間的關系。敘事者作為一個客觀觀察者,確立合適觀察點,把握時代精神,通過歷史事件和行動者反映歷史觀念,國外學者稱之為“移情”,而對于具有美學底蘊的克羅奇和柯林武德而言,歷史是完成人由惡到善的轉變,歷史女神克麗奧美育的歷史,當然不應該凸顯民族仇恨。這對于任何一位史學家都是一種挑戰。國外日韓關系研究,日、韓學者之所以演繹出“民族情感沖突說”和“美國導演說”,正是這樣一種歷史觀念的缺失。因此,“當代日韓關系”對于安成日這樣一個具有韓國血統的歷史學者而言,不亞于一場心靈戰爭。可貴的是,在民族情感的波瀾中,安成日奉獻給我們的是一部歷史理性的日韓關系研究著作。
這并不等于說安成日比國外研究者聰明,而是說他完成了理性智慧的歷練。安成日以民族情感入境,以理性史學觀念出境,唯此才有了由“民族情感論”到“國家利益論”的國際關系史研究著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安著》既是世界史研究的突破,更是作者歷史觀念上的突破。
第三,細節上為歷史行動者以傳神寫照,凸顯歷史觀念。作為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詳細列表、考據分析的 Seminar(研究、討論、提高)是必需的過程。這主要體現在對于資料的運用方面。《安著》大量運用了韓國和日本的各種統計資料,通過數據說話及列表分析,給人一目了然的直觀感覺。對于翔實的資料,安成日博士仍審慎地核實,如對日文中的“瓦”,提出了自己的考證[1]28。《安著》在資料的運用方面,除對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檔案、回憶錄、論著、報刊予以關注外,還對那些不直接相關但是反映了兩國政治動態、社會風情、國際國內背景的民情、民意、民風的著作,同樣予以了應有的關注[1]6。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文本的闡釋,語言是把握細節的第一關。許多歷史思想、觀念往往蘊涵在本民族凝練的語言中,決策者的會意傳神的語言盡顯其思想、觀念,如吉田茂鼓勵池田勇人改善日韓關系的“勇往直前”,經作者注釋方知實為一語雙關[1]283,讀后釋然一笑。這當然取決于作者精通日語和韓語的功底。實際上,安成日潛心日本研究二十余年,悉觀日韓民俗,始能做到細節上為行動者傳神寫照。
《安著》談到“李承晚的下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時,則用“李承晚是權欲極其強烈的男人”的寥寥數語,勾畫出了李承晚的性格、品行,如見真人,也說明了事件的本質[1]241。對學生運動,反對李承晚選舉舞弊謀求第四屆連任的游行示威,則情深義重[1]243,反映了社情民意。對于樸正熙軍事政變美國導演說,直言沒有資料,證據不足,存此一說[1]280。另外,通過對著書宣稱“日本侵略戰爭是‘圣戰’”的日本外相椎悅三郎,在韓國機場上臨時寫上“道歉語”的這一“靈活外交”典型細節的把握,把日本外相的隨機應變能力和日本對韓外交的本質躍然紙上[1]346。《安著》還分析了韓國在野黨最終妥協的原因稱:“中國連續舉行了兩次核試驗,越戰爆發等緊張的遠東局勢下,韓國有被孤立的擔憂。”[1]363一語道出了民族情感與國家利益的心靈之戰。還有對于不同社會的反響,中國和朝鮮的否定聲明,其也一一加以記述[1]360。
總之,通過對日韓七次會談中典型細節的分析,《安著》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論證了國家利益對于決策者的影響,反映了各種利益階層與決策者之間的壓力互動,為我們理性認識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平等提供了難得的歷史范本。作為一部開拓性的研究著作,《安著》以國家利益論重新審視了當代日韓關系,但其研究實證分析有余,最后的理性展開卻略顯不足,讀來使人有言猶未盡的感覺。
當代日韓關系的研究,折射了人類歷史所遇到的共同問題:民族、戰爭、仇恨、邦交。《安著》在研究視角和理論以及歷史觀念上已經有了超越,主張不能只盯住民族仇恨。在分析日本對朝鮮半島殖民統治的認識問題和日韓邦交正常化的問題時認為,日本“否定侵略”、“美化殖民統治”的態度和立場曾經對日韓會談和日韓關系的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盡管如此,在實現日韓關系正常化的過程中,日韓雙方在現實國家利益的誘惑下,擱置日韓在殖民統治認識問題上的爭議,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375。這里,“誘惑”一詞不確,如果改成“做出了理性的歷史選擇”則更符合民族理性,更符合不能只盯住民族仇恨的國際關系史研究。人類歷史上的這種情感,每個民族都有,只有著眼未來,才能避免盯住仇恨不放。這種情感的超越,就是人類偉大的理性。《安著》對此有哲學概括,“日韓關系的正常化,說明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的國家,為實現各自更加現實的,更加重要的國家利益是有可能超越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就某些問題達成妥協的”[1]6。
筆者認為,《安著》提出的日韓兩國“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可能是從廣義上而言的。自1910年韓國被日本吞并,就兩國在人權、主權、侵略與被侵略、殖民與被殖民的社會地位而言,它們的認識和情感是對立的。但是,就 1945—1965年而言,筆者認為日韓之間狹義上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價值觀念等并不存在根本對立。因為它們同屬于一種政治陣營,政體上一個是君主立憲的內閣制、一個是總統制;它們同屬于美國自由觀念的國家,對立的是對過去的歷史認識和民族情感。日韓之所以能超越歷史認識和民族情感的對立,實現日韓關系的正常化,是民族情感向民族理性的回歸,執政者以國家利益為重做出理性的歷史選擇的結果。至于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筆者認為應該是中美、東西兩大陣營等之間的事情。對于中美而言,超越思想認識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建立邦交,同樣是執政者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歷史選擇。因此,從民族情感到國家利益實質是民族理性的體現。
[1] 安成日.當代日韓關系研究 (1945—1965)[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 唐啟華.“北洋外交”研究評介 [J].歷史研究,2004,(1).
[3] 王瑋.美國史學對 19、20世紀之交美國海外擴張的思考與認識[J].史學理論研究,2004,(2).
[4] 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D7
A
1007-4937(2011)03-0118-03
2011-02-12
隋竹麗 (1965-),女,山東文登人,副教授,從事古希臘、古羅馬歷史文化研究。
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