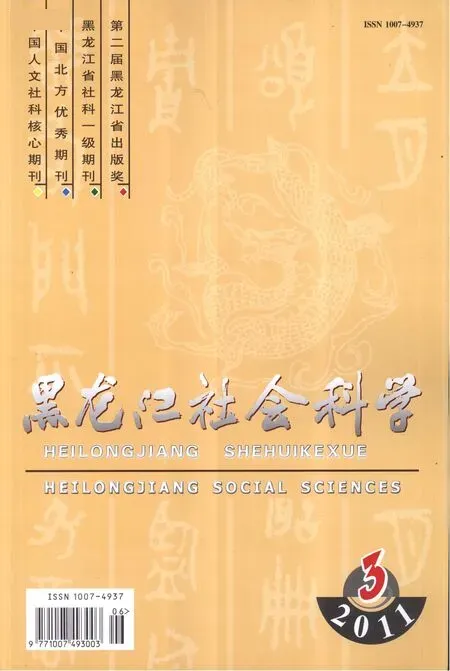敦煌文學的上源
伏俊璉,楊曉華
(1.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蘭州 730020;2.西北師范大學圖書館,蘭州 730070)
敦煌文學的上源
伏俊璉1,楊曉華2
(1.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蘭州 730020;2.西北師范大學圖書館,蘭州 730070)
敦煌自漢武帝建郡以來,學術文化及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900年藏經洞出土的五萬多卷文書,其中有六千多篇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基本上是唐、五代至宋初大約四百年間形成的。這些文學作品的出土,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敦煌文學;上源;河西漢簡
敦煌文學是保存在敦煌文書中的文學,并不是有記載以來,尤其是西漢建立敦煌郡以來的文學,這是首先應當明確的。敦煌遺書中的文學基本上是唐、五代至宋初大約四百年間的文學,此前在敦煌一帶流傳的文學是它的源頭,此后在敦煌一帶流行的是它的流變。追源討流是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所以本文簡單追溯敦煌文學的上源,并對在宋以后的嬗變略作論述。
一、簡牘所見兩漢時期敦煌地區的文學
漢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前,敦煌一帶主要活動的是塞中胡人、烏孫人、月氏人和匈奴人,他們的文學活動和創作我們不得而知。西漢“設四郡,據兩關”以后,中原文化比較快地進入河西走廓。兩漢時期傳世文獻對敦煌地區文學的記載很少,倒是近百年來的出土文獻中零星地發現有這一時期的文學,使我們得以窺見敦煌地區文學之一斑。1913年至 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在敦煌漢塞烽燧遺址中挖掘出了一批漢簡,其中有一首七言詩:
日不顯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視兮風非 (飛)沙。
從恣蒙水誠 (成)江河,州 (周)流灌注兮轉揚波。
辟柱槙到 (顛倒)忘相加,天門徠 (狹)小路彭池。
無因以上如之何,興章教誨兮誠難過。
1931年,張鳳先生《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將這首詩擬題為“風雨詩”,學者多從之。①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 1984年)編號為 476;吳礽驤《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1年)編號為 2253;何雙全《簡牘》(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4年 2月);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 2004年)均有釋文。但詩中雖然出現了“風”字,并沒有出現“雨”字,且全詩沒有寫到風雨,所以李正宇先生改擬題為“教誨詩”。②李正宇《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見《轉型期的敦煌語言文學——紀念周紹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 1月。詩的開頭兩句寫烏云密布,狂風卷沙,不見日月。接著兩句寫洪水泛濫,大地一片汪洋。“從恣”即縱恣,無所顧及。“蒙水”,李零釋為水名,在崦嵫山下。“州流”,同“周流”,謂洪水四處流泄。“辟柱”兩句寫人間是非顛倒,賞罰不公,天門狹小,仕途險惡。“辟柱”是國家之柱。“槙到”即“顛倒”。“徠”為“狹”之訛。“彭池”即聯綿字“滂沱”的另一寫法。最后兩句寫報國無門,無可奈何,只有吟詩告誡后人:這樣的時光確實難熬。“興章”指寫詩吟誦。全詩是一位失意文人的憤世嫉俗之作,詩題作“風雨”似更切題意。
敦煌地區的漢簡還殘留了一些民謠,如“三四姑公六七妹,□語眾多令腸潰”(《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476號,《敦煌漢簡釋文》2007號),可能是寫新出嫁的兒媳在婆家遭遇七姑八姨閑言碎語的痛苦情形。“伯樂相馬自有刑,齒十四五當下平”(《敦煌漢簡釋文》843號),是民間相馬的法則和規矩。“□□已溯酒上多,丁壯相佻 (逃)奈老何”(《敦煌漢簡釋文》774號),則是描寫戰亂的時代,青壯年都逃離家鄉,老弱病殘者只有留在家鄉,聽任老天的安排。更有意思的是,敦煌文學中的一些題材,在敦煌漢簡中可以找到上源。如敦煌馬圈灣出土的韓朋故事簡 (《敦煌漢簡釋文》496號),雖殘存字數很少,但在敘述方式和風格上更接近于敦煌本《韓朋賦》,其體裁與后世的話本相近[1]。
出土于敦煌漢塞烽燧的“田章簡”(《敦煌漢簡釋文》2289號),與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中的田章故事相近,也與敦煌本《晏子賦》、《孔子項托相問書》中的一些句子雷同,說明作為講唱文學,它們是一脈相承的①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上海有正書局,1931年;容肇祖《西陲木簡中所記的“田章”》,《嶺南學報》第二卷第三期,1932年 6月;勞干《漢晉西陲木簡新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七 (臺北),1985年。。無獨有偶,在居延烽燧中也曾發現過“田章簡”,②內蒙古考古研究所《額濟納漢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說明田章故事在漢代的河西地區廣為流傳,且余波不斷,一直延續到唐五代時期。居延出土的漢簡中還發現了三則類似于《晏子春秋》的故事,③甘肅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則在今本《晏子春秋》中找不到相同的內容,另外兩則還可以在《晏子春秋》的《內篇·雜上》和《外篇第七》中找到對應的段落,故事結構相同,內容吻合,只是個別詞語不同。這為敦煌本《晏子賦》找到了上源。在敦煌地區出土的漢代木簡中,還保存下來了一些書信。這些書信的作者,可能是戍守邊塞的有文化的將士,大都寫得情真意切,千載之后,猶能感動人心。如出土于敦煌漢塞烽燧的《政致幼卿書》(擬題,《敦煌漢簡釋文》1871、1872號),就是一個居住在成樂地方的名叫政的人寫給幼卿君明的信,信中雖為客套問候語,但由于天各一方,朋友之情深仍溢于言詞之間。出土于玉門花海的七面棱形觚簡上抄有一篇書信 (《敦煌漢簡釋文》1448號),是一個叫馮時的人寫給他的朋友翁系的。信中叮嚀翁系,春天到了,要注意飲食,調理好心態,多和自己聯系。同址出土的木簡中有“元平元年十月”的紀年,那么這封信當抄于此年 (前 74年)前后。馮時其人,不僅有這封信保存至今,在同一觚簡上,他還抄寫了一篇《遺詔》。何雙全先生綜合諸家的意見,釋讀如下:
制詔皇太子:朕體不安,今將絕矣。與地合同,終不復起。謹視皇大 (天)之祀加曾 (增)。朕在善遇百姓,賦斂以理。存賢近圣,必聚謀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恣,滅名絕紀。審查朕言,終身毋欠。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絕矣。告后世及其孫子,忽忽錫錫 (惕惕),恐見故里,毋負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廬,下敦閭里。人固當死,慎毋敢怯[2]163。
根據文意,這件遺詔是某皇帝臨終前寫給皇太子的遺言,是戍卒馮時于漢昭帝元平元年 (前 74年)七月抄寫的。根據詔書的抄寫年代,學者推測可能是后元二年 (前 87年)武帝臨終時的遺詔。因為西漢前期皇帝因病危臨終而遺詔托孤的,只有武帝一人。④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方詩銘《西漢武帝晚期的巫蠱之禍及其前后——兼論玉門〈漢簡漢武帝遺詔〉》,《上海博物館集刊》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9月。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是早于武帝的某一皇帝的遺言,甚至可能是劉邦的遺詔[2]164。由于出土的木觚是習字之作,不是正式的公文,所以通篇錯別字很多,從文意看,遺漏的字句也不少,書法也欠佳。但大意還是清楚的。遺詔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做了簡單回顧,告誡太子謹慎行事,舉賢任能,善待百姓,不要像胡亥那樣自大放縱。詔書字里行間流露出自信和無悔,行文豪放而又帶著悲涼的傷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也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文學作品。
敦煌懸泉遺址還出土了一批帛書,都是私人信札,其中“元致子方書”最為完整,也最為學者所關注。①王冠英《漢懸泉置遺址出土元與子方帛書信札考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第 1期;馬嘯《敦煌郡懸泉置漢宣帝間帛書二件》,《中國書法》1992年第 2期;饒宗頤《由懸泉置漢代紙帛書法名跡談早期敦煌書法》,《出土文獻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98年 11月;陳波《敦煌懸泉置出土西漢求刻印章帛書》,《篆刻》2000年第 3期。內容講元托子方為其買沓 (可能是指可以包鞋子的金屬片或革之類)、筆及刻印等事,信寫得很認真而小心翼翼,可以看出寫信者元的心境和為人。這位“元”,不僅文章寫得不錯,而且字也寫得很好。饒宗頤先生在《由懸泉置漢代紙帛書法名跡談早期敦煌書法》一文中說:“行筆渾圓,體扁平,捺處拖長,作蠶頭雁尾狀,意在篆隸之間,古意盎然。”信中說“愿子方幸為刻御史七公印一塊”,則子方是篆刻家。敦煌自東漢末至晉,書法家輩出,可以眸敵中原。張芝、索靖等尤為著名。張芝之后,敦煌一直有他的后人活動,而且以“墨池”作為地望,名其族為“墨池張氏”[3]。懸泉置出土的簡冊和帛書中,不僅反映早期敦煌文學的繁盛,而且是中國書法史上珍貴的資料。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地區的文學和學術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動亂,江左板蕩,河西地區相對安定,因而文學和學術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傳世文獻對此略有記載。下文對這一時期敦煌籍學者和文人的著述和創作作一簡要鉤稽。
漢末敦煌人張奐精通經典,曾“著《尚書記難》三十馀萬言”,“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后漢書》卷六五《張奐列傳》)。其長子張芝、次子張昶,并善草書,時人謂之“草圣”。張芝的外孫索靖,也是著名的草書家。
后漢敦煌人侯瑾、覃思著述,有《矯世論》、《應賓論》、《皇德傳》三十篇,所作雜文數十篇 (《后漢書》卷八十《文苑傳》)。《隋志》有《侯瑾集》二卷。
三國時敦煌人周生烈學精而不仕,“歷注經傳,頗傳于世”(《三國志》卷十三《魏志·王朗傳》)。
西晉敦煌人宋纖“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余人”,“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晉書》卷九四《隱逸傳》)。
西晉敦煌人郭瑀“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余人”(《晉書》卷九四《隱逸傳》)。
西涼時期敦煌人劉昞,《魏書》和《北史》都為他立傳。《魏書》本傳說,他曾“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余人”,又說“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 》二十卷 ,《方言 》三卷 ,《靖恭堂銘 》一卷 ,注《周易 》、《韓子 》、《人物志 》、《黃石化三略 》,并行于世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云:“劉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說者,此亦當日中州絕響之談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說,則今日亦難以窺見其一斑矣。”
西涼時,劉昞被尊為國師,同郡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并以文學見舉 (《魏書》卷五二《劉昞傳》)。索敞“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延明為劉昞字),著有《喪服要記》(《北史》卷三四《索敞傳》)。
《隋志》著錄有“《謝艾集》七卷”,按謝艾為五涼時敦煌人。《文心雕龍·镕裁》:“昔謝艾、王濟,河西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镕裁而曉繁略矣。”對謝艾的文學才能給予很高評價。
西涼名士張湛,敦煌人,《北史》卷三四《張湛傳》說他“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與金城宋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見稱于河西。其侄張鳳,“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西涼時敦煌人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曾作《玄石神圖賦》(《十六國春秋別本》卷九《北涼錄》)。
敦煌人闞骃“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北涼時,曾領銜“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馀卷”(《魏書》卷五二《闞骃傳》)。
北齊敦煌人宋繇,“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家無馀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北史》卷三四《宋繇傳》)。
北齊敦煌人宋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 ,撰《年譜錄 》,未成 ”(《北齊書》卷二十《宋顯傳》)。
以上這些著述,除劉昞《人物志注》外,基本都失傳了,文學作品存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
這一時期敦煌地區的文學,還應當提到西涼開國君主李暠倡導的文學活動。李暠建立西涼伊始,便在都城敦煌南門外修筑了靖恭堂,“圖贊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于后園,以圖贊所志”(《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遷都酒泉后,又勒銘酒泉,使劉昞為文,刻石頌德。上巳節,燕于曲水,命群僚賦詩,李暠親自作序。可惜的是,這一系列活動中的文學創作,都沒有能保存下來。李暠不僅是這些活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也創作了不少的文學作品。根據《晉書》本傳記載,李暠曾創作有《述志賦》、《自稱涼公領秦涼二州特奉表詣闕》、《復奉表》、《手令誡諸子》、《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顧命長史宋繇》(以上存);《槐樹賦》、《大酒容賦》、《上巳曲水宴詩序》、《圣明帝王序頌》、《忠臣孝子序頌》、《烈士貞女序頌》、《辛夫人誄》(以上佚)。本傳還說他“自馀詩賦數十篇”,《隋志》還著錄了《靖恭堂頌》一卷,都亡佚了。另外,《初學記》還節錄了他的《賢明魯顏回文》、《麒麟頌》兩篇殘文。
《述志賦》是李暠的代表作品,雖不創作于敦煌,但確實是魏晉南北時期根植于敦煌文化的最完整、最有藝術性的作品。這篇賦是作者對自己大半生志的回顧和總結,全文先寫自己幼年的志趣,希望隱居讀書:“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茂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于滄浪,善沮溺之耦耕。”成年后,由于家世的關系,他對前涼張氏政權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想施展才華,做夔、益那樣的賢臣,貢獻國家。但前涼滅亡后,河西一片混亂:“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于閨墻,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回湯沸于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煙。”自己為大勢所趨,在艱苦的環境中建立了西涼政權,賦中極力寫自己任人唯賢的用人思想和思賢若渴的心情,表明要以劉備和孫權為榜樣,以寬大的度量,為國家延攬了許多人才。賦的最后寫自己苦心經營,等待時機,籌劃著統一河西,進而配合東晉恢復中原的大業。這就是本篇所說的“志”。這篇賦在寫作上充分利用了比興手法,使文章形象、生動。賦還運用了祁連山一帶的神話傳說,給西涼政權增添了神秘性,使作品顯得瑰麗浪漫。尤其是大量使用歷史典故,更使作品具有厚實的歷史文化意蘊。
《晉書》本傳還載錄了李暠前后兩次上東晉朝廷的表文,與《述志賦》的內容是一致的。前表說:“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祖國的大好河山,為五胡所亂,李暠為此肝腸寸斷。西涼與東晉,雖相隔萬里,但“風云茍通,實如唇齒”。所以他熱切地“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為祖國的統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后表說:“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嘆憤,以成成歲。”表達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的急切心情。可惜此時的東晉王朝,內訌時起,自顧無暇,更無及于國家的統一大業了。
李暠長期生活在敦煌,后又以敦煌為都城建立西涼。他自己對敦煌非常有感情,他曾告誡諸子:“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是五百年中原文化的濃厚灌溉,培養了他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情感。大約 450年后,敦煌人張議潮率眾一舉推翻了吐蕃的統治。歸義軍政權建立初期,朝廷曾派使者抵達敦煌。他們一進敦煌,就被這里的情景所吸引:“嘆念敦煌雖百年阻漢,沒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 (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見甘涼瓜肅,雉堞雕殘,居人與蕃丑齊肩,衣著豈忘于左衽。獨有沙洲一郡,人物風華,一同內地。天使兩兩相看,一時垂淚,左右驂從,無不慘愴。”可見五百年來,敦煌人民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一直沒有中斷。
[1] 裘錫圭 .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J].復旦學報,1999,(3).
[2] 何雙全 .簡牘[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
[3] 伏俊璉,張存良 .草圣張芝在隴上的兩處遺跡[J].敦煌學輯刊,2007,(2).
J2
A
1007-4937(2011)03-0082-04
2011-03-28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 (09YJA751040)
伏俊璉 (1960-),男,甘肅會寧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和敦煌學研究;楊曉華 (1961-),女,甘肅臨洮人,館員,從事古籍文獻編目研究。
王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