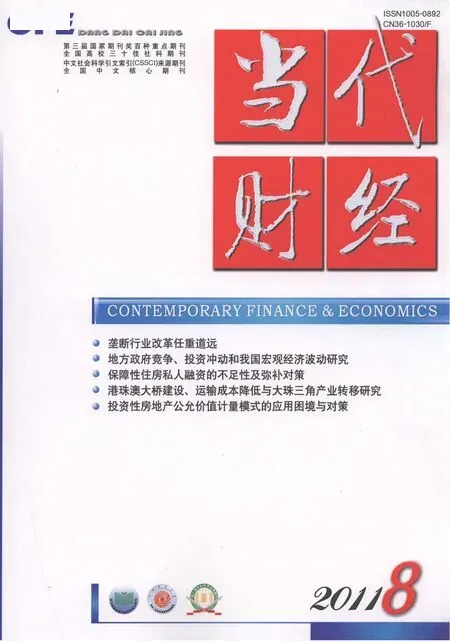論“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和倫理意義
逯 建,顧 芹
(西南財經大學 國際商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在當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討中,有關“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問題可謂是一個熱門話題。由于馬克思只是在某些論述和“六冊計劃”中提及過相關概念,但在《資本論》中并沒有關于國際經濟學的章節,所以關于馬克思國際經濟學理論的種種設想,就引發了各國學者很大的研究興趣。是否有客觀的國際價值,國際價值如何轉化為國際價格,國際交換中是否平等和公平等問題,因切實關乎國際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和具體利益,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而這些討論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對于“國際價值”是否客觀存在,即“國際價值”的實體性的問題,世界各國學者發表了一些截然相反的看法。如在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日本學者中就分為“以名和、松井、吉村等為代表的國際價值實體肯定學派和以木下、行澤、木原等為代表的國際價值實體否定學派。此外,還有不屬于這兩個派別的中間派”。[1]德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分歧。“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問題還與是否存在“世界勞動”(universal labour)的問題有聯系。當然關于這兩個概念究竟是否客觀的問題,不同學者的看法也是見仁見智。[2]
在研究“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問題的時候,需要清醒地區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當前形勢背景下產生的理論自然與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所不同。我們對馬克思著作的研究,需要注意馬克思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與思維習慣,而不是把現代的經濟情況附會到馬克思的研究之中。只有把馬克思的本意研究清楚之后,比照現今的理論發展才有意義。本文就試圖遵循這一分析思路,從馬克思的本意與當今理論的發展中探尋“國際價值”的實體性以及“國際價值”這一概念存在的意義。
二、“國際”與“國內”相區分的意義
在討論“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和倫理意義之前,我們首先需要考察馬克思等政治經濟學家在經濟理論中區分“國際”與“國內”的意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論述,無一例外都是先把國內問題論述完之后,再選擇性地論述一下國際情形。這一論述習慣,自然是與當時的歷史特征分不開的。在馬克思等人所處的時代,人們對國家邊界的意識要比現在強烈的多,國際間的經濟活動不僅因受高昂的運輸成本、關稅壁壘等限制而顯得微不足道,還會因歐洲動蕩的政治局勢、接連不斷的民族國家戰爭而經常中斷。因此在政治經濟學者看來,國際的經濟問題是必須要與國內經濟問題相區分的,國際經濟問題因此成為政治經濟學中國內經濟的對照或一個單獨的研究對象。
正因如此,政治經濟學者在理論中一貫采用的就是國際與國內兩分的假設:國內因經濟日趨活躍,資本、勞動工資、利潤等是可以達到一致的,而國際則因各種原因而根本無法達到一致——這里所說的無法達到一致不僅包括了現在不能,也包括了未來相當漫長的時間內也不能。如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國際經濟學開創者的李嘉圖就把英國與荷蘭、西班牙、俄國的關系和約克郡與倫敦的關系存在顯著不同當成他的國際經濟學理論論述的基礎。[3]從理論上說國際問題是無法與國內問題等同的,因此世界上就出現了若干個彼此分割的國家(當然,要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市場。在國家內部管用的經濟規律是不能完全推廣到國際問題的研究的。
對國際經濟問題過于絕對的理論處理,給國際經濟學研究帶來了一個辯證的矛盾:一方面國際經濟學理論必須假定國際之間是彼此分隔的,但國際經濟學又需要研究彼此分隔的經濟體是如何進行經濟活動的,這種經濟活動會導致原本分隔的經濟體不再那么分隔。所以國際經濟學是介于完全分隔與完全融合之間的,它雖有絕對的假設卻始終蘊含著突破絕對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經濟學存在的意義就標志了另外一對矛盾:一旦需要“國際”,就意味著需要與“國內”有所區別,但區別的目的卻是為了消滅區別,或者以無阻礙的國內情況來類比有阻礙的國際情況。這是作為經濟學分支的國際經濟學的獨特之處。
從著作的寫作安排來看,馬克思也是接受“國際”要與“國內”有所區分的看法的。如果不是這樣,他完全可以把國際的經濟問題與國內的經濟問題混在一起,在《資本論》中就把國際問題論述了。正是因為馬克思有“六冊計劃”的寫作安排,他才在《資本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史》中對這個問題討論很少。并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猜測,馬克思有關國際經濟學的內容不會影響到對國內經濟的研究。偶爾出現的只言片語,只能被看作是馬克思對國際問題的研究預示,如在討論“世界貨幣”的時候,馬克思曾說過“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4]的話以及“國際價值”、“世界勞動”等概念,都說明了馬克思是有在研究完國內的規律后再重新研究國際問題的考慮的。
三、“國際價值”的實體性
馬克思的國際經濟學理論是馬克思沒有完成的事業,遵照已寫的內容他或許會在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使用“國際價值”的概念,然而此“國際價值”到底有沒有實體性?它究竟是當作一個實際存在的事物的名稱還是大家都彼此相互約定意義的虛擬概念?如果我們了解了政治經濟學對“國際”問題一貫的認識以后,就不會在這個問題上產生偏差。“國際”本身就是被假設為存在分隔的鴻溝的,因此如果“國際價值”是一個實體,就勢必要求國際間的鴻溝不復存在,從而也會導致國際經濟學的消失。顯然,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是不會如此徹底地思索“國際”消失以后的情形的,他想得更多的是國際間越來越頻繁的經濟來往會給國際經濟帶來何種變化的趨勢。
有學者類比國內經濟體,認為“價值”的概念就是從人的勞動中抽象而來的,可以被看成是價格長期穩定的趨勢,那么“國際價值”同樣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種“國際勞動”的抽象,可以用以表明某種國際間不同價格的運動趨勢,由此得到“國際價值”應該是實體的結論。這種類比并不是正確的,因為“國際”是被假定成與“國內”不同的,國內能有的經濟規律,在國際上就不一定適用。將國際問題當成是國內問題的類比的看法,實際上只是將實體性強行賦予國際情況的唯實論的做法,而如果我們注意“國際”與“國內”的區別,把“國際價值”僅看成是為了方便論述的某種約定(也就是唯名論的做法),也是完全說得通的。“國際價值”更像是一個理想的狀態,是越來越頻繁的國際間經濟交往的最終運動終點,由于在理論假設和現實中國際間的隔閡始終存在,因此這種理想狀態可以無限被接近卻始終無法達到,那些趨向于理想狀況的實際情形,就可以被稱為“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又應該如何確定?由于否認了作為實體的國際價值,我們就不能將這一問題簡單地化歸為取決于國際價值,我們只知道它應該介于交換的兩國各自商品價值之間,究竟是多少并沒有定論。事實上在兩國價值之間的任何交換價格都是可行的,它取決于國際間交換雙方的討價還價的能力以及歷史、習慣等因素。
雖然嚴格來說“國際價值”不具有實體性,但這并不妨礙“國際價值”可以指導“國際價格”的研究。這是因為隨著國際間交往越來越頻繁,“國際價格”會趨向于“國際價值”。而事實上關于“國際價值”的確定,也基本都沿襲從“國際價格”推導的辦法。“國際價格”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國際間各商品的利潤趨向平均后的結果,類比國內各部門間平均利潤的計算,再通過國際平均利潤就可以計算出長期穩定的“國際價格”(即“國際價值”的大小或“國際價值量”)。這樣的做法可以回避“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問題,而在承認各部門的意愿售價是互不相同的前提下把平均利潤看作是穩定的“國際價格”及“國際價值量”的做法是可行的。當然,計算“國際價值量”的具體方法并不是只有一種的,王泓遠(2007)指出了在分析國際問題上如何堅持勞動價值論的問題,[5]李翀(2007)提出了國際商品價格再乘以國際貿易量權重的方案,[6]李榮林、史祺(2000)也提出了使用西方經濟學中短期—長期分析來確定“國際價格”的方法。[7]這些方法都是對“國際價值”問題積極有益的探討。
由于“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并不存在,因此也不會存在實體性的“世界勞動”等概念。對于在馬克思著作中出現的類似的概念,我們傾向于認為是馬克思為了論述方便而特意構造出來的。首先,馬克思沒有反復地使用這些概念,這些概念也沒有成為馬克思著作的索引詞條。其次,諸如universal labour能否翻譯為“世界勞動”都還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即便能這樣翻譯,通過折算的各國勞動[1]是否還具有實體性,仍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與其那樣,我們還不如就把它們看成是一些有名而無實的標志,馬克思只是為簡便地表達出他的國際經濟學思想的一些指代而已。
攝影師高志明常常閑得發慌。整個上午,春風照相館里沒有一個來照相的顧客,午間,高志明跟搭班的同事打聲招呼,跨上自行車在街上閑逛。
四、國際勞動差異產生的原因
如何使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國際間價值的差異?這個問題也等價于如何將各國內部的勞動轉化為世界性的勞動。如果我們按照西方國際經濟學的理論,自然會得到許多不同的解釋,但對于政治經濟學,則必須使用勞動價值論,對那些理論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再解釋。馬克思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基本上是繼承李嘉圖的,而李嘉圖對國際間差異的解釋,就是各國生產效率的不同,因此馬克思將國際間價值的差異問題,也歸結為不同國家的不同勞動效率(即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價值規律在這里有重要的修正。不同國家勞動日的關系,能夠像一國之內熟練的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關系一樣。”[8]正是由于不同國家的生產技術不同,他們的勞動的復雜程度不同,所以商品在國際間才會有不同的價值。當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大致是按照勞動效率來解釋國際間價值的差異的。
在馬克思之后,現代西方經濟學又給出了國際要素稟賦(赫克歇—俄林)和規模效應(克魯格曼)差異的解釋。這些理論又該如何用政治經濟學進行解釋呢?從勞動價值論的視角,要素稟賦差異其實造成的是獲取某種生產要素難易程度的差別,從而需要一國比另一國付出多得多的勞動強度;而規模效應則體現出作為一種生產集團的勞動效率,是一種廣義的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這樣,西方經濟學對國際間價值差異的解釋都可以轉化為對勞動差異的解釋,而由此得到的“國際勞動”就可以作為計算“國際價值”大小的依據,雖然“國際勞動”仍然是需要估算而不是實際存在的。
五、“國際價值”的倫理意義
“國際價值”雖然不具實體性,但在關于國際經濟活動公平正義等倫理問題上卻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國際經濟問題并不服從某一國內的經濟規律,國際經濟問題也可以有多種解決方案,但在諸多方案中,遵循“國際價值”交換分配方案卻是其中最為事實公平的一種。首先,依照“國際價值”的交換分配最能促進各國獲得最大的利益。“國際價值”表示的是國際交往極端密切的理想狀態。如果兩國之間的經濟交往不密切,彼此之間的交換雖然沒有依照“國際價值”,但根據比較優勢,兩國還是能在國際交換中獲得各自的利益,由此兩國有了繼續交往的驅動力。而繼續交往的結果就是,兩國商品的價值差異被縮小了,新的交換向“國際價值”趨近了一步,由此又導致了新的交換以及價值的差異的縮小。如果交換偏離了“國際價值”,那么就無法繼續進行交換了,各國(至少從經濟角度來講)無法再繼續獲得比較優勢的利益,國際間也因這種偏離而喪失了最大的效率。
其次,依照“國際價值”的交換分配還能最大化國際各國的總福利。如果我們承認財富對各國福利的增加值是隨著現有財富的增加而逐漸變小的話,那么對于增加的同一筆財富富國顯然不會比窮國更加高興。如果國際間的交往出現了扭曲,扭曲的結果造成的是出現了富國和窮國的話,那么交換適當地向“國際價值”進行一些調整,帶來的結果只能是窮國得到富國損失的那筆財富,但富國不會因此變得比窮國還窮。這種變動的結果是窮國獲得了很大的福利而富國的福利稍有損失,兩者相加導致國際各國的福利總和增加了。
“國際價值”最具事實公平意義的第三條理由是依照“國際價值”的交換能使世界更加平衡和諧地發展。在這種方案中各國商品價值能夠得到最充分的展現,各國之間的勞動能獲得相同的尊重。落后國家不會因談判上的不公平而遭受損失,也不會因不同的勞動報酬而產生貧富差距,產生長期的購買力不足。發達國家雖在短期內會損失掉國際的超額利潤,但卻會在長期中因落后國家的發展而獲得更為廣大的銷售市場,從而延緩經濟危機的發生。只要發達國家保持科技的持續進步,它是不用擔心喪失國際分工中復雜勞動的有利地位的。
“國際價值”雖然不具實體性,但并不妨礙我們在處理國際倫理問題時將其當作一個重要概念來使用。在實際處理國際間的討價還價的問題時,“國際價值”也只給我們提供改善國際經濟秩序的方向,而真正絕對依照“國際價值”的交換是無法達到的。由于復雜勞動向簡單勞動折算時較復雜,也由于各國的發展瞬息萬變,因此在實際使用中準確地說出“國際價值”的數值并不容易。這一方面需要現代的經濟學發明更加有力的工具來予以估計,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的歷史研究,來揭示“國際價格”偏離“國際價值”的程度以及其逐漸接近“國際價值”的趨勢。
六、結語:“國際價值”的當下意義
我們之前的論述,是以馬克思所處時代的歷史特征為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在當今情況下“國際價值”是否具有了實體性?筆者并不贊同這樣的表述,因為當今世界中國家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還是可以在各個方面起到阻礙國際經濟自由的作用,商品的國際價值并不會達到最終的完全相等。但如果我們辯證地看待“國際價值”的實體性,就會得到當今世界商品的“國際價值”的實體性比過去大大增強的結論。我們不妨將“國際價值”的實體性看成是一個數值,只不過與19世紀相比現在的這一數值變得比較大了,使得它看起來就快要達到完全的實體性而已。
雖然當今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大大增強了“國際價值”的實體性,但在國家消亡之前,“國際價值”非實體的那一面仍然是不會被徹底消滅的。國際一體化、世界大同的時代遠沒有到來,國際間的經濟交往還有不小的阻力,由于國際交往更為頻繁,這些阻力會更加廣泛地困擾到國際經濟活動上。因此對“國際價值”的分析,仍會給各國以很大的指引。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在19世紀開創的國際經濟學是不會過時的。“國際價值”因其具有的倫理意義而成為國際經濟交往中的重要標準,這一標準還會在很長的時間內成為國際經濟交往及國際談判的核心議題。
[1]中川信義,張開玫,匡鳳姿.圍繞國際價值論的若干理論問題[J].經濟資料譯叢,2008,(1).
[2]謝富勝,李 安.國外學者對馬克思國際價值理論的新探討[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2).
[3]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13.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6.
[5]王泓遠.正確對待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性[J].當代財經,2007,(1).
[6]李 翀.馬克思主義國際經濟學的構建[J].當代經濟研究,2007,(4).
[7]李榮林,史 祺.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與西方國際貿易學說[J].南開經濟研究,2000,(5).
[8]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