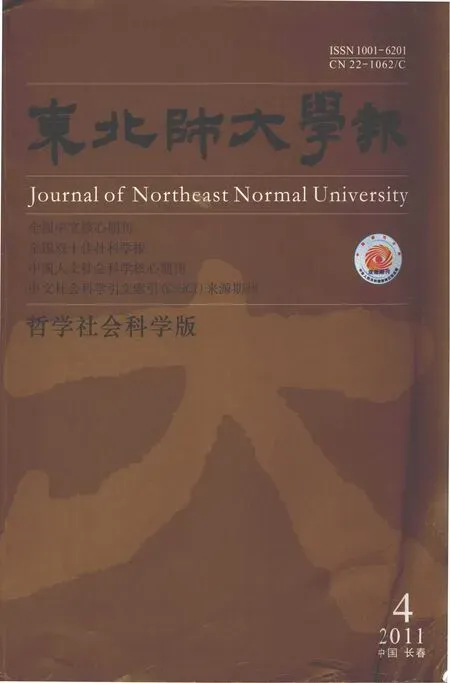同途殊歸之思: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再審視
梁大偉,黃定天
同途殊歸之思: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再審視
梁大偉1,黃定天2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共同的路徑是救亡圖存,但甲午一役卻似乎使洋務運動的成果在瞬間化為烏有。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從發(fā)起到最終結束,中國和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有相似之處,也有所不同。不應該單純因甲午戰(zhàn)爭中國的失敗而全盤否定洋務運動的改革成果及其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進步影響。
洋務運動;明治維新;甲午戰(zhàn)爭;晚清
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產生于同一歷史時期,變革的出發(fā)點都是救亡圖存,但是最終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可謂同途殊歸。但是,不可以狹隘的把洋務運動置于歷史的平面進行“點線式”的分析,更不能單純以甲午戰(zhàn)爭中國的失敗作為衡量洋務運動成敗的唯一標準。相反,我們應在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多維比較和重新審視中客觀評價洋務運動的作用,多一份理性,少一份苛責,還歷史以本真。
一
對于洋務運動的評價,學界多持批評態(tài)度。要么從政治角度貶洋務運動踐行的出發(fā)點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逆歷史潮流而動,其結果注定失敗;要么從經濟角度貶洋務運動不遵循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限制私營經濟發(fā)展,導致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無法壯大,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要么從文化角度貶洋務運動在變革理念上的片面和枝丫,“中體西用”的思想在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zhàn)中就已經被駁得體無完膚,后來“雄辯”和確鑿的史實——甲午戰(zhàn)爭,更使人對此深信不疑;要么從軍事角度貶洋務運動只注重西方火器之能效,沒有從根本上認知軍事與政治的不可割裂性,致使北洋水師灰飛煙滅;更有甚者從運籌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多學科角度,從主觀與客觀、主動與被動、個體與群體等多個層面對其進行批判,理論觀點自然五花八門。眾所周知,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內憂外患的大歷史背景之下,近代中國先后經歷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驚醒了大清“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國開始重新審視諸多“蠻荒之國”,有識之士探索救亡圖存的真理,相繼提出“自強”、“求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口號,進行了長達三十幾年的改革運動。而日本同一時期也在經歷著一場自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xiàn)代化的改革運動,中國和日本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環(huán)境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都是封建制度逐步土崩瓦解,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早期萌芽,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的封建制度經歷了幾千年的苦心經營,保守勢力頑固而強大,致使洋務運動先天動力不足,如《周易》之《井》卦,雖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1]的時期,但是因其泥沙積淤、僵化久長,所以革新起來必然耗費更大氣力,加之中國的洋務派在中央以奕?為代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為代表,其成員都是封建官僚,階級立場所限,不可能有打碎封建制度,重新建立新政權的想法,在改革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徹底性,而日本明治維新雖然在時間上落后于中國洋務運動七年,但是日本的頑固勢力與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是無法相提并論的,并且,日本變革運動的主體是武士、大名階層,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明治維新以“脫亞入歐”為宗旨,經濟上效法英國,軍事上效法德國,文化上效法美國,推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yè)、文明開化”[2]三大措施,走出了“民族主義的、家族式的、反個人主義的”“日本模式”的現(xiàn)代化道路,使日本迅速從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轉變?yōu)橐粋€經濟較為發(fā)達的工業(yè)國。但即便如此,中國仍然以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沖破了牢籠,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一批近代民用工業(yè),拉動了內需,緩解了原料、燃料不足等問題,為軍用工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資金;平息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消除了內亂給原本已經千瘡百孔的大清統(tǒng)治造成的嚴重威脅,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了和平穩(wěn)定的國內環(huán)境;創(chuàng)辦了新式學堂,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培養(yǎng)了翻譯人才,以特殊的方式化解了國際間的諸多影響中國發(fā)展的不利因素;尤為重要的是建立起以福建水師、廣東水師、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為建制的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
二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毗鄰而居,同屬亞洲國家,秉承東方文化。近代,中國和日本更是面臨同樣境遇,幾乎同時被西方列強叩開國門,被迫簽約通商,走上效法西方,富國強兵之路。不同的是,中國經歷了洋務運動的改革之后,在甲午戰(zhàn)爭中慘遭日本屠戮;日本經歷明治維新之后,“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很多學者把甲午海戰(zhàn)中中國的失敗理解成或者片面理解成洋務運動的失敗,并由此進一步分析洋務運動的封建性、腐朽性及對外依賴性,從中找出種種與洋務運動有關的貌似很有根據(jù)的根據(jù)。誠然,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腐朽性和對外依賴性的說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號稱遠東第一的海上力量定非空穴來風,而且,中國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中國人貴柔守雌、涵容萬物的性格,中華民族一直奉行萬物和諧共生、周邦睦鄰友好的理念,以保全自身、不略外族為一貫宗旨,當時洋務運動建立的北洋水師的實力既然可以得到全世界所公認,就無疑是不爭的事實。如此看來,洋務運動的成果就毋庸置疑。而戰(zhàn)爭的勝敗是受天時、地利、人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等多方面因素制約的,甲午海戰(zhàn)前夕,洋務派以李鴻章為首的中堅力量一直受頑固強悍的封建勢力所掣肘,統(tǒng)治階級內部對戰(zhàn)爭的戰(zhàn)法也存在嚴重分歧,缺乏應對戰(zhàn)爭的長遠戰(zhàn)略規(guī)劃,避戰(zhàn)求和派將領不乏其人,難以動員全國軍力與民眾,臨戰(zhàn)倉促調兵,主戰(zhàn)將領戰(zhàn)場屢屢貽誤戰(zhàn)機,節(jié)節(jié)敗退,致使軍人的榮辱觀喪失殆盡,鼓衰而氣竭。本質上講,當時日本根本沒有確切的能夠戰(zhàn)勝中國的軍事實力,其中摻入了復雜的政治因素,僅美國政府的遠東政策就極大地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日本始終對中國處心積慮、垂涎三尺,它之所以敢于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是與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和日本的民族性有關的,國土面積的狹小和資源匱乏等多重地緣因素的長時間積淀,使日本這個民族形成了效忠天皇、崇軍尚武、自負好戰(zhàn)的性格,并且,日本民族的狂妄和狼子野心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歷了甲午戰(zhàn)爭后才得以逐步建立的,時至今日,日本仍然承認,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創(chuàng)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zhàn)爭奇跡,因此,甲午戰(zhàn)敗并不能作為否定洋務運動功績的憑據(jù),反倒有力地證明了洋務運動在軍事上的成績斐然。
三
透過甲午戰(zhàn)爭的烽煙,我們更多需要反思的是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同途殊歸的深層次原因。誠然,洋務派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是有限制私營經濟發(fā)展的某些做法,但洋務派興建的近代民用工業(yè)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不能說沒有正方向的影響,而且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資金。明治維新之所以可以使日本在政治上突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發(fā)展,使其在軍事上迅速強大起來,首先在于日本的封建制度開始就不曾也從來沒有中國的封建制度完善、堅固和難以摧毀,改革的阻力小于中國,可謂占盡天時;其次,日本一般被看作是接近于理想民族國家,本州雖然有朝鮮族、華人、菲律賓人和巴西人,以及一些西洋系民族,但比例不足百分之五,所以在意識形態(tài)的推廣和政策的實行方面相對容易,可謂占盡地利;再次,日本領導明治維新的階級是以武士、大名為首的新興資產階級,革命相對徹底并具有顛覆性,在思維觀念的更新和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方面相對見長,可謂在人和方面有較為明顯的優(yōu)勢。而中國在先天不足、肘腋兼憂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建立起近代軍事工業(yè)、民用工業(yè)、文化產業(yè),不能不說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和智慧,而且,洋務運動在思維觀念上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影響也是無可估量的,隨之而來的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與實踐,不能說與洋務運動在客觀上對中華民族意識覺醒的促進作用無關。一般說來,某個歷史時期或者某個歷史時期的某個特定年代出現(xiàn)少數(shù)思想先驅并非難事,但精英思想能夠為多數(shù)人所普遍認同并為之前仆后繼,才是真正理性意義上的民族覺醒。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覺醒,沒有長久以來的思想積淀和偶然的歷史事變的撞擊是不可能促成的。我們不應該將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和民族振興的運動簡單的放在歷史中的某一點或者某一時段進行“點線式”的分析,更不能以一次戰(zhàn)爭的勝負作為片面的評判標準。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明治維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打破了傳統(tǒng)的東方靜態(tài)社會的模式,建立了開放的環(huán)境,加強了與世界民族間的聯(lián)系與溝通,引入競爭機制,從而徹底地激發(fā)了社會活力,使一潭死水得以波瀾壯闊。梁啟超當時就曾提出,中國欲自強,首先要“取法東洋”,“以日為師”,甲午一役振聾發(fā)聵,中國人從此在思想上徹底覺醒,重新看待中國的現(xiàn)狀和周遭世界,理性地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由此更不能否認洋務運動的進步作用。變法是亙古恒常,取法則需與時俱進,而今,我們更應該對那一場蛟龍擘水式變革運動進行重新審視,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進深刻認知這一與我們隔海相望,與中華民族有著深遠淵源的鄰邦,對中日兩國在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相互交織的復雜的發(fā)展因素中重新定位,樹立民族自信心,謀求國家科學發(fā)展和迅速崛起,避免悲劇再度發(fā)生。
[1]朱熹,李一忻.周易本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336.
[2]汪淼.明治政府的文明開化政策[J].史學集刊,1987(7):49.
K256.1;K313.41
A
1001-6201(2011)04-0258-02
2011-03-10
(作者單位:1.吉林大學農學部公共教學中心;2.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責任編輯:趙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