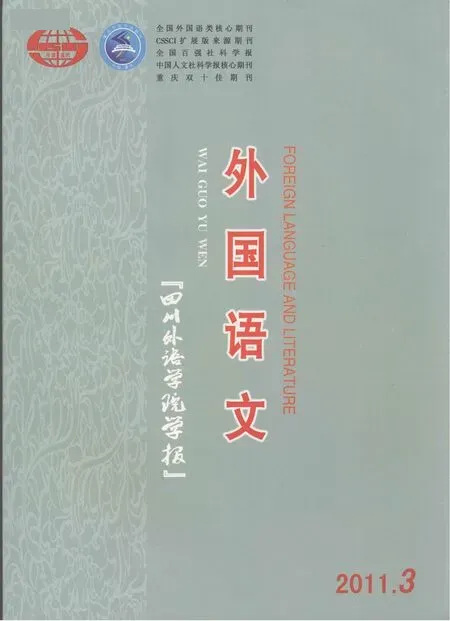論翻譯的主觀性
程 平
(廣州航海高等專科學校,廣東 廣州 510725)
1.引言
在翻譯領域一直存在著一種類似于尋找絕對客觀真理的企圖:翻譯應盡可能從內容和形式上“客觀”忠實地再現原文。但真實的翻譯表明:翻譯是一個“不忠的美人”,譯本無定本,翻譯只能是“形似”與“神似”、“等值”與“等效”乃至“化境”了。由“原文中心論”向“讀者反映論”的轉向也折射對翻譯“客觀性”的理性反思,與“客觀性”相對立的“主觀性”成為翻譯隱而不發的“真值”。但“主觀性”是形而上的哲學范疇,為避免偽科學性,譯界對“主觀性”一詞諱莫如深,借以“主體性”蔽之。可是西方哲學中的“subjectivity”乃“主體性”與“主觀性”的同一,有學者提出主體性研究實在沒有必要,因為人自然是從事對象性活動的主體,主體性背后的主觀才是我們研究的使命。因此,本文試圖對翻譯主觀性的定在作一點初步的探討。
2.主觀性——中外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邏輯指向
在中外翻譯理論與實踐領域,雖一直把譯文對原文的“客觀”、“忠實”、“對等”視為最高原則,但也不乏學者提出了諸多蘊涵翻譯主觀性的觀點。
在西方,早在公元前46年古羅馬哲人西塞羅《論演說術》提出“不要逐字翻譯”的理念就包涵著譯者主觀理解的內在邏輯。1964年,尤金·奈達提出的“所謂翻譯,是指從語義到語體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文”中的“最切近而最自然”、“對等”就是不具有可以量化的、因人而異的主觀概念。以至于后來紐馬克批評這一觀點時指出“等效只是一個理想中的目標”(Newmark,1988:48)。張美芳教授指出:對于翻譯研究,在傳統翻譯理論家和現代語言學家之間有相當多的誤解和分歧,前者常常指責后者故弄玄虛,脫離實際;后者則認為前者“主觀”、“隨意”、“不科學”。紐馬克屬于前者,而貝爾屬于后者。
莫娜·貝克(Mona Baker)是翻譯研究界的佼佼者。她的研究興趣之一就是利用語料庫研究各種翻譯的特點,包括研究譯本的特征以及不同意者的文體和風格。她有一個假設:譯者有自己的文體。為此,她選用了英國當代著名翻譯家布什(Bush)和克拉克(Clark)的翻譯作品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不同譯者的譯文風格具有鮮明的主觀特征,克拉克偏愛使用過去時態和直接引語而不喜歡間接引語,而布什過度地使用“學術型”的語言結構。赫曼斯(Hermans)指出:譯者有時“沖出語篇層面為自己說話,甚至用自己的名字,例如在譯文后的注釋中用第一人稱解釋所述的問題”(張美芳,2005:53)。這足以看出譯者的主觀性有時表現得十分突出。列維(Levy,1967:1171)干脆把翻譯行為描述成一種抉擇行為,他認為主觀因素(例如譯者的審美標準)在抉擇中起著重要作用。古阿德克(Gouadec,1990:334-335)則提出譯者“選譯”(selective translation)策略,在“選譯”過程中,只有與原文本某個特殊方面有關的細節得到翻譯,而所有不相關的信息都被排除不譯。無論是“抉擇”還是“選譯”,都十分強調譯者主觀性的重要作用,或者把主觀性“術語化”為具體翻譯行為。
弗米爾(Hans J.Vermeer)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目的論(Skopostheories)認為決定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圖里(Toury)又將目的論描述為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目標文本趨向(Target Text-oriented)范式(Toury,1995:25),譯者必須通過選擇那些最符合目標情境要求的特征來解釋文本。德國籍芬蘭專業翻譯家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Mattai)1981年她在其著作《翻譯行為理論與研究方法》中幾乎不使用“翻譯”一詞,把翻譯被解釋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特定目標而設計的復雜行為”(張美芳2005:79)。行動指的是行動的過程,是指有意圖(或隨意)地引發或阻止世界(本質上)發生變化。因此,行動可以界定為故意改變某種事態使之轉變為另一種事態。這等于將主觀性“目的化”或“意圖化”。
自17世紀德萊頓(Dryden,1989:8)提出“釋譯”(paraphrase)概念之后,“釋譯”被認為是介于“自由譯”和“字面翻譯”的折中方案,賦予譯者有節制的主觀性闡釋。赫維(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則提出“詮釋性翻譯”(exegetic translation),將其界定為“一種在目標文本中把源文本中未能明確傳達出的額外細節加以表述、解釋的翻譯類型”,允許譯者依據其主觀理解加以擴充。斯坦納(Steiner,1992:314)進一步運用闡釋學原理把翻譯過程所表達的“詮釋步驟”細分為:信任、入侵、合并和補償四個階段。“信任”是基于譯者對原文意義的假定;“入侵”是譯者對原文意義“俘虜回家”;“合并”或“挪用”是把新的因素引入目標語和文化系統;“補償”這意味著“譯者此時必須努力用自己的語言恢復他們未能傳達的源文本內容”(Leighton,1991:23)。顯然,他在闡釋的基礎上對譯者主觀性進行了“程序化”加工。在我國,“信”作為中國譯論中一脈相承的“極軌”和“道”始終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界定而呈現見仁見智的主觀特征。發軔于佛經翻譯的中國翻譯思想從一開始就注重主體的主觀“頓悟”和“通脫”。
嚴復就是一個翻譯主觀化的突出典型。有時他全然不顧原作的本來面目而依據自己的主觀意圖進行刪減、添加。蔡元培說,嚴氏譯《天演論》時本甚激進……后來激進的多了,他乃發趨于保守。于民國紀元前九年,把四年前舊譯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權界論》。蔡元培的意思很明白,嚴復的翻譯在選書與標題上有其現實的用意。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說“嚴譯是藉翻譯來作詮釋的絕佳案例”(黃克武,2000:89)。林紓的主觀性翻譯更加明顯。鄭振鐸在研究林紓的翻譯時指出:他不懂外文,譯文完全建立在與他合作的口譯者身上。因此,他把許多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敘事,刪減了許多對話。
郭沫若指出,有些譯者的目的并不是基于客觀實際,而是基于個人的主觀目的。他說:“目下我國的翻譯界,其中自有真有學殖、純為介紹思想起見而嚴肅從事的人,但是我們所不能諱言者:如借譯書以糊口,借譯書以釣名,借譯書以牟利的人,正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羅新璋,1984:332)其意思就是說譯者的翻譯行為往往受制于所持的各種主觀的、并不純粹的意圖。譯者沽名釣譽、苦心追求低下目標都不足為奇的,何況中國人還有“搶先”的習慣。鄭振鐸在《譯文學書的方法如何?》一文中也認同譯者的主觀自由。但如何限制這種自由呢?那就靠譯者的天才與判斷力與謹慎綿密的觀察了。但后來他又指出:“對于這種全憑譯者的天才與判斷力與謹慎綿密的觀察而始能善于使用的自由,應該絕對的謹慎的用,并且應該絕對的少用——除了極必要的時候。”他所擔心的是主觀過度。
陳西瀅在《論翻譯》一文中認為,為什么神似的譯本寥寥難得,其原因在于一本原著很難遇到一個與原作有同樣心智的譯者,只有一本書遇到了一個與原作有同樣心智的人,才會有一本新書重新產生這樣的幸運來臨。在他看來,神似的翻譯不在于譯者如何臨摹、如何孜孜以求,而全依賴于原作與譯者心智的偶合。因而把神似的翻譯看作是一場對譯者的賭注,把譯者的主觀因素夸大到了極致,最終走向了主觀唯心。后來曾虛白針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認為“神韻”二字仿佛是能意會不可言傳的一種神秘不可測的東西,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毫無標準的神秘物。林語堂也指出:“其實翻譯上的問題,仍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的文字的兩樣關系,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問題。”(羅新璋,1984:419)
金圣華提出:“譯者在早期雖有‘舌人’之稱,卻不能毫無主見,缺乏判斷……翻譯如做人,不能放棄立場,隨波逐流;也不能毫無原則,迎風飄揚。因此,翻譯的過程就是得與失的量度,過與不足的平衡。譯者必須憑藉自己的學養、經驗,在取舍中作出選擇。”既承認譯者所承擔的責任與特殊地位,又不忘譯者的主見、原則和選擇。在談到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時,許鈞指出:“一部作品被引入一個新的語言與文化環境,文本生命所賴以生成的條件與環境發生了變化,原作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形,問題的關鍵在于,原作的變形,有的是由于可觀的障礙和各種差異造成的,而有的則是譯者主觀的追求。”(許鈞,2003:6-11)在他們看來,譯者的主觀性不可避免。黃振定(2005:19-22)在談到解構主義對翻譯主體性研究的理論貢獻時指出,“解構”的要義是“破壞”、“毀滅”(unmaking),它不僅闡明了一般閱讀的開拓創新,還特別合理地揭示了翻譯的創造性——并非主觀任意的“胡譯”或“超越”。言下之意,翻譯的創造性自然包括主觀故意的“胡譯”或“超越”。
陳大亮在分析作者中心論范式下的主體性表現及其存在的問題時指出:“正因為有理解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存在,譯者不可能不帶有自己的‘前理解’客觀地理解原作者的意圖,也不可能填平時空所造成的溝壑……理解的主體性不僅表現為合理的偏見……那種全然不顧理解主體存在,忘卻對自我前提的分析,要求將理解主體的存在回歸到文本之中,作無理解主體的理解的觀點只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陳大亮,2005:5)很顯然,他只是把譯者表達合理的偏見看作是譯者主體性的一種表征,殊不知作為文本理解者的譯者在歷史的文本面前必定會表現出不合理的偏見。與其說這種不合理的偏見是理解者主體性的一種表征,倒不如說是理解者的一種主觀性體現更為恰當。其實,邏輯實證主義的維也納學派的奠基人莫里斯·石里克(1882-1936)早就認為,實在知識里的時間、空間和感覺質都具有主觀性(石里克,2010:299-322),更不必說時空下的理解了。
3.人的自然屬性與翻譯主體
主觀性與主體的人密切相關。哲學上如何界定主體一直存在著爭論。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主體是一個對象性范疇,只有在對象性關系中才能獲得自己的規定。笛卡爾、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將人的理性和感性視為主體(劉宓慶,2007:49)。主體的理性表現為能動性,主體的感性則表現為主觀性。黑格爾認為“主觀性只是作為主體才真正存在”。在絕對意義上講,只要人作為主體存在著,就無法真正解除自我中心化,必定存在著主觀性(何中華,1992:17)。主觀性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自然屬性。
主體的自然屬性制約了主體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廣度和深度。“人類天生就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不擁有既一覽無余、又明察秋毫的‘上帝之眼’或‘天眼’(eyes of God)。人類的感官和大腦限定了自己所知和所能知的世界的廣度和深度,也限定了自己的認知的形式、范式乃至觀點”(李醒民,2009:113)。因此,主體有其本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有限的主體在無限的世界面前總是信以為真地探尋奧秘和真理,汝不知多少被蒙上主觀色彩,這不是對真理和科學的懷疑,而是對人的認知能力的實事求是。
以此觀之,不論是譯者還是讀者,翻譯中的主體同樣不具有“上帝之眼”,甚至更糟。所以“透明”、“忠實”的翻譯只能是一個假定(謝天振,2000:3)和一廂情愿,譯者對原作的理解與表達一定會因譯者自身的局限性而呈現出主觀性。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說的那樣:“譯者介入神人之間,既要通天意,又得說人話,真是‘左右為難’。讀者只能面對譯者,透過譯者的口吻,去想像原作者的意境。翻譯,實在是一種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詞’。”(余光中,2002:55)。他雖未直截了當地使用“主觀性”,但“一面之詞”不就是譯者主觀性的另一言說?
在福柯的知識譜系學里,文本的“歷史”不是由連續性的確定事件構成的,而是由不確定的“斷裂”構成,主體就被散布于多種可能的位置。沒有任何一個領域如同翻譯活動那樣更能體現主體這種內在的“斷裂”。在大量的話語實踐中,翻譯活動的“主體”所面臨的是最不安全的處境。對于主體,它意味著對于自我整合性的否定,意味著進入陌生的區域使得主體失掉這種整合性而發生“彌散”。于是,斷裂、彌散、差異和不確定性構成了主體的可能存在的狀態(許寶強、袁偉,2001:5-7)。不難看出,“斷裂”的譯者主體在“歷史”的文本面前往往迷茫而無助。于是“操縱”、“消解”、“顛覆”等成為譯者“敲擊”文本的手段,推測、主觀臆想就成了“不在場”主體解構意義的不二選擇。
此外,主體還具有一般“人性”所具有的傾向——主觀偏好。作為從事對象性實踐活動的主體——譯者——如同其他科學家一樣具有“我們所謂的‘人性’,不是指作為一個物種或人種的本性,而是指個人或科學家的人的本性的方面,特別是他們的正常的感情和偏好等。馬奧尼指出,科學家在履行他的職業角色時是主觀的——他往往是明顯易動感情的”(李醒民,2009:114)。顯而易見,理性的科學家們在需要理性的科學面前都是會彰顯動情和主觀,更何況感性十足的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及其譯者?譯者所從事的工作就是集藝術性和科學性于一體的思想活動,需要比普通讀者擁有更高超的跨越文化差異的想像力。難怪陳西瀅在《論翻譯》一文中提出只有當譯者與原作者的心智相同時,幸運的譯本才會產生。
4.語言的主觀性——翻譯中介與承載的規定性
語言是翻譯實踐活動中主體(譯者)與客體(文本)的工具和載體。沒有什么比語言更能決定翻譯的本質。自從哲學的“語言轉向”之后,“語言主觀性”便成為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范疇。Lyons(1997:739)明確指出:“主觀性是指語言的這樣一種特性,即在話語中多多少少總是含有說話人‘自我’的表現成分。也就是說,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這一方面是反映語言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又使語言帶上任意性的成分,意義因人而生。人們可以從說話人視角、情感和認識來發現語言的主觀性表征,如句式、指示語、時體、情態、語氣、語篇標記等,可以說語言主觀性體現在語言的各個層面。
語言的意義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在使用中確定的而具有相對性。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的實際運用是一種“語言游戲”,就如下棋、打牌一樣,在各種各樣的游戲包括語言游戲中,并沒有共同性,只有相似性。人們常用的語詞、概念并沒有確定不變的意義,它們存在于“語言游戲”之中,即依據具體的、特殊的條件和場合來確定。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人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顯然,理解語言是與理解者本人聯系在一起的。理解者的文化背景、思想狀況、情感意志、知識經驗等主觀因素在理解的實際過程中構成了語境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理解的現實因素。
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之間的翻譯實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際。那么,人與人之間語言交際的前提是:一切認識都能由語言來表達、傳遞嗎?事實上,在人類的認識中,有相當一部分只能是了然于心去無法形諸語言的,除了存在能用語言表達的“言外之意”外,還存在著與之對應的“意會認識”。莊子曾經精辟指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莊子·秋水》)維特根斯坦也指出語言有不能談論的東西,有拋開梯子才能到達的彼岸。“意會意識”與特定的認識主體緊密相連,不是純粹理性,常滲透著認識主體的情感、欲望、需要和動機等意向成分,只能憑借認識主體的多種心理機能和個體的獨特經驗來認知和領悟它,因此它必然帶上個體的主觀性成見。
5.主觀性識解——翻譯行為的路徑
“識解”是指人們可以用不同方法認識同一事態的能力,因而具有主觀性。有學者認為翻譯也是一種體驗性的認知活動,那么“主觀性識解”必然會在翻譯中起重要作用(王明樹,2009:15)。基于對認知科學識解觀的理解,對原文的理解和解析過程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對原文的主觀性識解。
翻譯是一種體驗性的識解。我們常說理解就是翻譯,實質上翻譯更是一種體驗。陳永國(2005:8)指出:在語言的外圍存在某種任意的偶然性,某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意義的播撒,以及由兩種被命名的歷史語言所創造的一個空曠的沉默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作為閱讀的翻譯變成了一種身體行為,變成了快感的產生;而作為讀者的譯者則行使著“愛”的權力,在閱讀和交流中感受著“愛”的甜蜜(或苦澀),在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徘徊往返中體驗著一種包含有他性的經驗。在這里,情感、思想和詞語都在愛中產生,翻譯的過程變成譯者一種語言和身體交流的體驗。翻譯,包括對原文的理解和接受、詞語的增補和刪減、意義的傳達和丟失、個人習語的使用等,都取決于譯者身體稟賦的偶然性,取決于譯者愛欲沖動的狀態。其情緒的飽滿和呆癡,激情、靈感、喜悅乃至成就感等精神因素都決定著翻譯的結果,它賦予原文/譯文的生命是單純的詞語轉換所無法獲得的。翻譯的過程是譯者對文本切身感受的過程,他往往會結合自身的體驗去感悟,帶著自己的情緒去理解。文本的情景和語言會在譯者心靈產生“映射”,對文本中具有體驗性的語言和情景的譯者會用自己最熟悉最生動最貼切的目的語語言表達。反之,對文本中不具有譯者體驗性的語言和情景,譯者只會基于自己既定的經驗和語言知識認識能力去加以主觀識解,作出“自以為是”的翻譯。
翻譯是一種動態性的識解。王寅(2008:211-217)以《楓橋夜泊》等40篇英譯文為素材分別從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和詳略度等四個方面分析了翻譯的主觀性。他認為譯者在對一個表達式的意義或結構的理解與翻譯時首先需要相關的體驗和相關的概念域,如對“泊”一詞的翻譯就要體驗和想象用繩子把小船拴在河邊樁上的情景;然后就應當考慮從哪一個視角來理解原文,這里涉及譯者與事件之間的相對關系以及原文中人稱、分句的語法主語等問題。第三是在有了范圍和視角之后,就要抓住場景中的哪一部分進行描述而加以突顯,這跟譯者的注意力和認知能力有關,他會重點關注主觀上對某一事體感興趣或最感興趣的部分。最后譯者還會對原文翻譯呈現詳略度差異,他可能聚焦某個部分加以詳細地翻譯,也可能對某個部分只是輕描淡寫,對原文中有關信息予以刪減或僅用少量詞匯來加以表達,甚至詳細程度少于原文。實際上,譯者對文本的不同部分會采用不同的識解形式,各種識解形式在翻譯過程中交替使用,不管譯者是采取哪種識解機制,識解會因主體策略不同呈現出對原文意義識解差異性。因此,任何文本的翻譯不會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6.翻譯主觀性之表現形式
6.1 通過翻譯主體意識的選擇性表現出來的主觀性
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主體的勝利系統對客觀外界刺激的信息具有選擇功能。就翻譯而言,譯者意識的選擇方向容易傾向那些能夠吸引他的東西。不僅如此,感官能對他所感受到的任何事物進行選擇。而且,譯者的生理系統對外部刺激——文本具有主動的過濾作用,外部刺激經過這種過濾就已經發生了某種折射或變形。思維科學也表明,人類思維(無論抽象思維、形象思維還是直覺思維)也不可能復制與再現對象本質的全部多樣性,而是有所篩選和取舍。從認識內容來看,不同主體對研究對象,即便是同一對象,也會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從而造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很不相同的認識結果。
翻譯主體對文本的認識總具有自覺的選擇性,這種選擇性是由目的來控制的,如我國洋務運動時期的翻譯活動主要為了戊戌變法、變革時局,當時主要的翻譯活動都受制于這一目的。當然,翻譯主體的認識目的不是憑空杜撰的,為何翻譯、翻譯什么、翻譯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誰來翻譯,一方面取決于翻譯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取決于譯者主體以前的實踐經驗,依賴于主體關于認識文本客體對自身活動意義的價值評價,這種價值評價是實施翻譯行為和實現翻譯特定價值的基本動因之一。而當一經形成的特定價值目標以翻譯目的的形式納入翻譯主體的認識過程,就構成翻譯活動的起點,決定翻譯對象的選擇,支配翻譯的整個過程,制約翻譯的最終結果。
6.2 通過翻譯主體意識的情感性表現出來的主觀性
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一個知、情、意三者統一的,內容極其豐富而又錯綜復雜的過程。情感是翻譯主體對客體文本的認識而產生的對客體文本是否符合翻譯目的以及自身需要的態度的體驗,它通常以主體滿意不滿意、肯定或否定、贊成或厭惡、愉快或憤怒等心理狀態表現出來。意志是翻譯主體在一定理性的支配下,自覺地確定翻譯的目的,并為實現預定的目的而有意識地支配、調節其翻譯行為的心理現象。從這一方面來看,情感和意志是翻譯主體意識性的產物和表現。另一方面,情感和意志又作為翻譯主體能動性的內部因素,反過來影響和制約主體的意識。它們不僅支配一個具體翻譯活動的發動,影響翻譯活動的效率,成為發動、延續、強化或中止主體翻譯活動的動因和動力;而且積淀到翻譯結果之中,使翻譯主體意識的內容具有主體獨特的情感性。
6.3 通過翻譯主體意識的創造性表現出來的主觀性
許鈞教授(2003:9)指出:“所謂譯者主體意識,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現的一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及其在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意識。”人的認識不是主觀與客觀簡單的對號入座,而是能動的創造,認識過程是反映過程和創造過程的統一。翻譯主體意識的創造性首先表現為理想性譯本客體的建立。所謂理想性譯本客體就是借助于翻譯主體的抽象能力建立的、在翻譯實踐中孜孜以求的、符合所謂翻譯標準(如信、達、雅)的譯本客體。理想譯本客體是譯者對原文對象本質方面合乎目的語規律的創造性的反映。其次,翻譯主體意識的創造性還表現為譯者的意識能超越個別性把握普遍性,超越有限把握無限。任何文本的產生都是歷史的,譯者本人也是歷史的,譯者對文本所認知的和文本原本所要表達的不可能直接統一的。再次,翻譯主體意識的創造性還表現為翻譯理念的形成。翻譯的根本任務是按照翻譯主體設定的目的,用目的語對原文進行語言轉換,以創造滿足人類需要的對象。翻譯不僅按照原文本身的語言邏輯、文化邏輯以及事件邏輯等進行活動,而且要把翻譯主體自己內在的尺度運用到譯本客體上去,創造體現著兩個尺度的統一因而對翻譯主體來說是“應當如此”的譯本客體。為了在翻譯實踐中創造這種客體,就必須事先通過思想實驗或思想預演,把兩個尺度觀念統一起來,為翻譯實踐活動過程及其所要達到的結果建立觀念模型。在這一翻譯理念形成過程中,翻譯主體意識不僅反映原文客體現存的樣子,而且反映根據翻譯主體的需要它可能被改造成的樣子,翻譯主體的主觀創造作用是很明顯的。
7.結語
盡管客觀忠實地向目的語讀者傳遞原文思想是翻譯存在以來始終不一的目標,但作為主體的譯者(或讀者、發起者、贊助者)和作為客體的以思想、情感等為主要內容的原語文本和譯語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主觀屬性。正是由于翻譯的這種主觀性,才使翻譯主體能夠對客觀文本(原本和譯本)信息進行抽象概括,從詞語到篇章,從顯現到隱含,從文本內到文本外等進行想像、預測,設計理想客體,進行創造性思維,才使得翻譯異彩紛呈。那些主張翻譯純粹是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對等,企圖用譯文文本來還原原語文本的客觀論思想是一種超然的主觀愿望,是把譯者看作一種毫無任何情感、“出污泥而不染”、好像一面鏡子的翻譯機器。這種客觀反映論所追求的客觀性將主體排除在外,但這種排除其實本身包含著一個矛盾:一方面,翻譯主體要對原語文本進行客觀反映,就必須排除主體在對原文的理解過程中所起的主觀作用才能達此目的;另一方面,翻譯主體又必須參與認識過程,因為沒有主體的參與,反映就不可能成立,因而主體的參與及其主觀性的介入對于認識結果又是一種永恒的必然。
[1]Dryden,Hohn.Metaphrase,Paraphrase and Imitation[M].Andrew Chesterman(ed.),1989:7-12.
[2]Gouadec,Deniel.Traduction Signaletique[J].Meta,1990,35(2):332 -341.
[3]Hermans.T.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Target,1996,8(1):23 -48.
[4]Levy,Jiri.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C]//To Honor Roman Jakobson.The Hague:Mouton,Vol.2,1967:1171-82.
[5]Leighton,Lauren G.Two Worlds,One Art:Literary Translation in Russia and America[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1.
[6]Lyon,J.Semantics(Vol.2)[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7]M.A.K.Halliday & M.I.M.Christian.Matthiessen.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CASSFLL,1999.
[8]Newmark.P.Approach to Translation[M].London:Prentice Hall,1988.
[9]Steiner,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econd Edition,Oxford:OUP,1992.
[10]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11]陳波.論意識內容的主觀性[J].湖北大學學報,1989(1).
[12]陳大亮.翻譯研究:從主體性向主體間性轉向[J].中國翻譯,2005(2).
[13]陳永國.翻譯與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9.
[14]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評[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5.
[15]黃振定.解構主義的翻譯創造性與主體性[J].中國翻譯,2005(1).
[16]何中華.主體性問題及其誤區[J].哲學動態,1992(8).
[17]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7:3.
[18]劉宓慶.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11.
[19]李醒民.論科學不可避免的主觀性[J].社會科學,2009(1).
[20]羅新璋.翻譯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5.
[21]石里克(德).普通認識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5.
[22]王明樹.翻譯中的“主觀性識解”——反思中國傳統譯論意義觀[J].重慶大學學報,2009(4).
[23]王寅.認知語言學的“體驗性概念化”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析力——一項基于古詩《楓橋夜泊》40篇英譯文的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3).
[24]謝天振.翻譯的理論構建與文化透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12.
[25]許寶強,袁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
[26]許鈞.“創造性叛逆”與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1).
[27]余光中.余光中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1.
[28]張美芳.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