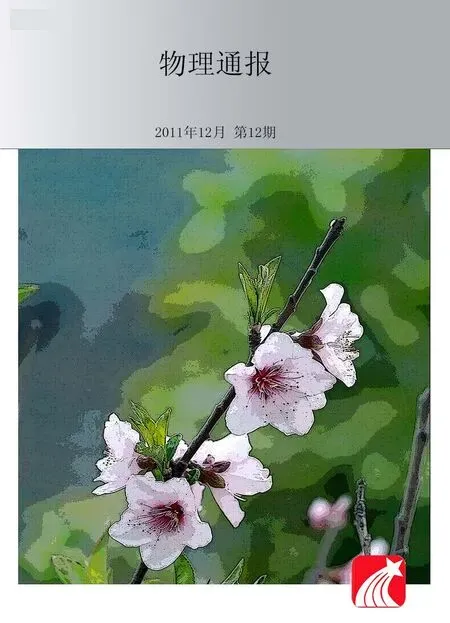從文化的角度審視科學與人文*①
薛永紅
(華北科技學院基礎部 北京 東燕郊 101601)
王洪鵬
(中國科技館 北京 100012)
1 問題的由來
20世紀50年代,就職于英國劍橋大學的斯諾(C. P. Snow),雖然是一位科學家,卻以一個人文學者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準確地捕捉到彌漫在劍橋大學乃至整個社會的兩種文化分裂甚至對立的現象;由此成就了他之后轟動學術界的關于“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雖然斯諾并不是首先提出“兩種文化”命題的人,但是不可否認,因為他,才使這一命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并且深入人心.按照劍橋大學史蒂芬· 科里尼(S. Collini)教授的說法,斯諾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發明了一個詞匯或概念,闡述了一個問題,引發了一場爭論.”[1]
自斯諾以后,兩種文化的命題及其隱含的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擔憂造就了曠日持久的關于兩種文化的分裂與融合的辯論.這一現象的出現,說明人們一方面承認科學與人文分裂的客觀現狀,另一方面也承認科學與人文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即二者有本質區別.在此基礎上,討論科學與人文以什么樣的方式、在何種層面、以何種程度進行融合.斯諾本人也明確地指出,融合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所有這一切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重新考慮我們的教育”[1].與此同時,身處美洲大陸的科學史學家薩頓(G.Sarton)提出“科學史是溝通科學與人文的橋梁”,后來也有學者提出科學人文化與人文科學化等命題來使二者相融合.不可否認,這些關于科學與人文融通的方式具有可行性,但仔細分析,似乎存在天然的缺陷.
2 重新審視科學與人文
回溯到斯諾和他的研究本身發現,斯諾是出于對人類前途與命運的關心,指出社會上存在著兩種文化,一種是人文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存在一條相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甚至存在著敵意和反感.對立的雙方經常以無知的自大而蔑視對方[1].在詳盡地論證了確實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文化之后,斯諾還特別指出了這種文化上的分裂將造成的危害——會使一些即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無法在同一水平上就任何重大的社會問題展開認真的討論.而且,由于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只了解一種文化,因而,很可能對現代社會做出錯誤的解釋,包括對過去進行不恰當的描述,對未來做出錯誤的估計.產生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們對專業化教育的過分推崇和要把社會模式固定下來的傾向,因為人們總是希望一個人能最快地在某一領域達到很高的層次[1].
但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真的有本質區別嗎?科學與人文的本質又是什么?
當把科學納入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的時候,我們發現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過程是與人類文明的演進密不可分的;其本質在于不斷地推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光在物質層面,還有精神層面.這樣,我們就可以認為科學本身就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或者科學本質上就是人文的.當科學在本質上具有人文的特性時,科學與人文的融合、科學的人文化等命題將失去其存在的邏輯前提.但是事實上,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客觀存在的;造成這種分裂局面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有文化的、觀念的、教育的等各種原因,其中的一種觀念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科學觀念,即人們對科學本質的看法.因此,我們將借助科學哲學的理論做進一步的分析.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的本質就是數理邏輯和實證,強調科學的精確性、實證性.當實證性受到威脅的時候,卡爾·波普爾(K.Popper)便以證偽的方式、拉卡托斯(I.Lakatos)則以“硬核與保護帶”的概念來盡心地辯護.到了歷史主義,托馬斯·庫恩(T.S.Kuhn)似乎開始對科學的人文性有了覺醒.他認為科學的變革和社會革命具有類似性,即當舊的范式不能解釋的問題——反常問題越來越多的時候,科學革命就會爆發,結果是新的范式代替舊的范式,同時他從科學家群體、科學家個人的心理及價值取向等方面說明其所指的范式.后現代主義則開始趨向于承認科學的主觀性、相對性,即科學是科學家群體所建構的一種對科學現象的相對比較合理的描述,而建構的過程是和科學家群體、個人所處的文化背景、審美取向、價值觀念等有密切關系的.到了費耶阿本德(P. Feyerabend),他不但開始激烈地反對方法,甚至取消了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也就是“不賦予科學以優于其他形態知識或其他傳統的地位”[2].同時強調尊重科學家個體的主觀愿望和自由.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學哲學中對科學本質的認識經歷了強調精確性、實證性、邏輯性到主觀性、相對性、歷史性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過程使科學越來越具有人文的特性.當然不能就此武斷地認為科學就是人文;但是最起碼可以認為科學應該具備人文性的性格.這樣一來,對科學形象的表述將變得非常豐富.科學可以作為一種建制、方法、積累的知識傳統,一種維持或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一種信仰和對人類的態度(貝爾納法)[3].科學本身就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體,或者科學本身就是人文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
3 科學教育的出路
雖然科學本身是人文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但是在目前,無論是大家的共識還是實際情況,科學與人文還是隔離的,尤其是在教育范疇(包括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對于學校科學教育,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僅僅引進科學知識本身,即顯性的知識和技術,而漏掉了科學作為隱性的文化內涵,其核心就是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的.也就是在一開始就將科學的人文性隔離在了科學之外,科學成為單向度的科學.民國初年,時任《科學》雜志主編的任鴻雋先生認為:“欲效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紹介整個科學(包括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4],并且批評國人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同時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只重視知識的傳授,過于依賴書本,忽視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科學教育弊病.
就目前的科學教育現實來看,人文性的普遍缺失(或科學與人文的隔離)在科學教育的整個因素(如教學綱領、教師、教材等)、環節和過程中,不但被合法化,而且進一步得到了鞏固.以教材為例,科學教材在編寫過程中僅僅重視科學的邏輯過程而忽視科學的歷史過程;重視科學過程的實證性、精確性而忽視科學發現中存在的偶然性、不確定性;重視科學家在科研過程中實事求是、不屈不撓的優良作風而忽視科學家作為一個人的個性心理、審美取向、價值觀念;重視科學轉化為技術對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作用而忽視科學作為意識形態對人類精神文明的巨大價值;重視科學的正面價值而忽視其負面作用[5]……科學教材林林總總,但基本上千篇一律.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十幾年的教育經歷中,人們似乎從來沒有從科學教育中得到人文的熏陶,似乎從來沒有從一本科學教材中讀懂它所涵蓋的人文關懷……這造就了根深蒂固的關于科學與人文是不相關的前概念.因此,在基礎科學教育中要實現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首先需要解決教材編寫的問題,其中以文化敘事的方式進行編寫科學教材將會是一種非常可行的方式.按照目前對科學教材的研究,做好以下幾點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第一,宏觀上要以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兩大文明)為主線,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展現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過程,既要體現兩種文明的各自特點,又要相互關照.
第二,對于具體理論的表述,要以其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為基礎,按照真實的歷史順序,重演該理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從而構建起符合學習者認知過程的“準”歷史過程.
第三,重視對科學價值的評判,既要揭示其對人類帶來的巨大利益,也要反思其潛在的危害[5].
這種處理實際上就是要將科學拉下神壇,揭開其神秘面紗,使其具有普通公眾理解的前提,使科學真正成為人類文化活動的組成部分.這無疑和費耶阿本德的初衷——不賦予科學以優于其他形態知識或其他傳統的地位——是相契合的.
參考文獻
1 C·P·斯諾.兩種文化.北京:北京三聯書店,1994
2 A·F·查爾莫斯.科學究竟是什么?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3 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4 任鴻雋.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5 薛永紅,石雷先.淺議“物理文化”的定義和傳輸問題.物理通報.2010(6):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