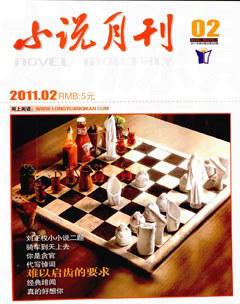楊二爺
王春迪
那時候,老家村子里的人氣,全攏在村口小店的墻根底下。
小店沒有名,以前也曾起過幾個,但,大伙都不興叫。小店也沒有門,只在齊胸高的外墻上開了一個兩人寬的柜臺。平日,老少爺兒們吃飽沒事,就喜歡倚著柜臺外面的水泥墻根蹲成一排,抽煙、嘮嗑、曬太陽、看莊鄰來往買東西。
可他們最喜歡的,還是聽楊二爺胡侃。
說起楊二爺,可了不得!當小伙子的時候,給淮海戰場送過糧。后來參軍,打渡江戰役,負過傷,立過功,繳過俘虜,去過上海,見過陳毅!有見識啵?更厲害的是,這些年,楊二爺侃的,不重樣!侃戰斗、侃戰俘、侃戰友,再侃戰友的戰斗、戰友的戰俘、戰友的戰友……老爺子在外不過兩三年的經歷,卻將店門口的小樹苗,足足侃成了合圍粗的老槐樹。
當然,二爺也會擺點兒譜。
一般,二爺總是牽著牛,打村路北邊過來,叼著煙袋,腿因渡江時負了傷,一瘸一拐,卻也不急不慢。那牛似乎也會耍威風,邁著方步,老遠便“哞哞”地叫,肆無忌憚。
近了,自有人將牛繩牽去,在不遠處,把牛橛子夯進草多的地方。然后將二爺蹲的地兒挪出來,一邊做傾聽狀。
二爺也不抬眼,只管抽煙袋,不做聲。待到人多了,二爺便故意打打嗓子,摳摳鞋上的泥巴。就等人請一聲:“二爺,要不,講兩句?”
二爺笑笑,“那,講兩句?”
緊接又說:“講兩句就講兩句!”
這就開始了。
二爺蹲的地兒,有講究,要靠著柜臺的右下角。右下角的一抹紅磚,長年累月,被二爺的后背磨得極為光滑,天好的時候,太陽一照,還反光!二爺就圪蹴在那兒,每每侃到白刃相接,喊殺震天時,這邊老少爺兒們抻著個脖子眼珠子都要跳出來了,那邊二爺忽然兩肩一松,向后一倚,不侃了。
就瞇著個眼,掏出幾張毛票,也不抬頭,往柜臺上一擱。
店掌柜趕忙打開酒壇塞子,滿滿打上一碗“柜臺酒”。自有人接了,雙手捧給二爺。那“柜臺酒”,山芋造的,雖賤,味大!只聞一下,這酒氣就直沖腦門,在鼻腔里經久不散,喝一口,更是跟吞了火一樣,從嗓門順道燒到肚臍眼。二爺端著酒,也不就菜,咬著黑碗邊,美美地“吱嘎”一下,下去一半,袖子一抹,幾滴還粘在花白胡子上,晶晶亮,亮晶晶。半晌,很舒服地呼一口長氣,五米外都能聞得著。
然后遞給周圍的老伙計,一人嘬兩口。
戰斗繼續。
當然,喝了酒,戰斗更激烈了。
這時,總有幾個人,打醬油忘了回家的,鼻子掛到嘴邊忘記吸的,打條魚拎在手里被貓叼去都不知道的,就連店掌柜的,出了神,都把醬油打成了酒,而把酒打成了醋的。
村子里的孩子,聽了戰斗故事,就開始依照故事里的情節,玩起打仗的游戲,直到被
大人擰著耳朵回家,齜牙咧嘴,還不忘學二爺的口氣:“狗日的,給我狠狠地打!”
一個村子的情緒,就這樣被楊二爺掌控著。
有時,村長有事和大伙商量,也不喊喇叭,只往小店那兒一望,準齊!直等二爺侃完了,把事一說,如是好事,大伙擁護;有問題,大伙一塊解決。
那時候,少有啥難斷的事兒。
二爺侃起來的時候,偶有一些小車子吱嘎停下來,扯著嗓門問路,態度倨傲,派頭十足,大伙總裝作不知道,待那人悻悻而去,二爺少不了譏誚他兩句,笑得大伙前俯后仰。
然而,一天,又來了一輛車子,卻不是問路的,是奔二爺來的。
原來,村長的兒子小胖,長大后成了一個軍旅作家,寫了一部小說,拍成電視,風靡全國。后來,電視臺聽說他的小說,源于楊二爺的故事,就扛著機子,拿著話筒,來請二爺到城里做節目了!
二爺想想,覺得沒啥,就去了。
可他對著攝影機,說得一點也不順溜。好不容易憋出幾句話,那頭,人家總說他錯。
二爺說,我這話講了幾十年了,咋錯哩!
那頭人們哄然大笑,笑得二爺心里發虛,覺得自己或許真的錯了,只得硬著頭皮一字一句地聽人家教他說,說得很生硬。
不久,二爺的節目播出來了,那晚,一村子的人圍著村長家的大電視興致勃勃地等著看二爺,可電視里的二爺,怎么看,怎么不像;這話,怎么說,怎么別扭。
就都回家了。
那晚,二爺沒去村長家,他在家,和老牛說了一夜的話。
好長時間,二爺沒在村頭的小店那出現。終有一天,他去了,可蹲在那,半晌說不出話來,店掌柜給他端了一碗“柜臺酒”,一口下去,二爺竟醉了!
從此,柜臺右下角的位置,就空了。
一年后,二爺的須發盡白,老牛走了以后,很快,他也就走了。
打那時起,村里人便很少聚在一塊了。
再后來,村頭的小店砸了,蓋起了三層小樓,而當年二爺圪蹴的地方,豎起了一塊高高的村碑,赫然刻著村子的名字。但,我們這些晚輩回老家的時候,竟然經常走過了道。
竟沒留心,那個擦肩而過的地方,原來就是我們的老家。
責任編輯孫丹dandan633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