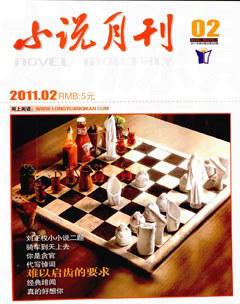夜的黑
陳毓
夜里十點(diǎn)鐘,鶴山公園的看門人老丁走出溫暖的矮屋去廁所,像每個(gè)夜晚一樣,他這個(gè)時(shí)候總要朝山下那片燈火望上一會(huì)兒,盡管永遠(yuǎn)弄不清哪盞燈是屬于秀的,但沒關(guān)系,因?yàn)樗肋h(yuǎn)確信,那盞屬于秀的燈就混在其中。二十年了,自從他在這個(gè)城市的一條窄馬路上和她偶然重逢,他就打算收住流浪的腳步,把自己殘存的光陰和她一起度過,在同一片地上同一片天下,呼吸一樣的空氣,看一樣的陰晴,哪怕只有這些,他也滿足。他在這個(gè)城市打一份又一份的臨時(shí)工,只為能留下來。他的心思永遠(yuǎn)沒法和別人說,包括秀,包括帶走了秀的黑子。是我讓你們走的,盡管你們一走我就后悔了,可我就是沒辦法呀,老哥,你比我強(qiáng)啊。這些話永遠(yuǎn)是老丁的心語,因此沒人能聽的見:要是我提早說出心思,你會(huì)為我留下?秀?生活無法假設(shè),但每晚睡前向山下眺望卻是老丁最大的自由。
這個(gè)夜晚,當(dāng)老丁又一次做他的晚課的時(shí)候,一束汽車的強(qiáng)光像一把明亮的刀,從空中劃過,光的尾巴掃到了他的眼睛上,強(qiáng)迫他閉眼,等他從突然的黑暗中恢復(fù)了視力,他斷定有一輛汽車正向他開來。
鶴山公園正在建設(shè)中,山下入口處就豎著個(gè)“游人止步!”的路牌。因此少有人來,更別說是開車來了,老丁因此心里有點(diǎn)不悅,他咕噥。“寒天凍地,黑咕咚咚,有啥可看的?”他站住,想等汽車開到大門邊時(shí)他再指教來人一番。但是,他站在那里三分鐘,五分鐘,直到十分鐘過去了,他也沒見有汽車開上來。老丁納悶了半天,疑惑,剛才是自己眼睛看花了?
他終于拐進(jìn)山上的臨時(shí)廁所,做睡前的清空工作。
然后,他就回去睡覺了,夜,如往常一般黑而且靜。
但是第二天醒來,卻是不同往常的。因?yàn)橐惠v汽車在距離鶴山公園大門不到二百米的地方翻出了路沿,掉進(jìn)了谷中,車上有一男一女。警察來調(diào)查,直接敲響了看門人的屋門。
老丁站在門口發(fā)呆,回想,把昨晚自己的所見、所做、不解、納悶、以及心理活動(dòng),口述一遍,然后在一個(gè)年輕警察的筆錄上按下手印。
接下來,看門人在第一時(shí)間跑到事故現(xiàn)場,他看見一輛汽車(是的,所有的汽車,無論型號(hào)、牌子,在看門人那里,都被統(tǒng)稱為汽車)還保有汽車的基本形狀,汽車打眼望去是黑色的,再看,是墨綠色的,癟癟的臥在那里,讓看門人聯(lián)想到一灘濕牛糞。
看門人迅速獲悉,被那一灘濕牛糞窒息了生命的一男一女并不是夫妻,這在不大的鶴城迅速成為緋聞。深更半夜,寒天冰地,在禁止游人深入的在建公園,這對男女,他們能干什么呢?想干什么呢?他們不是夫妻,不是兄妹,那他們,到底是什么關(guān)系呢?看門人聽著嗡嗡嚶嚶的議論聲,看著一張張翻攪著舌頭的嘴巴,看著一雙雙閃著莫名亮光的眼睛,他覺得不可思議,覺得十分陌生。咳、咳,他咳嗽兩聲,但是他的咳嗽聲沒有起到靜止作用。看門人悻悻地走掉。
可是走不掉,那些人倒追過來向看門人打聽他的所見,他們認(rèn)為,看門人這里連警察都來過了,可見是有直接的線索呢。
看門人什么都不說,他現(xiàn)在就像一個(gè)深沉的啞巴。直到多數(shù)人都失望地從他的小屋里退出去了。但世上總有好打聽的人,他們見從看門人那里打聽不到什么,只好先把自己的獲得放出來,仿佛看門人的話是一條深水里的大魚,只有他們放出誘餌才能釣上來。
一個(gè)中年男人憤憤地向看門人抱怨:婊子,風(fēng)流成性的婊子,看看,不得好報(bào)吧!他的語氣仿佛那個(gè)死了的女人是他妻子,但是,那個(gè)死去的女人顯然與他無關(guān)。
一個(gè)女人言之鑿鑿地說出事女人的男人是個(gè)大學(xué)教授,聽說大學(xué)教授得知妻子的死一點(diǎn)也不吃驚,仿佛聽說她要出差一樣。他作為死者一方的家屬也被警察調(diào)查了,但是,他并不認(rèn)得死去的那個(gè)男人,也不認(rèn)得死去男人的女人。他和死去男人的女人只是因?yàn)檫@一樁死亡案件偶爾相連。他們的見面,看上去既同病相憐,又存在隔閡。他們在警察的的監(jiān)護(hù)下認(rèn)領(lǐng)了各自配偶的尸體。對視了一眼,匆匆走開,仿佛忘卻死者的最好方法,就是連他們兩個(gè)活著的,也不要出現(xiàn)在彼此的記憶中。
看門人真佩服這個(gè)講話的女人,他覺得她講話倒像個(gè)女教授。但是他更不喜歡她。他在心里嘲笑這一男一女,說,你們說你們的書。說一說,就倦了。
只有夜晚總會(huì)來臨,再次走向那座山上的臨時(shí)廁所的路上,看門人先是長久地朝山下望,再朝山上那條路上望,山下明亮,山上黑暗,看門人站著,直到能在黑暗中看清身邊的所有存在,直到他最后斷定并沒有汽車朝山上開來。
他搖搖頭,嘆息一聲,心里嘀咕:誰都以為自己全知道,誰其實(shí)真的知道呢?誰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看門人在黑暗中對自己搖頭。
時(shí)間很快翻過了舊年,轉(zhuǎn)年春天來到的時(shí)候,看門人老丁有一天路過那個(gè)汽車翻下去的豁口,他不知道為什么,竟順著斜斜的土坡連跑帶滑地下去了,直到跑到當(dāng)初那輛汽車落地的地方,才停下。經(jīng)過了一個(gè)冬天,汽車的痕印已經(jīng)模糊不清了。看門人看了半天,想了半天,就用手中拖著的鐵锨,把附近疏松干凈的泥土培了幾锨在那個(gè)地方。他看了看,又走出去一段,他再回來,鐵锨上托著一窩紫花地丁,他最后把已經(jīng)抱花蕾的地丁花移栽到他新培上去的土中。
看門人攀上路沿兒,回頭看那個(gè)地方,自言自語。看門人說:有些事情,永遠(yuǎn)沒人能說清楚。
710068
西安市朱雀大街中段58號(hào)陜西畫報(bào)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