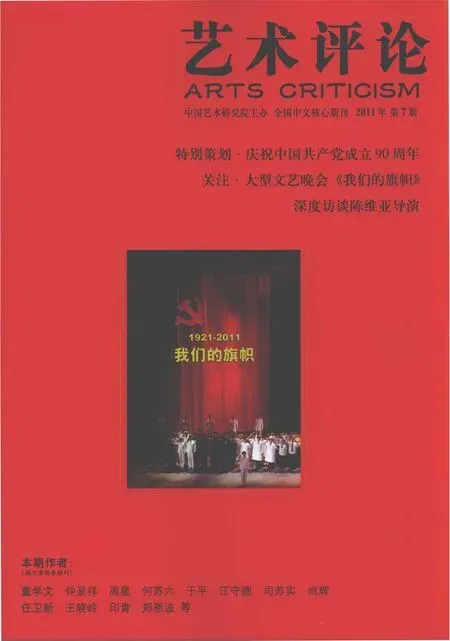《劉心武續紅樓夢》評略
關四平

《劉心武續紅樓夢》出版信息發布以來,質疑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認為狗尾續貂者有之,認為勇氣可嘉者亦有之。[1]筆者無意介入這個爭論,僅就續書本身談些個人讀后感受。
一
續書的出現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現象還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古已有之,前人對此已有定評。清人劉廷璣就指出:“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于世,即襲其名,著為后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后以續前者,有后以證前者,甚有后與前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2]這種批評基本符合事實。《紅樓夢》則不僅是“盛行于世”的問題,它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經典中的經典,代表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因此,對當代《紅樓夢》續書的首次出現,學界也不能僅僅限于視而不見,而應該給讀者一個客觀的評價與說明。這不應僅限于說好說壞的層面,還應該進一步指出好在哪里,差于何處。這也是一種創作經驗的總結。通過各種層次的比較愈可見出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的難以企及。
劉心武作為一位作家,在當代文壇上也曾取得可觀的創作成績。這應該是他敢于續補《紅樓夢》的基礎所在。他自言:“續寫《紅樓夢》蓄謀已久”,二十年來“發表出版大量談紅文字”;他“認為可以在探佚成果的基礎上,試以曹雪芹的思路、思想、風格來續寫八十回后的二十八回”。[3]問題是他的探佚研究采用的是“編造故事,過多地依靠主觀猜測”等“新索隱派的做法”,[4]這就會使其續書的基礎不牢,其“力圖恢復曹雪芹后二十八回原意”[3]的主觀追求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二
從整體構架層面觀照,《續紅樓夢》牽強附會處多而合情入理處少。從劉心武在卷首《說明》中的表述可知,他的確下了不小的功夫,創作態度也是虔誠的,續書中也不乏其得意之處,但刻舟求劍、牽強附會、違背情理之處也相當多。這恐怕是續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其實,任何續書作者的一個共同追求目標便是想要與原書的情節建構大致吻合。程偉元、高鶚也一再表明其要遵循曹雪芹的愿意,力圖做到“前后關照”,“有應接而無矛盾”。[5]他們在這方面的利弊得失學界多有評論,在此不贅,那么《劉心武續紅樓夢》與前八十回的關照、應接關系如何呢?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此僅舉其中重要情節為例以說明之。
關于黛玉之死,程高本寫的是病死的,而且是因為寶玉與寶釵成親其病情加重而死,實際上等于是殉情而死。這應該視之為與前八十回是吻合的,因為林黛玉一直身體不好,而每一次和寶玉產生感情矛盾都會加重其病情。而《劉心武續紅樓夢》則寫成了投水而死,且是在寶玉尚未成親之時。續作者把林黛玉的死因設計成趙姨娘的下毒導致“無法支撐”,“更緊要的是他淚已盡,在人間還淚的使命已經結束。”(第八十六回)這就把黛玉之死中所包含的豐富的感情因素與復雜的心理因素全然抹去,而主要歸之于神話因素。相比之下,哪一個既符合曹雪芹原意且更合情合理呢?答案應該是程高本。
續作者為了與前八十回呼應,寫黛玉死時“從容解下腰上那嵌有青金閃綠翡翠的玉帶,將其掛在岸邊矮林的樹枝上。……他用玉帶林中掛,告訴人們他是從這個水域里消失的。”這顯然是為了與第五回“金陵十二釵正冊”中的“玉帶林中掛”詩句相呼應,但僅限于表面,又太外露,有意為之的痕跡過于明顯。而“按那林黛玉,本是天界的絳珠仙草……”一大段話,更是重復曹雪芹筆下文字的贅語。
與此“玉帶林中掛”的坐實呼應相類的是續書中寶釵之死與“金釵雪里埋”的坐實描寫:“那寶釵這一倒,發髻上金簪落在厚雪中,直插朝天,閉目咽氣。”在曹雪芹筆下,“金陵十二釵正冊”中有意將黛玉與寶釵合為一幅圖、一首詩的設計,是為了回避二人排序先后的問題,其中“玉帶林中掛,金釵雪里埋”兩句,是以諧音的修辭手法,暗示二人的名字于詩中,并無預示其死時狀態之意。續作者如此呼應,未免有些膠柱鼓瑟,牽強附會。
妙玉的結局,“金陵十二釵正冊”中的“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之詩句的確有預示意味。因此,程乙本第一百一十二回擬出《活冤孽妙尼遭大劫》的回目,以妙玉遭強盜劫持的結局與前面呼應之。又留下一個懸念:“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6]《續紅樓夢》則設計成妙玉為了救寶玉而主動求見忠順王爺,“作筆交易”。雖然續作者讓妙玉說出“少不得自跳淖泥”、“白璧就污”等語,以之與前面呼應,但實際上妙玉不僅沒有就污,而是引爆煙花爆竹,與忠順王爺同歸于盡。這與前面八十回情節貌合神離,妙玉形象也與前不類,變成了帶有神秘色彩的女俠形象。
關于秦可卿之死,本來前八十回已經寫得很清楚,是病死的。而續書在第九十六回中一再借題發揮說明秦可卿的死因。先是借張太醫之口:“張太醫檢查了那女尸,確是賈元春無疑,啐道:‘你告發秦可卿,換取寵信富貴,畢竟一報還一報,也有今天。’”然后又借抱琴之口曰:“他見圣上盡棄前嫌親親睦族,方報知圣上,二十年來辨那秦可卿是誰,終于水落石出。圣上令那秦可卿自盡,允寧府大辦喪事,……圣上覺得元妃娘娘既深明大義,又能乞求赦免家族前衍,實在是忠孝兩全,故才選鳳藻宮,加封賢德妃,六宮恩愛,漸集一身。”這里的敘述問題頗多。第一,這里明確把秦可卿之死,歸于皇帝的賜死,這顯然與曹雪芹的原意不搭界。第二,續作者硬把元春說成是告密者,說她揭露了秦可卿為康熙皇帝廢太子的女兒身份,實屬無稽之談,這在前八十回毫無根據,是續作者生硬地把他的所謂探佚成果塞進其續書之中。這大大損害了元春的形象。第三,續作者把元春“才選鳳藻宮”的原因歸結為皇帝對她告密的獎賞,也與前八十回的描寫不合,純屬主觀臆造的不合情理的敗筆。
寶釵與寶玉定親也是一個重要情節,續作者為了與前面呼應,硬是在薛姨媽與寶釵的對話中,插入一段鶯兒的描寫:“倒是鶯兒聽了歡喜非常,拍手道:‘那年二爺跟姑娘互換佩帶,我在旁邊看得仔細,那通靈玉跟那金鎖上鏨的字句,竟對榫得嚴絲合縫。如今真成就金玉良緣了。’”(第八十八回)這既是毫無必要的贅筆,也不合情理。寶釵婚姻這么大的事情,一個丫鬟如何敢胡亂插嘴,再說薛姨媽根本就不會在有丫鬟在場的情況下商量這么重要的事。
石呆子扇子事件,續書中第八十四、九十八回兩次寫到,除了顯示續書與前面有照應而外,實在是無必要的浪費筆墨。
在續書末尾,續作者借二丫頭與史湘云的眼睛寫到:“只見門外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遠近一個腳印皆無。”這顯然是與第五回《紅樓夢曲》中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相呼應,但實際上也是犯了膠柱鼓瑟的毛病。曹雪芹原文只是一個賈府大廈傾倒的比喻而已,這樣坐實為某種景致,未免太笨拙了。這與程高本犯的是同一個毛病——“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并無一人。”——而又顯得更加穿鑿附會、生硬做作。
三
從小說品格層面觀照,《續紅樓夢》神秘低俗味重而真實高雅氣少。這是在閱讀《續紅樓夢》時一個很大的遺憾。李漁從小說戲曲創作的一般規律角度著眼,曾明確指出:“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7]魯迅先生在具體評《紅樓夢》時也有過精辟論斷:“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8]可見,《紅樓夢》的創新與魅力主要在于“寫實”這一點。而續書也未免落入了魯迅批評的“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的窠臼之中。試舉例論之。
如黛玉之死,續作者有意在制造一種神秘的氛圍,似欲以此氛圍來超凡脫俗,結果卻事與愿違,反而落入了古代小說創作中一種神秘怪異的老套路。且看:“他對自己是林黛玉漸漸淡忘,他越來越知道自己本是絳珠仙草。他是花,卻不是凡間之花。……當水沒到他腰上時,忽然他的身體化為煙化為霧,所有穿戴并那月云紗披風全都綿軟的脫落到水里,林黛玉的肉身沒有了,絳珠仙子一邊往天界飄升一邊朝人間留戀的眷顧,……”(第八十六回)這就把一個美麗不幸女子死亡的人間悲劇,變成了俗不可耐的道教信徒的尸解升天的喜劇。至此,續作者仍然意猶未盡,在第八十六回又進一步坐實、強化這種神秘氛圍。當眾人尋黛玉到水塘邊時,“眾人都看到黛玉的穿戴皆按其身前順序飄在水中,連繡鞋、釵簪亦浮在水面,……王夫人還說要撈取尸體,寶釵因道:“他是借這片塘水仙遁了!我們一天一天總顰兒顰兒的,只當他是個閨中良友,誰知竟是仙女下凡,總是他在凡間期限已滿,就飛升天界了。若非神仙,那些衣物并釵簪早沉入塘底了。那里還有肉身?”邢夫人也說:“林姑娘既是仙遁,他的遺言如何能夠違逆?”這種神秘化的渲染,既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也會令讀者感到無聊乏味。而程高本中的黛玉之死,格調則大不相同:“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第九十八回)語言簡潔,自然真實,無絲毫的神秘靈異氣氛,真實自然而令人心碎。
再看《續紅樓夢》第八十六回關于林黛玉流淚的文字,當寶玉問紫鵑:黛玉披風上“用紅絲線綴箍住一些血紅的寶珠”的來歷時,紫鵑曰:“你當是些寶石,實告訴你吧,是你林妹妹眼里溢出的紅淚!老太太過世時,你原也見過他流血滴子的。先時那樣的血淚珠子還能抹掉。后來,那紅淚珠子能接在我手里,先還是軟的,擱在白玉盤里,漸漸的就變硬了,隔些日子再看,就跟紅寶石無異了。”從寫實的角度說,這種淚變珠子的說法根本就不可能。續作者以如此坐實的情節來附會曹雪芹獨出心裁的美好空靈的“還淚說”,是化神奇為腐朽,實虛錯亂,令人生厭。
寶釵之死,也是續書的重要情節,續作者同樣以不可思議的細節來營造神秘氛圍。“那寶釵香魂已然出竅。麝月等三人將寶釵連抱帶抬送入房中榻上,彼時兩只秋后隕落在天花棚中的玉色蝴蝶,忽然蘇醒過來,從氣口飛出,在寶釵頭上蹁躚,麝月等驚奇不已,那一雙團扇般大的蝴蝶,隨即從風斗口飛了出去。麝月道:‘莫非寶二奶奶也和林姑娘一樣,是個仙女,如今也化蝶歸天了吧?’”(第九十四回)續作者的主觀命意可能在于:既與曹雪芹筆下的“滴翠亭楊妃戲彩蝶”相照應,也與他虛構的黛玉尸解相呼應,還想賦予其“梁祝化蝶”的文化意蘊,似乎是一石三鳥的得意之筆,但這只是一廂情愿,因脫離了曹雪芹“寫實”的風格,反而給續書帶來了隨意、神秘、俗氣的格調,產生了點金成鐵的遺憾效果。
從小說品格層面觀照,續書中“寶玉湘云一對鰥寡,正好因麒麟而聚合”(第九十五回)的刻意設計,也落了才子佳人小說的俗套,格調不高,了無意趣。還有像迎春的丫鬟蓮花主動迎合孫紹祖(第八十一回)、皇帝將元春腹內的胎兒“壓得流出”(第九十六回)等描寫,格調低俗,筆涉淫穢。襲人在“二寶衾下褥上,鋪有接紅單”(第八十八回)等繁冗描寫,也俗不可耐,多此一舉。與此相關,元春被勒死的描寫又過于殘忍血腥。這均應歸之于續書的品味不高,難脫俗氣。
四
從文字表達層面觀照,《續紅樓夢》平淡敘述多而感情含量少,這是不能感動讀者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學作品以打動讀者為創作目的之一,創作《琵琶記》的戲劇家高明曾指出:“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9]小說人物塑造過程中的感情表現應該是打動讀者的主要因素之一。《紅樓夢》前八十回中人物形象的感情表現應該視之為中國古代小說的典范,這也是它打動千百萬讀者的原因之一;后四十回雖相形見絀,但主要人物形象的感情表現仍然是相當豐富的,敘事中的感情含量也是相當濃厚的。如:林黛玉死后,作者反復渲染了一系列主要人物的情感表現,其中寶玉的情感宣泄最為突出,也最為動人。黛玉死后,寶玉的第一場大哭是寶釵告訴他黛玉已死的訊息后:“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第二場大哭是“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時:“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里,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眾人原恐寶玉病后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緊接著第三場痛哭是寶玉被“大家攙扶歇息”后,“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聽后“寶玉又哭得氣噎喉干。”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悲傷情感表現,才能夠與二人的曠世愛情相符合。與此相呼應,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也擬得相當精彩,可謂文題相符,相得益彰。
以寶玉的痛哭為中心,其他人的情感表現也足以令人動容。“黛玉氣絕”時在場的人是:“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賈母初知時是“眼淚交流”,然后是“要到園里去哭他一場”;“又哭起來”;“越發痛哭起來”;“又是哀痛”;“忍淚含悲”;“滿面淚痕”;“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就連寶釵也有不止一處的傷心落淚描寫:如“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其余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
相比之下,《續紅樓夢》寫到黛玉死后上述諸人的情感表現時,包括寶玉在內竟無一人落淚。這真是令人費解,違背人之常情。續作者似乎也想為自己的這種描寫尋求解釋:“因眾人皆知那林黛玉非凡人夭亡乃仙女歸天,故多只是嘆息,只紫鵑忍不住哭泣。”這種神秘化的解釋顯然不足以服人,更無法動人。關于寶玉的表現,作者也曾借助筆下人物來指出他的反常:趙姨娘“原以為寶玉會慟哭倒地,卻只見寶玉摩挲著那條玉帶出神”;“襲人亦覺意外,那寶玉竟無大悲慟,只是凝思”。但寶玉為什么會如此表現,作者并未能合情合理地揭示其深層原因,所以這種似乎欲以違背常情來追求出人意表效果的人物塑造,顯然是不明智的下策,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違背了曹雪芹追求人物情感真實自然的創作主旨與文學風格。
若再將續書與曹雪芹筆下寶玉與黛玉的情感表現比較一下,就更可知二者差距之大。在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錯里錯以錯勸哥哥》中,當黛玉得知寶玉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后,她的情感如潮水奔涌,毫不掩飾:“只見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可以想見,黛玉痛哭到何種程度,才能把眼睛哭得腫起來像桃一樣?人物的感情表現是何等的濃烈動人!回目擬得也好極,不避重復,連用了三個“情”字,意在以情動人。寶玉對黛玉的感情表現,正可與此相得益彰,當寶玉聽說黛玉要回蘇州時的表現是:“眼也直了,手腳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第五十七回襲人語)這才是比“哭”更能表現人物痛苦程度的高層次的感情表現。
從比較的角度看,續作者有意把程高本的一些重要情節加以改變,形成結局性質同而情節文字異的部分。從續作者的創作初衷看,似乎是為了避免雷同,或是想后來居上,但結果往往是白費功夫,事與愿違,甚至弄巧成拙,畫蛇添足。比如:司棋之死,在程高本中是司棋“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以簡潔而慘烈的文字生動地表現了其癡情、剛烈的性格。潘又安的殉情表現也是令人震驚:“他忙著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第九十二回)以真情追隨司棋于地下。這是后四十回的精彩構思之一。但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即這個情節是通過司棋母親派來的人向王熙鳳轉述的,而不是正面描寫,這就減弱了該情節應有的地位與份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劉心武在續書中將其改為正面描寫,增加了三分之一篇幅以加重其分量,且以回目“司棋殉情勞燕浴火”明確標示出來,這均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續作者將其自殺的方式改為自焚,則大可不必,男女主人公性格的剛烈程度與悲劇意味、審美感受等方面也因此有所降低,文字也顯得拖沓、煩冗。那么續作者為什么如此改變呢?續作者在字里行間似乎也透露出一些信息:“那性子跟一團火似的司棋,到頭來真化成了一團烈火”。這種意在賦予其象征味道的主題先行,反而給讀者刻意雕琢的感覺。還有司棋自焚引發了殃及無辜的不良后果:“司棋并前后五六家皆被燒得慘不得言。”這樣一來,司棋豈不成縱火犯了嗎?這恐怕也是續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五
若欲全面評價劉心武《續紅樓夢》的成敗得失,必須作多個層面的比較才行,如與程高本后四十回比較,與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庚辰本的比較等等,這不是筆者這篇短文所能夠完成的任務。其實,筆者的真實想法是:創作續書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事,除非續作者真正具有曹雪芹那樣的思想高度與藝術才華,那才可以一試,不然與其花費如此多的精力與筆墨去寫續書,還不如另起爐灶,獨出心裁地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那樣的創作意義可能會更大一些。
我們并不否認劉心武對《紅樓夢》的癡迷與專注,他花費二十年時間“了此心愿”[3],的確精神可嘉。而其失誤可能也就在于:他過于癡迷其探佚得來的帶有猜謎性質的一些索隱觀點,并將其情節化硬塞進續書當中,其客觀效果難免強加于人,生硬隔膜。這也是應該總結的文學研究與創作的教訓。比較而言,《續紅樓夢》無論是在思想層面還是在藝術水準上,總體上均不如程高本的后四十回。無論后四十回的續補者是高鶚還是“無名氏”,其突出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有的學者將其比作泰山,而將前八十回比作喜馬拉雅山,這個比喻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雖然泰山沒有喜馬拉雅山高,但它畢竟是五岳之首,廣大讀者已經接受了后四十回,并將其與前八十回視為不可分割的一個藝術整體。87版電視劇《紅樓夢》盡管有諸多優長,但其最大的不足,是后四十回的拍攝沒有尊重通行的120回本,而是根據探佚學的研究成果拍攝的。廣大觀眾對此普遍產生了拒斥心理,影響了整部戲的完整性與觀賞效果。這種教訓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劉心武不顧這個前車之鑒,盡管打著“恢復曹雪芹后二十八回原意”的旗號,其總體效果仍然無法望程高本后四十回之項背,更遑論曹雪芹原著了。
注釋:
[1]參見《中國文化報》2月23日許曉青、孫麗萍文。
[2]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24-125頁。
[3]《劉心武續紅樓夢》卷首《說明》,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所引《續紅樓夢》原文,均見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
[4]郭豫適先生指出:“劉心武的‘揭秘’和他的‘秦學’是用再創作的辦法編造故事,過多地依靠主觀猜測,恕我直言,這并不屬于科學考證,其實是新索隱派的做法。”見《博學慎思,實事求是——郭豫適教授訪談錄》一文,《文藝研究》2009年第5期。
[5]程偉元、高鶚:《紅樓夢引言》,程乙本《紅樓夢》卷首,見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第一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2頁。
[6]見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3頁。此書前八十回是以庚辰本為底本,后四十回是以程高本為底本,以下所引《紅樓夢》原文均據此書,不再一一注明。
[7]李漁:《閑情偶寄》,見徐壽凱:《李笠翁曲話注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頁。
[8]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頁。
[9]見高明:《元本琵琶記校注》,錢南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