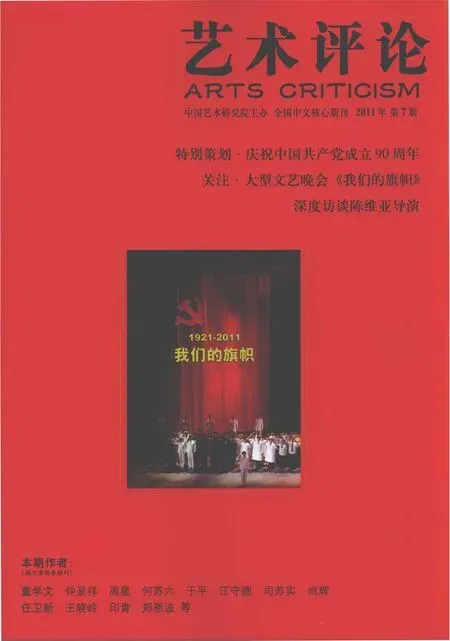我和我的阿爾巴尼亞文友們
鄭恩波

斯巴秀和戴代——我的兩個(gè)阿爾巴尼亞弟弟
毫不夸張地講,在留阿的學(xué)長們中間,能在40年的漫長歲月里,一直與當(dāng)年的阿爾巴尼亞同學(xué)保持著兄弟般的深厚友誼和同志式的親密合作的關(guān)系的人,恐怕只有鄙人一個(gè)。我當(dāng)年是以進(jìn)修生身份赴阿學(xué)習(xí)的,同時(shí)在幾個(gè)年級(jí)的文學(xué)班里聽課,所以結(jié)識(shí)的朋友很多,其中在63年入學(xué)的那個(gè)班里認(rèn)識(shí)的澤瓦希爾·斯巴秀和斯皮洛·戴代兩名同學(xué)是與我最要好的摯友。用北京話來說,我們是40年的“鐵哥們兒”。
斯巴秀于1944年出生于斯克拉巴爾農(nóng)村,礦工之子;戴代于1945年出生于紀(jì)諾卡斯特附近的扎高立,農(nóng)民之子。二人都酷愛文學(xué),自中學(xué)時(shí)代起,就開始發(fā)表詩歌。我比他們大5、6歲,出生在遼南渤海邊的一個(gè)山村,也是自中學(xué)時(shí)代起,就愛文如命并有散文作品發(fā)表。我們都嘗過吃不飽飯的滋味兒,我們都是苦水泡大的窮孩子,有許多共同語言,所以相識(shí)不久,就成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他們住在二層樓的28號(hào)房間,我住在30號(hào)房間,只隔一個(gè)門兒。我?guī)缀趺客矶家剿麄兾堇锎T兒,有疑難問題找他們解答,更是家常便飯。即使是考試的時(shí)候,他們對我也是照幫不誤。有時(shí)夜里時(shí)間拖得太晚了,我怕回自己房間打擾別人睡覺休息,干脆就在他倆的屋子里擺起椅子搭床邊兒。這么一來他們倆的聊侃勁頭更大了。我也不知是什么時(shí)候睡著的。突然,我被尿憋醒了,睜眼一看,燈還亮著,他們倆各自手拿書本擱在胸口上,睡得香著呢。
就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還未走出地拉那大學(xué)的校門,就翻譯了阿果里的長詩《德沃利,德沃利》,卡達(dá)萊的長詩《山鷹在高高飛翔》和《六十年代》,維赫畢·斯堪德利的長詩《一次交談的續(xù)篇》等一系列著名詩篇,為我后來的阿爾巴尼亞文學(xué)譯介工作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后來,這些作品大都發(fā)表和出版了。可是,有誰知道,在我的那些翻譯成果里,也浸透著他們兄弟倆的汗水呢。
不久,我們都畢了業(yè)。我被安排到《人民日報(bào)》工作;斯巴秀和戴代分配到《人民之聲報(bào)》工作。我們雖然分別了,但共同的新聞工作卻把我們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倆的才氣都很出眾,《人民之聲報(bào)》上幾乎每周都發(fā)他們富有濃厚的文學(xué)氣氛的長篇通訊;我在北京,也在《人民日報(bào)》國際版上,以“紅山鷹”、“紅英”、“辛文冰”等筆名,熱情滿腔地為中國的頭號(hào)朋友——英雄的阿爾巴尼亞大唱贊歌。那是偉大的中阿友誼日益發(fā)展、繁榮的黃金時(shí)期,我作為《人民日報(bào)》記者兼翻譯,多次赴阿訪問。每次我都不空手而去,總是給我的這兩個(gè)弟弟帶點(diǎn)具有紀(jì)念意義的禮品,他們倆也把自己出版的詩集送給我。就這樣,我們已把學(xué)生時(shí)代的友誼升華到一個(gè)新的高度——兩國新聞戰(zhàn)士之間的友誼。
一個(gè)人的成長,如同歷史的發(fā)展一樣,不可能是一帆風(fēng)順的,正當(dāng)我們處于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的興旺時(shí)節(jié),突然間,六月里下了一場九月霜。我因各種原因不得不撂下了手中的筆,去“五·七”干校整天與騾馬為伴。后來聽說,當(dāng)我身陷逆境的艱難時(shí)刻,斯巴秀和戴代對我的命運(yùn)極為關(guān)心,到處找熟人打聽我的情況。有一件事即可證明他們對我的一片兄弟之情:1974年,被流放干校2年之久的我,終于被宣布無罪解脫,再次赴阿訪問一個(gè)月。他們倆得到這個(gè)消息,在我抵阿的第二天,就立刻到達(dá)依迪賓館看望我,猶如親人一般詢問我和家人的生活細(xì)情。語言的親切,感情的溫暖,是當(dāng)時(shí)我從中國朋友那里感受不到的。
那是一段真假難辨,不正常的歷史發(fā)展時(shí)期。斯巴秀寫了那么多洋溢著澎湃的愛國激情的好文章,只因?qū)懥艘粌墒自诟邔宇I(lǐng)導(dǎo)看來不太健康的歌詞,便受到公開在報(bào)上點(diǎn)名的批評。不久,他被迫地離開了《人民之聲報(bào)》,幾經(jīng)周折,調(diào)到歌劇芭蕾舞劇院從事歌詞創(chuàng)作。當(dāng)時(shí),我從朋友那里聽到這消息之后,傷心極了,為斯巴秀這朵剛剛綻開的鮮花過早地遇到霜打感到痛心、惋惜。心里暗暗地思忖:像斯巴秀這樣忠于人民和祖國的人,都要受到如此打擊,難道還有可信賴的人嗎?痛心之余我又堅(jiān)信:金子有時(shí)會(huì)被埋在垃圾堆里,但它遲早還要重新發(fā)光,即使被打碎了,還是要賣金子的價(jià)錢。于是,我把報(bào)社里積存了幾年的《人民之聲報(bào)》,全都擺到辦公桌上,將斯巴秀的一篇篇充盈著才華和靈氣的通訊及詩作全都剪下來,張貼好,然后找印刷廠裝訂車間的師傅幫忙,給他整整齊齊地裝訂起來,作為對斯巴秀弟弟的一種安慰和支持,盡管此事當(dāng)時(shí)他毫無所知。
以后的10多年,中阿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令人遺憾的曲折,我與他們倆一時(shí)失去了聯(lián)系。可到了1990年,中阿關(guān)系又出現(xiàn)了復(fù)興的轉(zhuǎn)機(jī)。這年夏秋之交,我應(yīng)阿爾巴尼亞對外文委的特別邀請,作為阿爾巴尼亞文學(xué)研究者和作家,又踏上了已經(jīng)久違了16年的阿爾巴尼亞的神圣土地,再次與他們重逢了。這時(shí)的戴代已榮升為《人民之聲報(bào)》總編輯,但對我的學(xué)友之情依然絲毫未變,不僅幾次到我下榻的“地拉那旅館”看望我,與我暢敘友情,陪我到歷史_語文系路南邊綠蔭蔽天的樹林里悠閑散步,尋找青年時(shí)代的足跡和影子,而且還對報(bào)社接待室下達(dá)命令:“今后一個(gè)月里,每天都要把當(dāng)日出版的《人民之聲報(bào)》、《勞動(dòng)報(bào)》、《光明報(bào)》、《教師報(bào)》給鄭恩波同志留一份,他是我們報(bào)社最好的朋友。”這樣,在一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我便免費(fèi)閱讀了上述的各種報(bào)紙。在當(dāng)時(shí),戴代能對我這個(gè)老同學(xué)做到如此地步,已很不容易,實(shí)屬難能可貴。
這時(shí)的斯巴秀,似乎已從人生的低谷中走了出來,情緒還好,但不愿意提念往昔記者的生涯。我主動(dòng)向他索取通訊集,他無不感慨地說:“那些東西沒有太大意思,等我手上這部詩稿印出來后一定送給你。”我告訴他我已有了一本《斯巴秀通訊集》,他驚奇地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向道:“誰送給你的?”我告訴他是我自己為他剪報(bào)、裝訂而成的。他先是爽朗、開心地笑了笑,忽然,仿佛恍然大悟了似地,緊緊地把我抱起來拎了一圈兒,然后拍著我的肩膀說:“鄭,謝謝你的好意,我的中國大哥……”
1999年秋天,中國作協(xié)赴馬其頓代表團(tuán)歸來后,轉(zhuǎn)交給我一個(gè)便條兒,是斯巴秀寫給我的,從斯科普里向我問好。我為他能率領(lǐng)作家代表團(tuán),參加聞名歐洲的斯特魯加詩歌節(jié)的盛會(huì)而感到欣慰,同時(shí)也自然地聯(lián)想:何時(shí)斯巴秀也能來中國訪問呢?
2003年春夏兩季,我因?yàn)橐獛椭鶥GP完成一項(xiàng)特殊任務(wù),在闊別阿爾巴尼亞13年之后,又到了這個(gè)我日夜思念的國家,借此機(jī)會(huì)也會(huì)見了斯巴秀和戴代兩個(gè)弟弟。轉(zhuǎn)眼之間,他們也是將近花甲之年了,再也不見當(dāng)年風(fēng)流瀟灑的模樣。像我一樣,歲月和磨難也在他們不算蒼老的臉上,刻下了不少皺紋。斯巴秀濃密的黑黑的卷發(fā),失去了往昔的光澤,但依然精神矍鑠,健步如飛,氣宇軒昂,十分健談。那面容整個(gè)兒是普希金的翻版。衣著打扮,還是那樣普普通通,隨隨便便,跟學(xué)生時(shí)代沒有太大的差別。戴代的背稍有點(diǎn)駝,但卻還是目光炯炯,鶴發(fā)童顏,不大不小的將軍肚兒也初見規(guī)模。穿戴也不像當(dāng)年在報(bào)社工作時(shí)那么平常,讓人一眼就能看出經(jīng)濟(jì)狀況不太尋常,儼然一個(gè)大老板的神態(tài)和氣度。不同的儀表、裝束,給他們目前的職業(yè)和身份,作了很好的腳注:斯巴秀——浪漫味十足的詩人,總統(tǒng)府的文藝顧問;戴代——“阿爾濱”出版社的大經(jīng)理,全國著名的圖書出版家。
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一過了50歲,什么難于啟齒的話都說得出口。斯巴秀和戴代兄弟倆也不例外,跟我一見面,就把這些年來的酸甜苦辣、坑坑坎坎,一股腦兒全兜了出來,字字句句都撼動(dòng)我的心弦。不過,他們并沒有忘記我是個(gè)愛書如命的讀書蟲,因此,戴代便把我領(lǐng)到他的書庫,慷慨而真誠地告訴我:“鄭,這回可到了你早已夢想過的地方,這里的書隨你挑任你選,你想拿什么書,就拿什么書;愛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知道他的每本書都是有成本的,怎么能憑自己所好亂拿呢!他見我只是瀏覽,遲遲不行動(dòng),于是,架起梯子,到書架的高處,三下五除二,眨眼功夫抽出一大堆,專往文藝評論著作上盯。這堆書對我即將撰寫的另外兩部專著,將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的“阿爾濱”出版社以出版人文科學(xué)圖書蜚聲全國乃至巴爾干和歐洲,所有的書,不是經(jīng)典名著,就是關(guān)系到國家和人民命運(yùn)的正經(jīng)八百的書。我實(shí)在佩服他的遠(yuǎn)見卓識(shí)和對人民高度負(fù)責(zé)的職業(yè)道德。斯巴秀不從事圖書出版發(fā)行事業(yè),也就不能在向我贈(zèng)書這方面與戴代比武打擂。可是,他是個(gè)詩人,是阿爾巴尼亞當(dāng)代文壇上三大詩歌巨頭之一,他能把自己這幾年出版的3本詩作《阿爾巴尼亞詩歌》、《界線》、《危險(xiǎn)》全都送給我,已經(jīng)足矣。
7月14日晚上,我邀請13位阿爾巴尼亞好友,在地拉那“五·一”花園的“中國餐廳”小聚,斯巴秀和戴代是當(dāng)然的上賓。當(dāng)朋友們喝得最酣暢的時(shí)候,斯巴秀詩興大發(fā),朗誦了即興寫給我的一首詩,使晚餐的歡樂、喜慶氣氛達(dá)到了高潮。詩中寫道:
最親愛的鄭恩波,
對于我來說,你是一個(gè)不能忘卻的人,
永遠(yuǎn)留在心窩:
你的純潔,你的聰慧,他人很少具有的珍寶——
人的真誠的品格。
啊,人,啊,詩人,啊,來自偉大中國的偉大朋友,
我向你致謝,因?yàn)槟憬o予我的幫助很多!
你渴望它騰飛,四處傳播。
衷心地感謝你,斯巴秀弟弟!你的這首詩,是對我多半生的事業(yè)作出的最能讓我感到欣慰和快樂的評價(jià)。
親愛的斯巴秀和戴代,我們雖然出身貧寒,卻有著堅(jiān)定的志向,寧折不彎的品格。我們對青春無怨無悔,因?yàn)樵跒楣埠蛧鴱?fù)興、繁榮的偉大事業(yè)中,也有我們的心血和汗水澆灌出來的碩果!我們都有過夙愿:決心為實(shí)現(xiàn)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今天,盡管我們已是雪染霜鬢、皺紋滿腮的老人,但心里依然還燃燒著青春的烈火。歷史留給我們的時(shí)間已經(jīng)不多,很多事情正等著我們?nèi)プ觥W屛覀兘?jīng)常想想自己的年齡,趕緊快馬加鞭,全力拼搏。我們雖然是異國兄弟,血管里卻跳蕩著相同的脈搏。愿我們永遠(yuǎn)肩靠肩,手拉手,決不能在歷史的大搏斗中落伍一個(gè)。讓后世人拍手喝彩,贊美評說:阿爾巴尼亞的斯巴秀和戴代,中國的鄭恩波,他們不是兄弟勝似兄弟,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雅科夫老師一家人
結(jié)束了在BGP的工作后,該公司領(lǐng)導(dǎo)給了我在當(dāng)?shù)匦菁?0天的優(yōu)厚待遇,要我好好會(huì)會(huì)阿爾巴尼亞老朋友,因?yàn)樗麄冎溃乙簧氖聵I(yè)是緊緊地與阿爾巴尼亞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這個(gè)曾經(jīng)是我們的第一號(hào)朋友的國家里,我有數(shù)不清的朋友。確實(shí)如此,一般的相識(shí)者不算,光在新聞界、文藝界的“鐵哥們兒”,也有十幾個(gè)。

在要拜會(huì)的諸多朋友中,我自然想到了現(xiàn)任阿爾巴尼亞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經(jīng)理和總編輯阿爾奔·佐譯。他是阿爾巴尼亞最著名、最有影響的小說家,我當(dāng)年的恩師雅科夫·佐譯的長子。雅科夫老師于1979年因患癌癥去世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一腔尊師之情傾注在恩師的兒子身上。我也說不出更多的理由,在我的潛意識(shí)里,阿爾奔就跟雅科夫教授一樣。
按照朋友的指點(diǎn),七月初的一個(gè)早晨,我汗水津津地來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敲門,未過10秒種,門就打開了,只見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笑吟吟地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顯然,我的突然來訪出乎他的預(yù)料,臉上露出一點(diǎn)驚愕的神情。我立刻來了個(gè)三言兩語的介紹,話還未說完,他立刻緊緊地抱住我,眼睛里含著淚珠,激動(dòng)地說:“鄭叔叔,您這是打哪兒來啊?從天上嗎?”我問他:“37年了,我已變成了老頭了,你還認(rèn)得出來嗎?”他輕輕地松開胳膊,滿臉喜色地說:“人不管怎么變,眼睛是不會(huì)變的,您這雙善良的眼睛,跟37年前沒有什么兩樣。再說了,爸爸珍藏的照片中,還有您跟他在一起的合影。他在世時(shí),經(jīng)常對人提起您,說您是他所教過的外國留學(xué)生中最勤奮、最有天份的一個(gè)。您想,我們心中能沒有您嗎?”
聽著阿爾奔這句句情深意切的話語。端詳著他那大大的跟雅科夫教授幾乎完全一樣的四方臉,此時(shí)雅科夫老師善良慈愛的音容、舉止以及他與我既是師生又是摯友的親密交往中的一些細(xì)枝末節(jié),頓時(shí)像電影鏡頭一般,一個(gè)接著一個(gè)地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
我是在專門學(xué)習(xí)了一年阿語之后,于1965年秋季開學(xué)開始,到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一年和二年級(jí),聽與文學(xué)有關(guān)的課程的。聽“文學(xué)引論”課時(shí),班里只有我這么一個(gè)留學(xué)生。授課教授40歲剛過,但絲毫沒有青年教師常有的那種急躁的毛病。他的話講得很慢,關(guān)鍵的地方要反復(fù)重說好幾次,寫字快的阿爾巴尼亞學(xué)生,能把他講的每句話都記下來。然而,只學(xué)了一年阿語的我,聽老師講課猶如坐飛機(jī)一樣,很多句子記不下來。這時(shí),這位教授便把全班同學(xué)擱置一邊,走到我面前,把重點(diǎn)內(nèi)容一句句地重復(fù)幾次,直到我全聽懂了,記錄下來為止。這樣特殊照顧我的事不是一次,幾乎每次上課都是如此。這位善良仁慈,關(guān)心我到如此地步的教授不是別人,就是雅科夫·佐譯先生。同學(xué)們告訴我,雅科夫教授是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作家,他的長篇小說 《死河》,是阿爾巴尼亞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之一,頗有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氣魄。他原來是歷史_語文系的專職教授,自1965年開始,便作為作家與藝術(shù)家協(xié)會(huì)的專職作家,集中主要力量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附帶在我們系里講授文學(xué)理論。平時(shí)主要在從事寫作的基地阿波羅尼亞生活,有課時(shí)他才來系里。從阿波羅尼亞到地拉那有100公里,可他從來未缺勤過。
我對作家向來懷有崇敬的感情,對學(xué)者型作家更是要格外敬上幾分。于是,每次下課之后,總要和雅科夫老師攀談幾分鐘,有時(shí)甚至陪他回家,一邊散步一邊聊天。時(shí)間久了,他便主動(dòng)找我順著回家的人行道走上一程。記得有一次,上完課后,我陪著他一直慢行到水流潺潺的拉那河邊,談興仍然未盡。他特有感觸地告訴我,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他看到了一期法文版的《中國文學(xué)》,對該雜志特感興趣,以后如有可能,希望能經(jīng)常讀到它。我知道我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有英、法文版的《中國文學(xué)》,所以立刻告訴老師,從今以后保證讓他一期不漏地讀到這本雜志。我兌現(xiàn)了許下的諾言,從這次談話開始直到回國,我把每一期雜志都及時(shí)地送給了他,有時(shí)甚至親自送到了他家里。
我從地拉那大學(xué)回國后,經(jīng)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點(diǎn)名并批準(zhǔn),被安排在《人民日報(bào)》工作,主管國際部領(lǐng)導(dǎo)的對阿宣傳版面,有機(jī)會(huì)常到阿爾巴尼亞訪問。對此雅科夫老師感到非常欣慰、自豪,經(jīng)常把我的點(diǎn)滴成績介紹給他的朋友們。1974年11月—12月,我作為由張潮同志率領(lǐng)的《人民日報(bào)》記者團(tuán)的成員兼翻譯,又一次訪問阿爾巴尼亞時(shí),再次到了費(fèi)里區(qū)。車一開進(jìn)費(fèi)里城郊,我就想到雅科夫老師,因?yàn)樗麆?chuàng)作的基地阿波羅尼亞就位于離費(fèi)里只有20公里的海濱。多么想在此見到他老人家啊!要知道,到那時(shí)我已有6年未再見到他了。可是主人告訴我,雅科夫近日不在阿波羅尼亞,到外地去了。聞聽此言我是何等的悵惘。我把這一消息及時(shí)地報(bào)告給團(tuán)長張潮同志,他也感到很遺憾,因?yàn)槁犃宋业慕榻B,他也很想會(huì)晤這位阿爾巴尼亞的肖洛霍夫。可是,中午我們在餐桌上酒喝得正酣時(shí),陪同我們的《人民之聲報(bào)》負(fù)責(zé)同志卻接到了一個(gè)由地拉那打來的長途電話。5分鐘后,負(fù)責(zé)同志喜笑顏開地回到餐桌旁,告訴我們:“我們最敬崇的作家雅科夫·佐譯從地拉那打來電話,說他得到《人民日報(bào)》記者團(tuán)到費(fèi)里區(qū)訪問,特別是團(tuán)里還有他得意門生的消息,感到分外的高興,今晚他要在阿波羅尼亞的波揚(yáng)村的一個(gè)農(nóng)民家里設(shè)宴歡迎、款待記者團(tuán)全體同志。”這一消息使得記者團(tuán)全體同志酒興大增,個(gè)個(gè)都喝成紅臉大漢子,不是關(guān)公勝似關(guān)公。
晚6時(shí),雅科夫·佐譯老師主持的具有米寨嬌農(nóng)家特色的盛大宴會(huì)正式開始。雅科夫老師的左邊是團(tuán)長張潮同志,我被他拉到左邊,緊靠他的身旁。那天晚上,餐桌上一共上了多少道菜,事過30年實(shí)在是記不得了,不過,說那餐桌是用最美味的佳肴堆成的小山,那是不過分的。雅科夫老師平時(shí)很少喝酒,可那天晚上打破了慣例,不僅酒喝得多,話也說得多,而且全是實(shí)話實(shí)說,一句外交辭令和官腔都沒有。大家正吃著喝著,突然,幾位歌手在手風(fēng)琴的伴奏下,來到這戶農(nóng)家的庭院里,唱起民歌來,好聽極了。唱著唱著,他們又走進(jìn)屋里,當(dāng)著我們的面唱起中國歌曲《打靶歸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真正的朋友》,兩位少女還化妝跳起米寨嬌民間舞來,歡樂、友誼的氣氛達(dá)到了高潮,這是阿爾巴尼亞人歡迎尊貴朋友的最高禮儀。宴會(huì)結(jié)束后,雅科夫老師還主動(dòng)邀請我們一起照了像,并且又送給我們每人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小禮品作為紀(jì)念。對我這個(gè)學(xué)生還有點(diǎn)特殊待遇:將他的最新作品《幸福之風(fēng)》(第二卷)簽名贈(zèng)給了我。當(dāng)時(shí)他只有51歲,我35歲。然而,萬萬沒有想到,5年后,萬惡的癌癥竟奪走了這位風(fēng)華正茂的天才作家的生命,這次重逢反倒成了他與我的永別……
件件往事正在我的腦海里翻涌,忽然電話鈴響了,阿爾奔趕忙去接電話。這時(shí),女秘書按照阿爾巴尼亞家庭歡迎尊貴客人的禮節(jié),用干凈漂亮的塑料托盤端來了面包、食鹽、白酒等。阿爾奔很快打完電話,端起酒杯對我說:“歡迎阿爾巴尼亞人民尊貴的朋友,我爸爸的中國學(xué)生,今日的作家和阿爾巴尼亞文學(xué)專家鄭恩波先生到我們這兒來做客!”我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很高興見到我尊敬的教授,阿爾巴尼亞當(dāng)代最杰出、最富有天才的小說家雅科夫·佐澤先生之子,今日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阿爾奔·佐澤先生!”這一禮儀讓我想起當(dāng)年到雅科夫老師家里做客時(shí),他夫人杜拉塔教授代表全家歡迎我的情景,也想起她那能給人無限溫暖的慈祥的微笑、高雅的風(fēng)度和談吐。于是,便關(guān)切地向阿爾奔問道:“您母親怎么樣?她好嗎?我的問話使阿爾奔的眼睛紅潤起來,小聲地說:“媽媽,她……頭幾年也離開了我們……”阿爾奔的話仿佛像一個(gè)炸雷轟得我頭暈?zāi)X脹。我的手立刻顫抖起來,連酒杯也端不住了,趕忙放進(jìn)托盤兒里,酒水灑得滿盤子都是。“這……這怎么可能呢?”我問話的聲音也發(fā)顫了。阿爾奔說不出話來,只是聳了聳肩膀。我這顆容易動(dòng)感情的心,從一進(jìn)阿爾奔辦公室開始,就一直不平靜,此刻更是七上八下了,眼前又浮現(xiàn)出一連串的鏡頭:
杜拉塔,這位留學(xué)保加利亞的高才生,在索菲亞與雅科夫相愛,比雅科夫小5歲,是俄羅斯文學(xué)研究專家。回國后,先是從事教育工作,后到《教師報(bào)》從事新聞工作并間或有文學(xué)作品發(fā)表。晚年任“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編輯出版了許多文學(xué)名著。她本屬于高級(jí)知識(shí)分子,可是,我每次到她家里,她都像一個(gè)普通的家庭主婦那樣,為我和雅科夫老師燒茶和咖啡,驕嬌二字跟她毫不沾邊兒。
1968-1969年,我在地拉那“米哈爾·杜里”印刷廠陪同中國印刷專家工作時(shí),她正好在“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為出版書籍的事情,常跑印刷廠,這樣,我們就有了經(jīng)常見面的機(jī)會(huì)。每次見面,她都宛如一個(gè)老大姐一般,問我工作中有何困難,是否需要幫助。有一次,她還笑盈盈地把由她擔(dān)任責(zé)編并寫了序言的法特米爾·加塔的新版長篇《沼澤地》送給我,囑告我最好多讀一些加塔的小說,因?yàn)樗恼Z言是很規(guī)范化的文學(xué)語言,多閱讀這樣的文學(xué)作品,對外國學(xué)生學(xué)習(xí)外語非常有利。至于她請我到印刷廠餐飲店喝咖啡和茶,吃小點(diǎn)心,那更是常有的事兒。
坐在我面前,與我促膝交談的阿爾奔,已不再是當(dāng)年那個(gè)13歲的喜歡蹦蹦跳跳的少年,而是一個(gè)穩(wěn)重健談的大學(xué)者了。他那洪亮的聲音,臉上不時(shí)露出慈祥的微笑的表情,讓我產(chǎn)生一種幻覺,仿佛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阿爾奔,而是雅科夫老師。見我心情有些激動(dòng)、難過,成熟的阿爾奔馬上把話題轉(zhuǎn)到他弟弟身上:“您還記得我弟弟阿格隆嗎?”我立刻回答:“那還用說!當(dāng)年他還陪我看過電影,那也是您爸爸的安排,他說小孩子是學(xué)外語的人的最佳教員。阿格隆現(xiàn)在怎么樣?”阿爾奔說:“他比我強(qiáng),不僅是個(gè)很有成就的藝術(shù)家,當(dāng)過歌劇芭蕾舞劇院院長,而且還是個(gè)稍有名氣的作家、詩人。現(xiàn)在已不再當(dāng)劇院領(lǐng)導(dǎo),而專心致志搞藝術(shù)。”我見他言談中稍有點(diǎn)自慚形穢的意味,便自然地插話:“聽說您也寫小說,有部中篇叫《當(dāng)嫁的姑娘》,不要說在阿爾巴尼亞,連在科索沃都很受讀者歡迎。”“哪里呦,提不得,那只是一篇青年時(shí)代的練筆作。”阿爾奔有點(diǎn)不好意思。
時(shí)間已近11時(shí)30分,按計(jì)劃我還要去拜會(huì)文學(xué)評論家約爾高·布遼和作家協(xié)會(huì)的同志,所以只好告辭了。可是,阿爾奔堅(jiān)持非親自送我去不可,我只好客隨主便,跟著他一起下了樓,徑直向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走去。
根據(jù)阿爾奔與我的約定,第二天我又準(zhǔn)時(shí)地到了他的辦公室,從他 手上接過由他負(fù)責(zé)修訂印行的第12版的《死河》,他囑咐我:將來翻譯這部小說,就要根據(jù)這個(gè)版本譯,我向他做出保證:不把這部作品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我死不瞑目。7月14日,我在“五·一”花園中國餐廳設(shè)晚宴款待阿爾巴尼亞文友,阿爾奔自然是被邀請者。晚宴結(jié)束臨別之前,我對他提出請求:“相信不久我還會(huì)來阿爾巴尼亞,屆時(shí)我要買上一束最鮮艷的香馥馥的玫瑰花,請您陪著我,到文化名人陵園憑吊我的恩師雅科夫和師母杜拉塔。”高大魁梧的阿爾奔的眼睛里立刻涌出幾顆淚珠,與我緊緊地?fù)肀Я?分鐘,才戀戀不舍地走出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