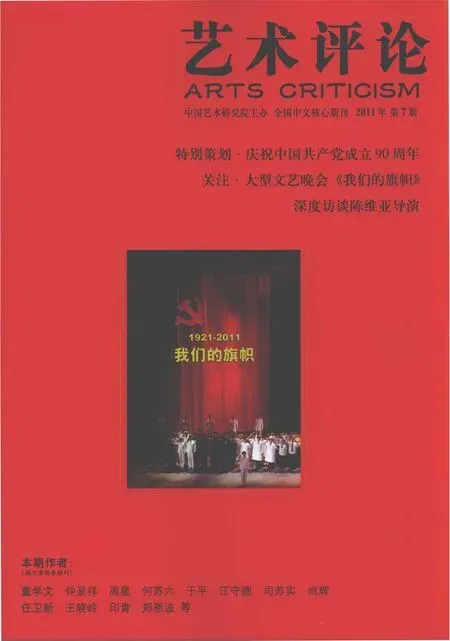開放與多元之中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
尚 輝
新時期由“解放思想”而開始的對于“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反思,糾正也拓寬了人們對于現實主義內涵的理解,人們逐漸從單一的寫實繪畫開始了藝術本體規律的某種自覺;關注“形式”在視覺藝術中的主導地位,關注個性生存、主體精神對于現實世界的獨立和超越,也都成為新時期更大范圍、更為深刻的思想解放主題。很顯然,新時期美術正是在這種思想解放運動中破除了“極左”時期主題先行的創作戒律,有關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既注重還原歷史情境的真實性,也注重發掘和表現歷史主題的人性精神。這種對于歷史主題審美內涵的表達,甚至和五六十年代高揚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精神的歷史展現也拉開了距離。隨著門戶開放,西方現代和后現代藝術潮水般地涌入,中國美術在借鑒西方現當代藝術和回歸本土藝術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多樣與多元的藝術生態。雖然,歷史與現實主題的美術創作只是中國當代美術整體的組成部分,但這種作為國家倡導的主流美術在建構中國美術的主體精神上卻發揮了引領與主導作用。
一、新時期之初關于主題性創作的理解與泛化
從“傷痕文學”而開啟的新時期美術,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主題性”創作進行了深刻反思。
1980年《美術》第7期發表了奇棘撰寫的《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美術創作中的一些問題》,作者指出:“什么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看來似乎簡單,但實際上,多年來我們一面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我們美術的創作方法,另一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在我們的美術實踐中卻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理解,也沒有被很好地思索過。經常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需要,反映現實政治的全部內容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根本內容。藝術變成了政治的寄生蟲。”這篇文章不僅大膽地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質疑,而且認為“理想主義”失去了“反映生活的廣闊可能性”。在同期《美術》上,胡德智在《任何一條通往真理的途徑都不應該忽視——只有現實主義精神才是永恒的》一文中,則把“現實主義流派”和“現實主義精神”區別開來。他認為“現實主義作為流派無非是和浪漫主義、印象主義一樣,是藝術發展洪流中的一個過程”,而“現實主義精神不是有了現實主義流派后才生的,也不是現實主義流派所獨占的,歷史上所有藝術流派,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人們當時對世界的認識、思考和表現,都具有現實主義精神”。
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反思,必然涉及對于“極左”時期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追問。高虹、何孔德提出了“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革命歷史畫的創作”問題,他認為“要尊重歷史”,“歷史畫應該忠實歷史的真實”。[1]而關于“主題性創作”,邵大箴則認為繪畫都是有主題的:“‘主題性’這個詞,大概是五十年代從蘇聯美術評論中引進來的。俄文ТeМаΤЦЧ eΚаЯΚаРТЦНа,是指有情節的歷史題材畫、風俗畫等。看來這個詞的含義很模糊,因為繪畫都是有主題的,印象派式的風景畫,一般的即興之作,不能說沒有主題,即使標榜無主題的抽象畫,其實也有主題。”他認為,五六十年代我們美術創作不太注意研究造型藝術的規律和特點,不太注意視覺形象的刻畫和提煉,一味追求在繪畫中表現故事情節。因此,他反對把文學、戲劇的情節觀念移植到繪畫中來,尤其是獨幅畫,忌用說明性、解釋性的細節來表達故事和情節。[2]
高虹、何孔德提出革命歷史畫要“忠實于歷史真實”的觀念和邵大箴強調造型藝術的獨特規律“忌用說明性、解釋性的細節來表現故事和情節”的思想,都影響了新時期以來關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趨勢。一方面是高舉“忠實于歷史真實”的現實主義旗幟,揭露“傷痕”,批判現實;另一方面則是突破寫實再現的局限性,嘗試和探索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各種藝術表達方式。人們當時努力從單一化的“主題性”創作的種種束縛中沖決出來,將“主題性”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表達意念、情感、心緒和印象的美術創作,而試圖去政治化概念、去情節性描繪、去思想內涵的表達與揭示。
二、歷史悲劇的現實宣泄
客觀地看,以革命歷史為主題的美術創作已不是新時期美術發展的主要內容,而且,在新時期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畫家,即使創作革命歷史題材也缺乏前輩那樣的戰爭經歷和體驗,這就使改革開放中的有關戰爭歷史內容的美術作品形成了和戰爭年代、五六十年代不盡相同的創作風貌和審美追求:一是在審美精神上,由原來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轉向了悲情現實主義和平民主義,像現實中的“傷痕”美術一樣,畫家們往往通過戰爭素材尋找中華民族歷史的“傷痕”。因此,這個時期以表現抗日戰爭中日軍“大屠殺”為題材的作品非常之多,而且作品大都通過酷烈的場景描繪,宣泄歷史悲劇的縱深面。它和五六十年代在表現“悲壯”時的只“壯”不“悲”正好相反,是“悲”而不“壯”。就表現人物而言,也由原來的表現“英雄”、塑造“典型”而轉變為對戰爭中普通人的描寫,甚至日軍俘虜的呈現。二是在表現方式上,突破了單一的寫實繪畫的再現模式,將象征主義、立體主義、并置陳列、表現抽象、媒材拼貼等多種現代藝術語言和觀念納入歷史主題的創作中,從而使這一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具有當代藝術的特征和文化含義。三是伴隨著“九·一八”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抗日戰爭紀念館的相繼建立、修整,出現了半景畫、全景畫等紀實性大場面美術作品。這些作品往往根據特定的環境而創作,具有復現真實的歷史空間與場景的作用。
作為“傷痕”美術一部分的《礦工圖》(圖1),是以歷史的“傷痕”抒泄中華民族的悲劇意識。創作者周思聰原計劃以舊社會的礦工史為主線展開畫面,但隨著作者深入吉林遼源礦區,從一些幸存下來的老礦工身上獲得了特別深切的感受,產生了以民族斗爭為主線的新構想。“那個時候,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就是扭曲的,在被壓抑的狀態下,它本身不變就不行。我就想畫那種受壓抑的狀態,壓得透不過氣來那種狀態。”[3]“藝術是人道主義的,要表現人性。”[4]這就是《礦工圖》組畫的思想基調和悲劇性的審美追求,在畫面那些極為壓抑、沉重、痛苦、令人悸動的形象中包含著整個民族在經歷各種壓迫、摧殘的社會變動中的復雜心理體驗,遠遠超出了礦工題材自身,它所控訴的,也不只是滅絕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也包括一切世間的殘暴與不義。該作品的造型雖以寫實為支點,卻大膽加入了變形。而結構上的最大特征是引入分割與拼貼,利用形象的重疊錯位,突破瞬間情節,造成不同時空的并置、擠壓和支離破碎的效果。

圖1 《礦工圖》之一
直接表現南京大屠殺較為突出的作品有陳鈺銘《歷史的定格》、李自健《1937·南京大屠殺》和馮法祀、申勝秋《南京大屠殺》等。《歷史的定格》是一幅高1.9米、長15.7米的長卷,作品以鏡頭不斷橫向推移的方式,展開了那個慘痛的悲劇性的歷史畫面。大段、大片撕成塊狀的水墨紙片,隔斷了橫尸遍野、殘肢曝地的人間地獄,仿佛殷紅的鮮血已褪盡歷史的色澤,只剩下那黑白的墨漬水跡。李自健的《1937·南京大屠殺》,則凸現了在長江岸畔被屠戮的中國百姓尸骨成山、血流如河的慘烈,像戈雅的《槍殺》和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島的屠殺》那樣,作品以土紅、深紅和黑色、藍黑構成凝重的色調,那痙攣的軀體、掙扎的雙手和死不瞑目的眼睛,都是那30萬遇難同胞的亡靈和怨魂。馮法祀、申勝秋的油畫《南京大屠殺》,雖然每組人物軀體是寫實的,但整幅作品卻是超現實的時空組合,作品將大屠殺現場的不同場景重新構織一起,仿佛是夢魘將民族傷痕的影像重疊在一起。

表現民族的悲劇幾乎是這個時期描繪歷史主題的一種傾向。除了出現相當多的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作品之外,胡悌麟和賈非的《楊靖宇將軍》則從另一個場景、另一個角度傾訴了悲壯情懷。畫面描繪了楊靖宇將軍被槍殺之后,尸體在雪撬上拖行的情景。這里沒有反抗,只有押運日軍踩雪的腳步聲和牽牛老農面部的木然表情。這種沉默固然也有一種力量,但更多凝固的還是一種歷史的悲壯。這幅作品用一種平淡、平靜的畫面所描寫的勇士之死,反而讓人們追想他那被害之前的壯懷激烈與英勇抗爭。其實,槍殺尸骨,大多慘不忍睹。作者就是要以這種悲傷、悲慘宣泄民族抗爭的某種悲劇的大劫痛。
對民族悲劇的凸現,實是在當時中國社會現實中對歷史的反思。這種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挾裹了當時的人性主義立場,于是通過被俘日軍懺悔的描繪,也成為其時表現歷史題材創作的一個視角。王盛烈的《秋雨》(圖2)把日軍投降后的撤離,作為畫面的主題。這是抗戰作品中,第一次直接描繪日軍形象的作品。該作品用“落葉知秋”的中國文化語義,把投降撤離的日軍置于蕭索的秋雨中,顯然是從侵略者的角度對戰爭的反思。那些在雨中行走的日軍,無不縮首萎靡,有傷殘疲憊,有歸心似箭,更有懺悔反思。該作已超越了對抗戰一般性的描繪,既不是寫英雄主義,也不是表現悲劇意識,而是從人性的角度、從歷史的空間融入更多有關戰爭的思考。同樣表現日軍人性證明的,是李抱一的《月是故鄉明》。作品以中國畫的素墨描繪了月光之下,被俘日軍由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而開始的人性覺醒,抒情性的主題和寧靜的月色反襯出戰爭的殘酷和被俘日軍渴望和平的心理。路璋的油畫《發亮的眼睛》用三分之二的畫面,描繪了一群投降日軍的背影,畫面只在左上角的遠處安排了一個領著孩子的父親的形象,“發亮的眼睛”是那個孩子在黑暗處發出的目光。這個孩子的目光既是對投降日軍人性的閱讀,也是對未來的歷史審視。這些作品都試圖從當代人文的視角,重新認識歷史。
三、選擇和塑造平民視角中的領袖、英雄和將士

圖3 《將軍與孤女》
從“傷痕”美術的寫真實,而引發畫歷史之真實,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終于被復歸到生活中平凡人的視線。新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極少像過去那樣表現英雄和領袖。像沈嘉蔚的《紅星照耀中國》則把領袖安排到大眾群像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位置、神態,都顯示了當代人把領袖和英雄視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審美心態。王吉松的《將軍與孤女》(圖3)沒有僅僅塑造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的聶榮臻元帥形象,而是通過這位驍將親手轉送一個在戰爭中離散父母的日本孤女故事的側面描寫,一方面刻畫了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和藹可親的形象,另一方面表現了中國人民對于無辜的日本兒童的友愛。蓋茂森的《戈馬江南》甚至描寫了陳毅在抗日根據地,與割草嬉戲的一群孩子談笑風生的場景。這個場景,和陳毅此刻率新四軍創建根據地的嚴峻形勢,構成了強烈的反差。作品從孩子的視角,表現了儒雅的將軍所特有的親切隨和。像杜鍵、高亞光、蘇高禮的《太行山上》,在塑造領袖將軍的同時,也把普通戰士、民兵和百姓放在更顯眼的位置,這些人物穿插在太行山脈里,共同進入了歷史的時空。
通過平凡的細節反襯宏偉而悲壯的歷史,構成了新時期主題性創作的一大審美特征,而這些平凡的細節多以女性的視角展現。王有政的《烽火歲月》,以八路軍女戰士手把手教兒童識字的日常生活鏡頭,反而凸現了那是一個極不平常的烽火歲月。李戰云的《艷陽天》擷取了八路軍女戰士和鄉嫂村姑在草灘溪畔納底做鞋的平凡場景,祥和而抒情的色調洋溢在后方支前的繁忙中,這是戰爭與和平的協奏。毛岱宗的《紅嫂》(圖4)是根據抗戰時期,沂河邊一位年輕的母親用自己奶水救活傷員的故事所繪。根據同一故事,還有李晨創作的素描連環畫。油畫《紅嫂》以解開衣襟的紅嫂形象為畫面主體,她和橫躺著的戰士剛好構成了畫面十字構圖。該作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增添了抗戰主題的人文主義色彩。而一直引起爭議、獲七屆全國美展金獎的邢慶仁《玫瑰色回憶》,是以當代人文觀念消解英雄主義的代表。那在延河邊上被賦予書卷氣的女戰士形象,的確已遠離戰火紛飛的年代,作品表達的主題也非常模糊含蓄。但它傳遞給我們一個信息,就是用日常生活的平淡來代替“典型”和“理想”,用日常狀態的質樸來代替“崇高”和“夢幻”。
四、歷史題材創作的現代藝術觀念與語言探索
新時期有關革命歷史主題的創作,大都突破了寫實主義繪畫的單一模式。上述許多作品的思想表達,也都借助于一些現代藝術的觀念和語言才得以實現。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現代藝術觀念與語言的運用,才開拓了主題內容的表現深度。王迎春、楊力舟的《太行鐵壁》,已不是敘述具體的事件,或尋找文學情節的某一瞬間,而是直觀地將抗戰中的歷史人物、普通將士、敵后民兵和太行山堅如鋼鐵的巖壁整合一體。它在當時既獲得了繪畫語言形式上的突破,也因象征手法的運用而深化了“太行鐵壁”的寓意。這兩位在黃河兩岸長大的畫家,受“黃河大合唱”的啟迪,此后在不斷涉渡黃河中逐步醞釀創作了《黃河組畫》。像“黃河大合唱”那激越雄渾的旋律,《黃河組畫》雖沒有直接描繪抗戰,卻用象征性的手法通過黃河和與風浪搏擊的船夫,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與魂魄。畫面以蒼勁厚重的線條為骨,結合潑墨渲染,構成黑白灰的大塊對比,略帶夸張的造型增強了表現船夫英勇頑強、團結奮爭的力度。王緒陽的《中流砥柱》,也是把黃河作為作品表達“中流砥柱”寓意的象征載體,黃河激流的奔騰氣勢恰好烘托出船中將士搏擊浪潮、巋然不動所確立的整個民族氣節。作品雖然以寫實為主,特別是嚴謹的人物造型與豪放揮寫的浪潮形成了對比,但由于象征性的立意而使作品具有宏闊的歷史意象。

圖4 《紅嫂》
上述諸多作品,都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形象的象征性。它不僅賦予了畫面固有形象以更多的內涵以深化主題,而且這些象征物也往往成為形式語言的要素。馮遠的《星火》本身就有以火把的“星星之火”寓含“可以燎原”的深義,而這戰士手中的“火把”也構成了畫面富有節奏的形式語言,它起到的不僅僅是好看,更由此使有限的尺寸獲得了視覺及內涵的無限張力。這是敘事性寫實繪畫難以表現和表達的、已超出形象載體內容的深刻寓意。尚輝的絲網版畫《誕辰的音符》,既用階梯構成了仿佛奏起雄壯的凱旋之樂的五線譜似的畫面主體形象,也讓和平年代的人通過攀登階梯而產生一種崇高感的心理體驗。畫面將戰士沖鋒陷陣、前赴后繼的悲壯場面與今天和平年代的階梯自然組接在一起,構成紅與黑、血與火、戰爭與和平的時空交錯,從而形象地揭示了戰士用生命燭照今天的和平與光明的寓意。這幅作品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完全用燭光與陽光象征主題的表達。
相對于上述具有濃郁的個人人文主義傾向和極端個性化藝術語言的作品,紀實性的戰爭美術創作則理性客觀得多。這些作品往往因博物館特定空間的要求而強化逼真感的還原性。這就要求畫家花更大的氣力去考證當時形象的細節,力求符合歷史的原貌。這里,除了要求畫家具備較強的形象塑造能力,還要求畫家能夠營構歷史氣氛,并在這看似紀實的外象背后融入自己對歷史的感悟。姚爾暢應上海歷史博物館約請創作的《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為考證當年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服和裝備,查閱了大量相關文字、圖片和影片等歷史檔案。畫面最終選擇以當時的北火車站為背景,表現十九路軍與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淞滬鐵路沿線展開激烈拉據戰的場面。如果說《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是城市巷戰的一個局部的再現,那么由何孔德、毛文彪、楊克山、崔開璽、高泉、孫向明和尚丁創作的《盧溝橋戰斗》則以宏闊的畫面復現了盧溝橋事變當日敵我雙方鏖戰的現場。這是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創作、也是我國第一幅大型的半景畫,高17米,寬60米,180°弧形,是七位主要畫家歷經兩年、數易其稿完成的,并輔以實物模型和燈光音效等。作品的紀實性要求極嚴,不僅要和近景的實物模型融為一體,而且要觀眾站在現場有良好的透視感,那里面的人物,不論燈光怎樣變幻,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為許多歷史博物館留下永恒瞬間的陳堅,最擅長創作紀實性作品。他歷時5年創作完成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是備受爭議的紀實作品。備受爭議的原因,并不在作品紀實的失實,而在于這個表現當時國民政府受降的巨幅畫面在現行體制里能否被接受。這倒從另一方面,顯示了該作品的紀實力量。畫面中所有的服裝、旗幟、桌椅和道具,均一一考證而得,細微到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和日本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兩人皮靴顏色差異的考據。這里的人物和現場,是可以作為真實的歷史來讀的。但這個紀實的歷史瞬間,并非沒有作者的藝術創造。那低低的視平線,所凸現的建筑基座,不僅夸張了建筑的實際尺寸,而且使場面更加開闊;那巨大的羅馬柱以及厚實的基座,仿佛是歷史的石碑,加重了歷史瞬間的沉重感。在紀實與藝術創造上,這件作品都是一個典范。[5]
五、歷史主題對于當代人文精神的呈現
從新時期始至20世紀末,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以“傷痕”引發的寫真實而轉向民族悲劇的凸現,由此改變并形成了此期歷史主題美術作品的凝重色調。它把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轉變為人性的溫情,由此關注戰爭中普通人的生命體驗,從而挖掘出戰爭中人性的覺醒和呼喚。這種對于人性精神的表現也延伸到新世紀歷史題材的呈現上,只不過這種呈現更帶有當下消費主義的審美視角。
2004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文化部和國家財政部共同立項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開始組織實施。這一國家美術創作工程是新中國以來規模最大、投資最多的歷史主題美術創作工程,前后歷經5年時間,耗資億元,由上百位經過嚴格評審篩選而出的當代優秀美術家共同參與完成。工程的立項,旨在探索新時期國家對于體現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承載國家文化利益的歷史主題的美術創作模式。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美術作品,無疑呈現了當下的人文思想與文化特征。這個特征首先表現在對于歷史真實的理解與尊重上。比如,重大歷史題材最難以展現歷史反面人物。是客觀地描繪還是丑化?這最能體現一個時代對于歷史的態度與人文思想的深刻性。鄭藝的《歷史的審判》就沒有回避對于“四人幫”人物形象的刻畫,更沒有帶著時代有色眼鏡去丑化,而是真實地描寫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在接受人民審判時自然流露出的神情,刻畫了他們一貫具有的張揚跋扈、驕奢淫逸。畫家并沒有因他們是歷史反面人物而放松對于他們的個性塑造,而是對其在審判席上的個性心理進行了深入細微的剖析與刻畫。也正是出自對于他們真實個性與心理的揭示,畫家才將他們本是背對公眾席(畫面)的現場改成正對公眾的形象。或許,“四人幫”人物形象刻畫的真實生動,才是這幅作品獲得成功的關鍵。同樣是表現歷史的反面人物,蔣介石的形象很少正面出現在以往國內的美術作品中。梁明城的雕塑《1945·重慶談判》,不僅正面塑造了蔣介石的全身塑像,而且尺寸、比例都放到了和毛澤東塑像等同并肩的位置。這件雕塑雖取材于重慶談判毛蔣合影的歷史照片,但將這樣兩個歷史人物等同放到一起的美術作品并不多見。這一方面表明今天藝術創作對于國共合作歷史中國民黨在抗戰中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的尊重,另一方面對于蔣介石形象的正面塑造,也只有在今天海峽兩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現實背景下,才能讓藝術家這樣真實客觀地處理。
如何看待戰爭,如何發掘戰爭中人性的存在,是新時期以來進行歷史畫創作表達時代人文思想的重要命題。和上世紀80年代眾多以表現女性在那場奢殺中慘遭奸淫暴尸的描繪不同,由許江、孫景剛、崔小冬、鄔大勇創作的《1937.12.南京》(圖5)不僅僅在于描繪橫尸遍野的慘烈場面,而且通過一位被屠殺的母親對于幼兒在臨死之前表現出來的那種人性的愛撫和掙扎,塑造了被屠殺同胞中的英勇不屈的形象以及母親對于孩子的守護。這些形象的刻畫,無疑具有人性象征的表現,它比單純地描寫女性裸尸的橫陳更具有人性反思的深度。如果從人性表現的角度,鄭藝的《歷史的審判》同樣具有探索性。在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里,關于“四人幫”的形象是漫畫化的形象記憶。因為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后“文革”時期,美術作品中的“四人幫”形象都被類型化了。而鄭藝的《歷史的審判》不僅還原了他們每個人的真實形象,而且刻畫了他們作為政治家在接受審判時的倔強與孤傲。這很符合他們每個人本來的政治信念與個性特征,而不是簡單的低頭認罪。這里揭示的個性,既有他們人性真實的一面,也有在審判席那樣一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所形成的人性扭曲與故弄玄虛。在人性的表達上,特別是在表現戰爭題材上,“工程”中有關戰士形象的刻畫,往往強調戰場中戰士體態的真實感。像孫浩的《平型關大捷》,秦文清的《挺進大別山·過黃泛區》,宋惠民等創作的《遼沈戰役·攻克錦州》,孫立新、白展望、竇紅的《平津戰役·會師金湯橋》,王希奇的《長征》等作品,都追求表現那些在戰場上沖鋒陷陣的戰士在沖殺、射擊、投彈、中彈時運動中的體態真實性,面對生與死的生命生理機能自然爆發出的生命感是我們平時難以模擬的。這種對于戰士自然生理體征的深度把握,也增強了戰爭場面描寫的生動感。這和當下影視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戰爭題材的真實性追求是緊密相連的。

圖5 《1937.12.南京》
當然,“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所體現出的當代人文特征,更多的體現在表現方法上。具象寫實無疑是“工程”作品的主要表現方法。比如靳尚誼的《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丁一林的《科學的春天》,楊參軍的《戊戌六君子祭》,王少倫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劉大為、苗再新的《井岡山會師》,趙建成的《國共合作——1924·廣州》,張國琳、王仁華、桑建國等的《生死印》,李象群的雕塑《毛澤東在延安》和陳科的雕塑《詹天佑修京張鐵路》等。這些作品在寫實語言的表現深度與表現技巧上,都代表了當代美術創作的最高成就,它們無疑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更具有寫實的力度與厚度。但同時,“工程”的作品又不局限于具象寫實,而是從具象寫實開拓出來,并融進了很多現代主義與當代藝術的創作成果,豐富與發展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
許江等人創作的《1937.12.南京》、井士劍等人創作的《阿里山的抗日斗爭》在人物塑造與環境渲染上,既有象征的成分也有表現的成分。陳樹東、李翔的《百萬雄師過大江》和曹立偉、施樂群的《唐山大地震》,幾乎完全用的是表現主義的創作理念,并結合了綜合材料的運用。施大畏、施曉頡的《永生——1941年1月14日皖南》采用象征與立體構成等多種藝術觀念,強化了畫面的悲劇意識與歷史內涵。陳妍音的《反內戰的吶喊》則消解了傳統雕塑的紀念性,而把平面性的圖像語言轉換為三維的雕塑語言,從而賦予傳統雕塑以當代性的意味。
當然,就當代人文視角的審美特征而言,我們還可以和以往的一些經典作品進行比較。比如,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和唐勇力的《開國大典》。雖然唐勇力的《開國大典》很難在寫實深度、厚重感和社會影響上超越已經成為20世紀美術經典的董希文的《開國大典》,但唐勇力的《開國大典》更帶有當代人文的審美經驗,它在工筆重彩人物畫的寫實程度、眾多的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整體畫面視覺形式的追求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應該說,唐勇力的這件作品帶有更多的視覺審美特征,是莊嚴而絢麗、厚重而輝煌的歷史畫卷,是從新中國60年這個當下視角對于歷史的想象與創造。
韓書力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創作過《解放西藏》,同樣主題的《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則試圖通過高原祥云來寓意和平解放西藏的歷史意義。如果說《解放西藏》探索的是水墨寫意人物畫的寫實強度與整體畫面的控制能力,整個場面被賦予一種歡樂喜慶的氣氛,那么《高原祥云》則試圖通過祥云的寓意來隱喻和平解放西藏的歷史意義。《高原祥云》沒有用太多的筆墨去描寫和平解放西藏入城的熱烈場面,而是采用了裝飾性的富有藏族傳統紋飾特征的祥云圖樣構成畫面的主體,其間穿插著入城的解放軍將士、藏族男女老少和寺院喇嘛等宗教界首領人物等。相比于《解放西藏》,《高原祥云》的畫面很沉靜,而且沉穆之中散逸出高原藏地特有的那種宗教氣息。作者對于同一主題在創作觀念、表現方法和審美內涵等方面顯現出的變化,都揭示了不同時代人文視角的差異。
楊力舟和王迎春的《太行烽火》也可以和他們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太行鐵壁》進行比較。如果說《太行鐵壁》采用的是象征性的手法和素描造型與寫意筆墨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機的統一,那么,《太行烽火》則是在畫面整體觀念上采用了立體主義的解構性,由此對畫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硬邊分割與空間重組,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則相對弱化了文人寫意筆墨的運用,凸顯了歷史圖像在作品中的效應。顯然,《太行鐵壁》著眼于新時期之初對單一寫實主義的主題性創作的突破,而《太行烽火》則是在這種突破的基礎上強化了畫面自身的結構性語言的探索,并從此把結構性語言和恢宏的歷史深度結合在一起。顯然,中國畫筆墨的圖像化在這里也有效地將歷史影像聯結在一體,從而增強了此作畫面呈現出的歷史感。同一作者、同一主題的不同表達,更深入地揭示了消費時代人文視角與審美視點的變化。[6]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無疑是新世紀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一個新的標志。這個新的標志,就在于在藝術崇尚自我、表現自我與極端個性化的當下,許多美術家仍能潛心創作反映這169年民族復興的歷史主題,并以當代人文關懷的審美視角深入到歷史的空間。這個新的標志,就在于在影像傳媒異常豐富與發達的今天,許多美術家仍然堅守著傳統造型藝術的表現方式,在借鑒與汲取當代藝術觀念與語言的同時積極推進架上藝術的當代性表達。這個新的標志,就在于這種美術創作本身體現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承載了社會主義美術的國家文化利益,并完整地呈現了主流美術的審美追求。
注釋:
[1]高虹、何孔德:《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革命歷史畫的創作》,《美術》1979年第1期。
[2]邵大箴:《更上一層樓——看四川美院畫展有感》,《美術》1984年第6期。
[3]周思聰:《歷史的啟示——關于<礦工圖>的創作構思》,《周思聰紀念文集》,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版。
[4]李兢哲:《周思聰印象記》,《泰安師專校刊》1985年4月15日。
[5]尚輝:《凝重色調——從現場到歷史的不同審美視點》,《永恒的記憶——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京滬美術聯展作品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
[6]尚輝:《當代人文視角中的歷史畫卷》,《美術觀察》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