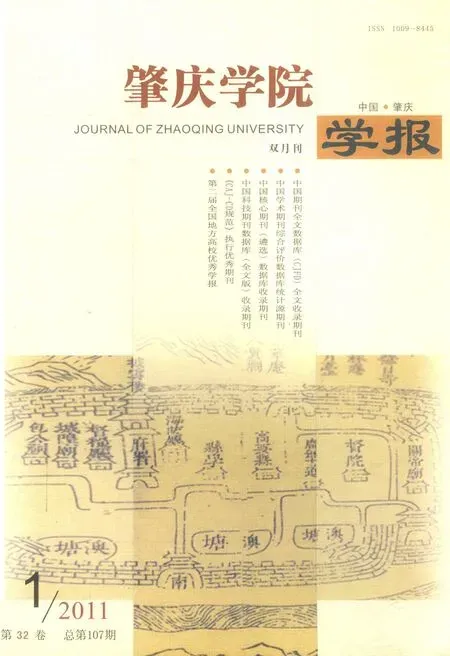安部公房短篇小說《紅色的蠶繭》探析
孫 苗
(四川外語學(xué)院 研究生部,重慶 400031)
安部公房短篇小說《紅色的蠶繭》探析
孫 苗
(四川外語學(xué)院 研究生部,重慶 400031)
日本戰(zhàn)后文學(xué)派的代表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說《紅色的蠶繭》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異化現(xiàn)象,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這種病態(tài)、畸形的社會現(xiàn)狀。小說中的幾個主要象征性事物:“無‘家’可歸的‘我’”、“女人的‘笑’臉”、“手持棍棒的‘他’”、“紅色的蠶繭”及“發(fā)現(xiàn)蠶繭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影射了戰(zhàn)后的日本人對日本前途的迷茫、悲觀絕望、孤獨無助的普遍心理狀態(tài)及人與人之間的虛偽和冷漠,影射了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種種不合理制度使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及精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使人民處于更加悲慘的境地。
安部公房;紅色的蠶繭;戰(zhàn)后文學(xué);自我;孤獨
安部公房是日本戰(zhàn)后文學(xué)的代表作家。在他諸多的作品中,安部公房大膽地借鑒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形式,以象征、寓意、超現(xiàn)實等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及貌似荒誕的表現(xiàn)手法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異化現(xiàn)象,表現(xiàn)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以及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扭曲及畸形,以啟發(fā)人類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引導(dǎo)人類進一步去探索人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意義[1-2]。
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說《紅色的蠶繭》發(fā)表于1950年的《人間》雜志,曾獲得第二屆日本戰(zhàn)后文學(xué)獎,可以說是安部公房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獨特的構(gòu)思,通過“人類變成蠶繭”這樣超現(xiàn)實的“變形”的表現(xiàn)手法,來寓意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異化、人存在的不合理等社會現(xiàn)象。小說通過主人公“我”,影射了戰(zhàn)后的日本人對未來前途的迷茫、悲觀絕望的普遍心理特征,表現(xiàn)了作者內(nèi)心的孤獨、憂慮和無助[3]。
本文將通過對《紅色的蠶繭》中,諸多象征性事物的詳細(xì)分析,來探索小說的創(chuàng)作目的,思索其中的深層含義。
(一)無“家”可歸的“我”
小說開篇,首先登場的,便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主人公——“我”。
“日漸西斜,己是人們匆匆各自回窩兒的時候了”,勞累工作了一天的人們,要回到自己的住所放松、休息,準(zhǔn)備迎接新的一天的到來,這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事情,可是主人公“我”卻找不到自己的房子,無家可歸。
“我在房子與房子之間的縫隙中繼續(xù)慢慢走著。‘街中房屋林立,如此之多,可卻沒有一間屬聆我。這究竟是為什么……’”
很顯然,“我”的疑問也是讀者們的疑問,如此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該存在的“家”,為何會找不到?此時,“我”進一步思考,“說不定是我弄錯了什么。可能不是沒有我的房屋,而只不過是我把它忘卻了。”于是,“我”開始了“尋家”的旅程。可是,“尋家”的過程意外地艱難,“我”四處碰壁,而最終還是未能找到自己的歸宿。總結(jié)來看,主人公“我”的遭遇如下:
無家可歸(不應(yīng)該沒有家→也許只是把家忘卻了)→尋家→未果→無家可歸
那么,小說中這個無論如何也無法尋找到的“家”,到底有何寓意呢?小說《紅色的蠶繭》中的“家”,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人的住所或房子,而是寓意著人們生活在戰(zhàn)后社會中,所必要的自我的地位及歸宿。
20世紀(jì)中后期的日本,還沒有完全走出戰(zhàn)爭的陰影,就急速地進入了高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復(fù)蘇狀態(tài)。此時社會雖然相對穩(wěn)定,但同時也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暴露的時期。這時,許多人對日本的未來感到的是惶恐、迷茫和不知所措……。在急劇變遷和發(fā)展的社會中,他們看不到未來,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他們有的只是悲觀和孤獨。他們也試圖努力地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棲身之處,可卻在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失去了自我,成為精神的流浪者。《紅色的蠶繭》中,無家可歸的“我”,便是這群社會人物的典型[4-5]。
(二)女人的“笑”臉
四處尋家的"我"終于鼓起勇氣敲開了一戶人家的房門,迎接我的,首先是一個女人“和藹的笑臉”。可正當(dāng)我充滿希望,追問“家”的所在的時候,“女人的臉變成了冰冷的墻壁,封死了窗戶。”此時,我才明白,“原來這就是女人笑臉的真實所在。是他人的,便不是我的。”
這里的女人,應(yīng)該可以說,象征著“我”身邊的,而除“我”之外的“他人”。女人的“笑”臉的變化,正影射出了,戰(zhàn)后日本社會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guān)系,表面上的和善、友好,可實際上人人都帶著虛偽的假面。脫掉假面,那面孔就如墻壁一般冰冷,而且將會死死地封住心靈的窗戶。換句話說,溫和、友善的人際關(guān)系背后,隱藏的是厚厚的、看不見的隔閡。
這樣冷漠的人際關(guān)系,的確讓人感到無比悲哀,但是與此同時,生活在這樣的現(xiàn)實中的所有人們,卻又別無他法,只有同樣關(guān)閉心靈之窗,帶上虛假的面具與他人交往。這或許也可以說是現(xiàn)代人保護自我的一種消極方法。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也許自己也會像主人公“我”一樣,失去自我,成為精神的流浪者,甚至無家可歸。
(三)手持棍棒的“他”
當(dāng)我意識到所有的一切都不屬于自己,所有的“家”都是他人的時候,我便放棄“尋家”的念頭,而轉(zhuǎn)寄希望于公園的長椅了。可是,事情還是沒有“我”想象的那么順利。手持棍棒的“他”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并將我驅(qū)趕出了公園。理由是“這是大家的地方,不是任何人的地方。”
“我”所期望棲身的公園,寓意戰(zhàn)后社會上各種名義上服務(wù)于民眾的設(shè)施、制度等等。表面上,這些都是為了民眾們而建設(shè)和實施的,可實際上,人們卻無法從中得到保障,反而更加不安和惶恐。而手持棍棒的“他”便是這些設(shè)施以及制度等的維護者。他們看似是在莊嚴(yán)地維護著社會的秩序,但實際卻使人與人之間更加冰冷,更加缺少信任。而那些所謂的設(shè)施、制度,其實也只是形同虛設(shè),沒有任何意義。
(四)紅色的蠶繭
“尋家”未果,失去了所有落腳之處的“我”,仍然在繼續(xù)走著。而接下來,“我”的身體發(fā)生了變化。最后,當(dāng)“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的身體已經(jīng)“只剩下一個空空的蠶繭”。
“啊,這下子我終于可以休息了。夕陽染紅了蠶繭。這毫無疑問就是我的房屋,不會受到任何人干涉的房屋。但是,房子雖有了,可是卻沒有了能夠歸家的‘我’”。就這樣,“我徹底消失了”,變成了空殼,徹底失去了自我。
安部公房用這樣獨特、另類的表現(xiàn)手法,將一個異化的、扭曲的社會,生動形象地展示在了讀者的面前。“紅色的蠶繭”象征著各種各樣無形且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和制度。它們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與個性,使人們無法展現(xiàn)自我的價值,最后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內(nèi)涵,變成虛無的空殼。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蠶繭中的時間。
“時間在蠶繭內(nèi)停止了它行走的腳步。外面雖已黑暗一片,但蠶繭中卻總是黃昏。從里面照射出的晚霞,染紅了它,使它放著光。”
如果“紅色的蠶繭”象征著各種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那么蠶繭中停滯不前的時間,便可以說象征著這種社會規(guī)則的未來。它停滯在封閉的蠶繭當(dāng)中,再無發(fā)展。而且時間靜止在黃昏時分,即使它再垂死掙扎,也只會迎來黑暗的夜晚,最后走向終結(jié)。
安部公房借“紅色的蠶繭”中的時間,來指引人們?nèi)ニ妓鳎瑧?yīng)該拋棄陳舊的、束縛人們心靈的社會規(guī)則,更應(yīng)該去開拓新的未來,共同走出這孤獨、冷漠的社會。
(五)發(fā)現(xiàn)蠶繭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
變成蠶繭的我,放著紅光,而“他在大車的道口與軌道間發(fā)現(xiàn)了已變成蠶繭的我。開始,他非常生氣。不過,他轉(zhuǎn)念一想,馬上覺得拾到的是個稀罕物,便放入了衣袋里。我在他的口袋里翻滾了一陣,便落入了他兒子的玩具箱里。”
此處,如果蠶繭象征著各種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那么,發(fā)現(xiàn)蠶繭的“他”,便寓意著可以改變現(xiàn)狀的賢士們。他們不但已經(jīng)意識到了社會現(xiàn)實中不合理性的存在,而且果斷地將其拋棄了。
變成蠶繭的“我”翻滾后落入了“孩子的玩具箱”。這“玩具箱”里的物品,沒有任何價值,只由孩子任意玩弄,而大人則將其視為廢物。“孩子的玩具箱”即是“蠶繭”的最終去向,同時,也暗示著這扭曲的社會制度與規(guī)則的去向,即最終會被人遺棄,走向滅亡。
從以上這些象征性事物各自的寓意中不難看出,作者安部公房,通過“人變成繭”,這樣一種超現(xiàn)實的寫作手法,生動地展現(xiàn)出了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現(xiàn)狀和人們的生活以及精神狀態(tài)。
安部公房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是現(xiàn)代社會中的孤獨形象,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不為人知的小人物,他們對社會現(xiàn)狀存有極大地不滿情緒,卻又無法與他人溝通和交流。生活環(huán)境的惡劣和精神上的苦悶,使他們陷入極其無助的境地,他們感到社會已經(jīng)拋棄了他們。《紅色的蠶繭》中,無論是“蠶繭”還是“墻壁”等都象征著這樣一個使人民感到無比痛苦和沒有希望的不合理的社會。
但是,在小說的最后,安部公房還是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的存在。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變成蠶繭的“我”、并將我扔進“他孩子的玩具箱”的“他”,使我們的眼前一亮,也許他就是未來的創(chuàng)造者。這樣的賢士的出現(xiàn),就如同沙漠中的人發(fā)現(xiàn)了狹小的綠洲,雖然看似微不足道,但無疑是人們繼續(xù)生存的一道曙光[6]。
[1] 葉渭渠.安部公房與日本存在主義[J].外國文學(xué),1996(3):3-7.
[2] 孫樹林.論日本戰(zhàn)后派文學(xué)(一)[J].日語知識,2000(1):29-30.
[3] 藍泰凱.安部公房及其創(chuàng)作簡論[J].金筑大學(xué)學(xué)報,1999,36(4):59-63.
[4] 竺家榮.評安部公房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寓意表現(xiàn)[J].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學(xué)報,1999(2):34-37.
[5] 劉炳范.日本戰(zhàn)后文學(xué)轉(zhuǎn)換的代表[J].日本研究,1999(2):64-70.
[6] 莊蘋安.安部公房小說藝術(shù)特色初探[J].龍巖學(xué)院學(xué)報,2007,25(5):62-64.
An Analysis of Abe Kobo’s Short Story Red Silkworm Cocoon
SUN Miao
(Graduate College,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Sichuan,400031,China)
Abe Kobo,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Japanese post-war writers exposes the alie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 irrational and morbid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n his Red Silkworm Cocoon.The major symbolic figures in the story,the “homeless I”,the “l(fā)ady’s smiling face”,the“he holding a Rod”,the “red silkworm cocoon”,the “he who found the Red Silkworm Cocoon and his children’s toy box”symbolize the Japanese people’s bewilderment to the future of Japan after the war,and the desperateness and helplessness,as well as the hypocrisy and indifference among people.All these present the unfair social system which led to inability of protecting spiritual and material lif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be Kobo;Red Silkworm Cocoon;post-war literature;self;loneliness
I106.4
A
1009-8445(2011)01-0016-03
(責(zé)任編輯:禤展圖)
2010-11-23
孫 苗(1985-),女,吉林長春人,四川外語學(xué)院研究生部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