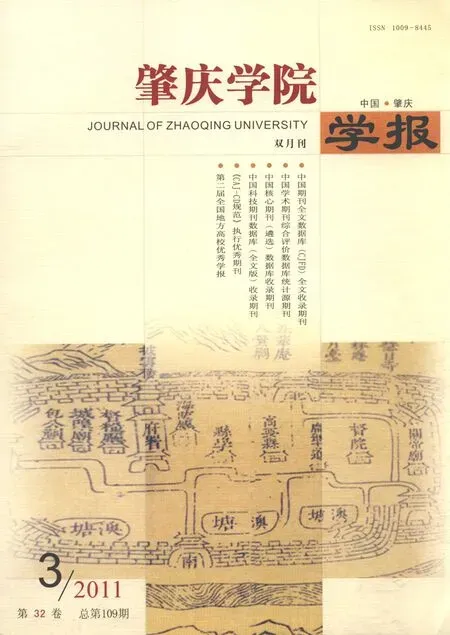“寫”在石濤畫學中的意義
吳勇
(肇慶學院音樂學院,廣東肇慶526061)
“寫”在石濤畫學中的意義
吳勇
(肇慶學院音樂學院,廣東肇慶526061)
“寫”作為對中國畫作畫狀態的特殊表達形式,尤其是在中國畫中“寫意畫”的廣泛運用,使得它在中國畫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自宋元以后由于這個直抒胸臆的“寫”字使得畫風大變,并且在之后的中國畫發展中也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石濤所建立的“一畫”系統也不例外,他把“寫”作為支撐其畫學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所使用的“寫”與古代畫學中的描述與運用,雖然在大體上一致,但是進一步分析就能看出,他不僅繼承了古代畫學中對“寫”的運用,并且把“寫”作為對當下的一種“創造”精神體現,運用到他的畫論、畫跋和當下的作畫狀態中。所以,石濤的“寫”不僅是中國寫意精神的高度體現,也是他“創造”思想的集中表現,更是他人格精神的寫照。
中國畫;石濤;“寫”
中國畫歷漢末魏晉的初期發展,至唐宋已經尉為大觀。人物畫自晉朝進入高峰,唐朝而趨于鼎盛,山水畫與花鳥畫在宋朝達到最高峰。而此時中國畫已逐漸由“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繪畫思想走向“畫寫物外形”、“功夫在畫外”。而畫論中“寫”的大量運用,更快的推動了此種變化,特別是“自元代始,文人畫家開始不拘于物象的形似,開始講求筆墨相對獨立的作用,開始講求區別于描頭畫腳的畫法,而主張一個直抒胸臆的‘寫’字,畫風于是大變。”[1]18可見,“寫”在中國畫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何等重要。而在對“寫”的歷史考察過程中我們發現,石濤有太多的理由被作為一個重要對象對其進行研究。
一、“寫”的本意闡釋
要深刻透徹的理解“寫”在石濤畫學中的意義,我們首先要明白兩方面:其一,“寫”的本義是什么?其二,石濤畫學的基本涵義。而明白這個字的本義,只好求助于古籍訓詁之學。“寫”即傾注,“寫”為本字,其后加水旁為“瀉”,其實為一個意思。既然是傾注,那么就有“盡”義,有由此器移彼器“傳移”之義;涉及內心與言詞,即有“表達”“表現”之義。到此,可知“寫”乃一個“關系詞”,其所要表達的是“雙方”、“兩重”、“表里”、“彼此”之間的微妙聯絡、交流、融會、貫通的意思。而《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此文下之《疏》云:“寫”,謂倒傳之意也。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倒”,是由此器倒在彼器,即為“傳”之意。《辭源》注為“以此注彼”,簡潔明了。正如詩圣杜少陵詠櫻桃“數回細寫愁仍破”就是很好的例子。寫,古又有“傾也”、“盡也”、“除也”等義,則都是“移置”的衍變義、引申義。既然是傾注,必然把它倒干凈了,所以為“盡”為“除”。轉而涉及情緒感思,則“寫”即為“抒發”義,如《詩經》里的“以寫我憂”、“我心寫兮”,都是佳例。這就可以悟出:立言作文,抒發內心,亦曰“寫”者,正因為那也是一種由此內心傾入彼言彼文之中,也是一種“移置”明矣[2],畫論中“寫”的基本含義即是指此。
由以上的解釋可知,“寫”大致有:“傾注,盡除”,“表達、表現”、“傳移、由此注彼”、“抒發”之意,根據這些詞意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主觀與客觀兩個層面。也就是說,“傾注,盡除”,“傳移、由此注彼”是作為對物本身而言,“表達、表現”、“抒發”是作為對個人主觀心里的描述。而對于中國畫而言,“寫”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它是否隨著歷史的演進越發強調了它的主觀性呢?宋元之前即有“傳神寫照”“傳移模寫”等中國畫中之精髓詞匯出現,并且成為當時和此后品評繪畫的重要標準。但此時“寫”的主觀心理作用沒有被突顯出來。并不是說古典期的畫家在創作時就沒有主觀心理的作用,而是當時畫家的主觀心理是服從于社會需求的,所謂“任何個人都是社會關系總和的一分子”,也就是畫家的主觀心理服從于社會需求而沒有被突顯。而宋元之后,“畫家的主觀心理則是逸出了社會需求之外的,他們的意識是要擺脫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以自我為中心”[3]。徐建融先生明確指出前后之差異就在個人意識的突顯問題上。而“當生宣紙成為文人畫的載體之后,過程性的講求更變成為隨機性的發揮。筆隨情轉而聚墨成形,因勢利導而偶然天成。于是,文人畫中筆墨的抽象表現功用,進一步主導了造型的夸張與變形,在‘不求形似求生韻’,‘借筆墨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的認識下,‘應物象形’的造型觀也以‘不似似之’的造型觀所取代。”[1]18石濤是這些偉大理論的建立者與實踐者,并把“我”的自覺意識放在高于一切表現方式與借助形式的位置,“我之為我,自有我在”,“我用我法”,皆是強調“我”,是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我”的體現始終是要通過載體來顯現和表達,“借筆墨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在這,“寫”為達到“我”的愉悅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筆墨”是表現形式,“天地萬物”是表現的載體,都是通過“寫”的方式而陶泳于“我”。
二、石濤畫學中“寫”的意義及運用
在石濤《話語錄》中,他11次提到“寫”,如此多次的用“寫”來對畫論進行闡述,可見“寫”在畫論中的重要性,而其意義是否與歷代描述相符呢?他在運用當中是不是客觀與主觀互用或者又發展了它的意義呢?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明確石濤的畫學思想主要為何。因為只有認清了他的畫學思想,我們才能更準確的把握“寫”在其畫學中的意義。
“一畫”是石濤畫學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它被放在第一章以達到統攝全文的作用,而“一法”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對“寫”的一種特殊框定和規范。朱良志先生在闡釋“一畫”的意義時,開篇即說:“石濤所謂‘一畫’乃是畫之一,是繪畫創作的最高法則。”[4]7這里很明確的告訴我們,“一畫”乃是一種法則。接下來他進一步解釋:“石濤所謂‘一畫’是一個不為任何先行法則所羈束的藝術創作原則。世人說的是‘有’或‘無’,他說的‘一’,不是數量上的‘一’,不是一筆一畫,是超越有和無、主觀和客觀、現象與本體等的純粹體驗境界。他的一畫之法,就是為了建立一種無所羈束、從容自由,即悟即真的繪畫大法。”[4]7朱良志先生對“一畫”的解釋仍是一種“繪畫大法”,那么,既然“一畫”是一種大法,便是有法則可依的,而石濤是不是要建立一種可依可尋的路徑準則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立一畫之法,即立我法,但我法非定法。在石濤這里,沒有定:法無定,定無法。一成定法,即為法拘。石濤要立我法,其所立乃玲瓏活絡之悟心也。創造如源泉活水,每一次創造都是內心的靈溪中涌出的一泓新泉,永不重復。他立一畫之法,即立我法。這并不意味樹立一個不同于他法之法。我法即非法,我說法,即非法,是為法。故石濤在強調法無定法的同時,又有另一層意,即法則非法。石濤樹立一畫之法,即破所有之法,而并不是破他法而樹立自己的法。法就是無法,無法即是他的大法。此大法即一畫之法。”[4]12這里明確指出石濤之法就是無法,無法就是他的大法,就是一畫之法,既然石濤辛辛苦苦建立的一畫之法就是無法,那么對于繪畫創作則沒有什么限制,是純然自由的,隨心所欲的。石濤是不是僅就建立這樣一種法則呢?這樣的觀念和藝術創作所要遵循的基本準則是否相符中呢?我們知道,藝術創作必須遵循一定的準則,藝術傳統的力量和藝術家的創造并非絕然對立,每一次創造都可以說是一種創新,但一無例外的是,每一次創新都必須在原有基礎上的創新。法無定法本身必然有法,法無定相也不是絕去法相,如果石濤只為騁一己之快,掀翻天地,無古無今,無物無我,行其所行,縱其所縱,這樣的畫論與小兒狂語無以異。
我們再來看石濤的說法:“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為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5]9。他的意思是說,古往今來的畫家沒有不遵守一定的創作規則的,如果沒有具體的法式,其繪畫也就不可能有具體的形制(限)。所以石濤提倡無法,并非強調“無限”——毫無法則可循;也不是強調有法--完全依據法度去作畫。“創作是優游于法與無法之間,石濤概括的‘不似之似似之’頗能反映他在這方面的斟酌,不為古法所拘,不為外形所限,不為先入的理性所控制,我手寫下當下之我,用他的話說就是‘只在臨時間定’,將一切交給瞬間的感悟,在當下之悟中。凝定意象,這樣雖無法而有法,雖有法而無法。”[4]41
朱先生明確指出,石濤并非是強調作畫毫無限制,也并非強調完全依據法度作畫。他是要優游于法與無法之間“只在臨時間定。”所以才有“信手一揮”這種對當下作畫的描述,“他是要使畫家進入到一片純粹自由的境界,而不是局限于法的束縛。自此大致已明石濤的主要畫學中心意旨即:強調創造,強調繪畫的個性化表達,強調妙悟。”[4]41
既然已明石濤畫學的主要思想,那么“寫”在畫學思想中起到何等作用?意義如何呢?下面我們將從石濤畫論、題畫詩跋和他的畫作3方面,對石濤“寫”的運用進行具體分析。
《一畫章》是石濤統攝全文的重要表述。他在這一章中有:“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5]3朱先生對“信手一揮”的解釋為“對當下作畫狀態的一種描述”,而這“一揮”是要揮何等物象,乃“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這些東西皆是要描述的對象,而這些物象要怎樣“揮”就于畫面。他說;“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前四字意思大致為:選取造型,用其態勢。其后之“揣意、運情”則是一組連續性情感表達。石濤有云:“夫茫茫大蓋之中,只有一法,得一法,則無往而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曰我法,又何法耶?總之,意動則情生,情生則力舉,力舉則發而為制度文章。”[5]3這里明確指出“我法”乃就是意動情生發而為制度文章。也就可以得出意動情生是通過“摹景”來展現,從而體現“我法”。而這里的“摹景”實際就是“寫景”,通過寫景來展現深蘊內涵,石濤所要表達的深蘊內涵就是“一法”,中心就是強調創造,而“寫”是體現“一法”的過程,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創新的過程,所以石濤的“寫”應是“創造”的過程。在下面的各章中將進一步闡釋“寫”應有“創造”之意。
試看《變化章》中寫的運用:“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5]13在此句話中,如果省去中間四句描述則為:“夫畫,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其意思大致可理解為:畫乃是借筆與墨創造出我心中的天地萬物而愉悅于我。這里我們也用“創造”來解釋“寫”,到底合乎其意嗎?我們先來看此章的開篇是如何說的:“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為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也。”[5]13他首先就指出因循守舊、一味崇古的弊端,這種只在古人的圈子里討生活的做法,不但沒有自己,對繪畫也將不會有任何發展。所以他舉例說到:“識拘于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也就是說,學習和繼承古代的知識和文化,目的是為了開拓和創造出今天的知識和文化。例子倒是舉出來了,具體的施行方法又該怎樣呢?:“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于化。”[5]13石濤在這里提到的“法”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它并不是一種固定具體的方法,它的“法”就是一種創造之法,“無法而法,乃為至法。”不為古法所拘,不為先入的理性所控制。即使“凡事有經必有權”,也“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于化。”所以他的“法”不是一層不變的,隨物而得,隨性而起,這就是石濤所要倡導的“方法”,它不是單靠學就能得到的。楊成寅先生在解釋“經”與“權”、“法”與“化”的問題時也說到:“石濤關于‘經’與‘權’、‘法’與‘化’的關系的論述,包含著客觀事物認識過程中的普遍性與個性(特殊性)、穩定性與流動性的辯證關系的深刻思想。他要求人們(包括畫家)既要注意普遍性,又要注意特殊性,既要注意穩定性,又要注意流動性。他更強調的是特殊性和流動性,因為當時許多畫家只注意到繪畫法則的普遍性和穩定性,忽視了藝術上的創新、發展和個性。”[6]166也申述了他所強調的是一種“創造”。接下來石濤就道出了這句名言:“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前面我們在解釋“寫”的本義時說到,“寫”是一個過程,既然是過程,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石濤就肯定加進了他的創作思想,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不用再過多重復,我們只要知道因天地萬物乃都是我心中的天地萬物,他們通過筆墨的個性化表達展現于畫面,一種當下的妙悟,一種當下的創造精神體現。
《皴法章》也運用到“寫”來描述:“筆之于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其開生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卻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峰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5]37在這里運用的“寫”是就具體的皴法而言,而皴并不是山本身所具有,它是人們為了表現山川的面貌賦予的。人們在寫石寫土的時候,只能得到這一隅的皴而已,并非山川自身的狀態。接下來他舉了很多皴法與峰名來說明它們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因為有了這么多皴法,所以局限了人們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創造性,他們都依賴于既有的經驗。其后又云:“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峰皴之見?一畫落紙,眾畫隨之;一理才具,眾理附之。審一畫之來去,達眾理之范圍,山川之形勢得定。”[5]37他是很反對依據既有皴法與當下寫畫的套用,明確指出應以當下的自我感悟去創造,只要畫家熟練地掌握“一畫”論,在創作時就會自由自在。在這句話當中不是提到一個“理”字嗎?其實“理”的本義就是指對象的本質。而在寫畫過程中,對象的本質與畫家的理解、感受原是融在一起的。所以“理”就包括對對象本質的揭示,也是畫家本人的心理表現。而每位畫家的心理感受是不一致的,這種不一致就不應該產生程式化的層層相因。所以,在這一章中所用的“寫”字,其實是一種反證,僅就“畫石畫土”,也就是說,這里的“寫”是一種客觀表述,是反對一些人只知道因襲前人,沒有創見性,是對他們的嘲笑。
再來試看第十章中的描述。這一章兩次運用到“寫”,其一為;“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辟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5]41這一節主要說明經營位置的程式化,表現為三疊兩段式,這種程式化直接導致繪畫沒有生活,毫無生氣。接下來即說明程式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啻印刻?兩段者:景在上,山在下,俗以云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為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才見筆力,即入千峰萬壑,具無俗跡。為此三者入神,則于細碎有失,亦不礙矣。”[5]41在下半節的描述中,明確指出“分疆三疊”已經程式化到沒有遠近感,寫的畫已經似“印刻”一般,古板乏味,絲毫體現不出生活的氣息。既然連生活都無法體現,那還談什么畫家自己的心理感受。畫家的心理感受本是創作繪畫的最好媒介,連這一點都沒有,不知從何談創造。所以以上兩處運用到的“寫”與《皴法章》相類,皆是對沒有創造性的批評。
在《蹊徑章》中,首句即以“寫”開頭;“寫畫有蹊徑六則”,接下來都是具體介紹“寫畫”的蹊徑。既然是蹊徑,那么就有路子可尋,而這些路子是不是一層不變呢?他在描述“對景不對山”時寫道:“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其大致可理解為:山象冬季一樣,卻配以春景。這樣的作畫蹊徑本就是一種創造。因為他把不同季節的自然,通過他的想象與加工,組合到一個畫面當中,這難道不是一種創造過程?這僅僅是他所舉的一個例子,它還可以擴大到夏與秋、秋與冬等的結合,只要符合藝術的基本規律。上面的創造還是具有一定的先驗經驗,因為每個季節都有過感受,而他在論述“險峻”的時候,干脆是:“人跡不能到處,無路可入也。”既然是人不能到,無路可進,那么你怎么描述這種險峻之勢?其實就是想象與創造,因為他沒有依據。從他對寫畫蹊徑的描述看來,對于“寫”的解釋仍不離“創造”之意,因為每個例子所強調的就是創造,如果沒有創造,那么只能是為“古”而非為“我”也。再者,如果“蹊徑”如上面所說是一層不變的,那么這種寫畫蹊徑仍是執于是而拘于法,石濤所要追求的不在于此,即使他舉例說明,他所強調的仍是當下的一種創造,是對“一畫”精神的具體表達。
《林木章》是用“寫”最多的章節,在首句他就舉古人寫樹之法:“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5]49這句話其實贊揚了古人在畫樹過程中所用的方法,他們的方法雖各自面目,卻非我的面目。所以石濤不僅就滿足于此,接下來便是對“我”寫樹方法的描述。他說:“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如英雄起舞,俯仰蹲立,蹁躚排宕。或軟或硬,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5]49這里強調的是“我寫”,既然是“我寫”,那么強調的就是我獨特的面貌,獨特面貌從何而來,乃是我通過當下進入對象后所感受和體會到的,通過這個過程而后我所進行的創造,只有屬于我自己的才是獨特的。接下來即是具體的方法。那么“寫石之法”又是什么法呢?石濤畫論中沒有明確指出。我們先不論“寫石之法”到底是什么法,但我們知道,石濤“法”的概念是貫穿整個畫論中的,而石濤之法就是無法,無法即是他的大法。此大法即一畫之法。而一畫的中心就是強調創造,所以“寫石之法”其實就是一種創造之法,而創造之法可寫乎?石濤并不拘于此,拘于此又是拘于法,拘于法何談創造,創造就是無法,就是“一畫”。
畫語錄最末一次提到“寫”是在《四時章》中,在此章的敘述當中,一開始就表明,寫四時之景要審時度候為之,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根據不同的季節進行不同的處理,也就是說,要根據季節的不同創造出新的意境。為何這么說呢?接下來他列舉了古人常識性描寫四時的詩句:“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共水云連。’其夏曰:‘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5]55這些詩句都清晰的描寫出四季,并把各季節的特征都清楚的展現出來,而石濤所關注的是情景違背了時令的例子:“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于冬,推于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云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5]55不合時令是一種天氣突變,天氣突變是因某種客觀原因導致,正所謂“滿目云山,隨時而變”,石濤所關注的就是這種變性,變性就是不平常,是特殊,而在這種不平常,特殊后面,石濤所要強調的是一種富于想象的、獨特的、具有創見性的精神世界。因為他不僅僅是要反映一般的或者不合時令的景象,而是要根據不同的景象創造出不同的意境。在本章結語中石濤寫道:“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里禪乎?”楊成寅先生在解釋此句話時首先指出“禪”與“詩意”的關系,并得出石濤的“畫里禪”就是“詩意”。他還引證了鈴木大拙關于“禪”的解釋:“禪則把自己投入創造的淵源,汲取其中所蘊含的一切生命。”既然禪是把自己投入創造的淵源,那么,創造在禪的這種行為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而這正是石濤所遵循的原則。楊成寅先生在從鈴木大拙對“禪”的解釋得到的啟發中指出:“‘禪的方法’可以說是審美的方法、藝術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把對象當成一個完整的、有生命的東西去進行感受,要求我們‘設身處地’去感受它的內在生命以及內在生命的外在表現,要求我們用‘生活本身的形式’即審美的形象的形式去描繪和表現對象。”[6]201他在這里強調的其實就是主客體的關系,這種關系乃是互為交流的,這種交流所激發出來的就是一種獨特的創造。
石濤在理論上對于“寫”的運用,從以上對畫論的分析我們已經清楚的知道了它的意義。那么石濤在具體的作品中,也是否身體力行的實踐呢?石濤留下了大量的題畫詩跋,在這其中有許多詩跋與“寫”的運用直接相關。
石濤在《題春江圖》中寫道:“書畫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筆混沌開,入拙聰明死。理盡法無盡,法盡理生矣。理法本無傳,古人不得已。吾寫此紙時,心入春江水。江花隨我開,江水隨我起。把卷望江樓,高呼曰子美。一笑水云低,開圖幻神髓。”[5]79在這段題跋詩文中,他說到:“理盡法無盡,法盡理生矣。”其意思可理解為:畫理有盡但畫法無盡,一旦畫法盡時,另又有了新的畫理。其實就是說畫法畫理本無窮盡,它是不會因為古人流傳下來一定的理法而不會衍生出新的理法。所以石濤接下來寫道他作畫的狀態:“吾寫此紙時,心入春江水。”何以把心交與了春江水呢?這又與“禪”似有微妙聯系。意思是說他在寫畫的時候,已經把當下的我交予了春江水,就是把我當成了春江水去感悟它的內涵所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石濤是不為古法所拘,不為外形所限,也不為先入的理性所控制,我手寫下當下之我,用他的話說就是“只在臨時間定,”將一切交給瞬間的感悟,這瞬間的感悟就是把我失卻在春江水中所得來的。他是這樣說的,也是在他作畫的同時這樣做的。
從對該題畫詩中“寫”的運用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他在題畫詩中也是把他的創造思想融入其中,這與他所建立的畫學體系完全相符(石濤還有很多題畫詩都是如此運用,如《夏日避暑松風堂畫蘭竹偶題.墨竹卷》等等)。然而,畫面本身是否也如詩一樣具有這樣的創造性呢?答案是肯定的,楊成寅先生在對他具體作品的創造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不單從線條抒寫性創造運用方面加以解析,并從構圖、用墨、意境、用色等等,都作了精辟的分析,特別是在分析《春雨圖》這幅畫中,他對石濤這種獨特的寫畫方式的由來,作了如下的解析:
這種樹的主干畫法從哪里來?我覺得是從以下兩方面:一是它純熟地掌握了古代繪畫積累下來的墨法,但這傳統的墨法未見用來畫老樹干。二是他對這種老樹逢春發新枝新芽的景象有直接的觀察、深刻的感受和鮮明的形象記憶,而且從中直接感到(受)或理解到(識)用什么樣的筆墨才能對之作恰當的描寫和表現。畫上樹后的雨中山,其山腰有霧氣的情景,完全象是現代水彩畫家用不顯筆墨痕跡的渲染法畫成的,真實而又簡潔。這種畫法絕對不是畫家參考了西洋當時已經存在的水彩畫法,而是畫家從自然景色本身感悟出來的。不管從上述的哪一方面看,就畫此幅作品中的樹干與迷蒙山色的具體方法本身來說,都是“無法”的,可以說是“以無法生有法”[7]。
他所說的“以無法生有法”,最終要強調的仍是創造。因為你無論是通過舊有的筆墨表達方式發展得來的,還是通過山水自身傳達出來的信息啟發而得,他都是石濤在當下之悟中的創造。所以在石濤的畫作中,(雖然只舉此一幅圖例,當然還有更多。楊承寅先生已經做了大量精辟的分析,在此不再累述。)我們依然可以看出他是把這一創造思想貫穿始終的,也即應證了石濤的“寫”不只是簡單的主觀或者客觀,它不僅包括了此二者的意義,同時它還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三、結語
從以上我們對“寫”的基本涵義解釋與石濤畫學中“寫”的意義分析可以看出,石濤的“寫”不僅僅具有了中國傳統的寫意精神,他還將“寫”畫的狀態發展為“創造”的過程,這種創造精神的體現,其實就是畫學思想的具體表達。他以一種對待新生命出現的方式去感悟、傾聽、發現他的每一次“寫”。
[1]薛永年.驀然回首[M].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36.
[2]周汝昌.神州自有連城璧[M].青島: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
[3]徐建融.中國畫的傳統[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32.
[4]朱良志.石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1.
[5]石濤.苦瓜和尚話語錄[M].周遠斌,點校.青島: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6]楊成寅.石濤畫學[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
[7]楊成寅.石濤[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43.
The Significance of“Xie”in Shi Tao’s Paintings
WU Yong
(School of Music,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Xie”,a distinctive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is widely employed in free-style painting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Free style”,namely,a free way of expressing emotions,has tremendously improved and changed painting styles 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re is no exception of Shi Tao’s“Yi-hua”system with“Xie”as a critical part.Shi Tao not only inherited“Xie”from ancient painting methods,but also made a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it.So his paintings have mirrored spirits of Chinese painting,his own innovation and personality.
Chinese painting;Shi Tao;“Xie”
J202
A
1009-8445(2011)03-0021-06
(責任編輯:禤展圖)
2011-03-12;修改日期:2011-04-14
吳勇(1983-),男,貴州銅仁人,肇慶學院音樂學院教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