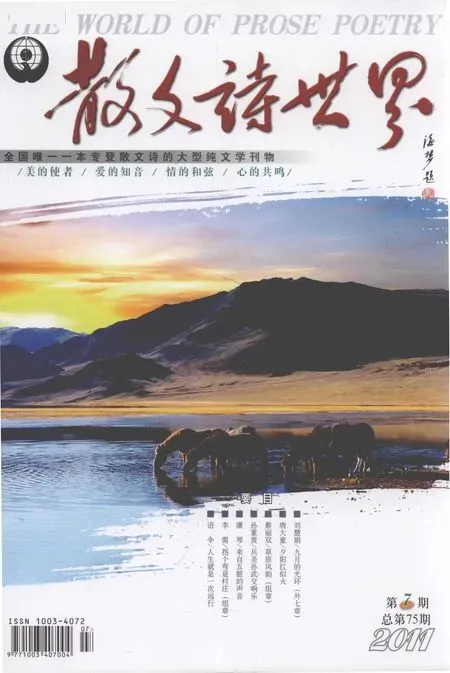草原風韻 (組章)
蔡麗雙

咫尺草原
離開了草原,草原卻近在咫尺。是牽掛縮小了距離,是眷戀縮短了路程。
在香港芙蓉軒的書案上,擺著我在草原拍下的彩照。那種沁入神髓的愛,以笑意,外現于眼角眉梢;以參悟,更深蘊于心靈深處。
以詩筆為鞭,鞭策記憶的駿馬,在草原拾綴刻骨銘心的印記,用靈感的膏腴,潤澤成一個個深有靈性的方塊字,妙組成如鯽的思辯詩行。
我要把洋溢的詩意,深鍥入哲理的詩篇,寄給草原,答謝草原恩賜給我的教益和啟示。
世間真正的距離,是心與心的距離。格格不入,咫尺即是天涯,遠在萬里外。靈犀相通,天涯若比鄰,毫無障礙,近在咫尺。
打開心窗,可以望見草原的奔馬,可以望見牧人的氈房;可以望見哈達的敬意,可以望見敖包的祭禮;可以聽見搖蕩的駝鈴,可以聽見馬頭琴的回聲……
奔赴草原,與草原零距離接觸,從此,不管置身于天涯海角,草原總鮮活在我的心中。
月亮湖畔
月亮湖是騰格里一塊無瑕的美玉。湖中蘆葦茁長處,竟把湖水分割成一半咸,一半淡。蒙古高原的奇異譎秘,也在月亮湖這個小梨窩中珍藏。
這時,絢爛的晚霞,正簇擁著落日,為湖水傾下妍輝綺彩。
終年生活在這里的野鴨,源自深衷的鳴叫,表白著留戀,濃情厚意投給這大漠綠洲。
南來北去的候鳥,正好在這里歇腳。天鵝舒展曼麗的身姿,悠閑得像仙鶴一般灑脫飄逸。
湖水蓄滿詩意,蕩漾詩行,厚蘊箴言。
湖水漫噬著憂傷的歲月。面對歷史的叩問,月亮湖在思考著圓滿的回答。
站在湖畔,為何我的鄉思,像湖水那樣浩淼,像蘆葦那樣娉婷?
草原黃昏
草海涌蕩著不朽的詩章,那是千年讀不盡的長卷。
當羊群回歸棚圈,黃昏美麗得如火燒云般燦爛。
一聲聲咩咩,是沁人心脾的美韻,揉順著氈房裊裊飄升的炊煙。
牧人心靈的企盼,在暮色中宏昂地呼喚,呼喚明天更加明媚。
少女明亮的眼眸,是閃爍著柔光的燈,神秘地燃放著心中的渴望。
夢想在風中砥礪,躍躍欲試,期盼用心尺丈量春天,丈量生活,丈量草原。
一支飽經滄桑的牧歌,染濃了草原的翠嫩,以一種鄉土的音律,在聚焦花朵般的微笑。
黃昏是一種過渡,黑夜是船,黎明是岸。
幸福的跋涉
暮色漸漸黛暗了沙丘,一隊駱駝徐徐行走于沙丘之上,色澤與沙丘融入大千黑色的眸子。
縱使聽不到駝鈴的清音,但堅信駝鈴一定鏗鏘地響著。
一聲聲駝鈴,是播撒于沙漠的福祉,恰似神奇的種子,會萌生沙漠的鮮嫩綠意,會衍生沙漠的塞外江南。
駝峰豎起我心中的帆檣,在駝鈴的美韻中,正一步步作幸福的跋涉,欲抵達綠色的遠方,欲抵達美好的港灣。
駱駝馱著沉重的夜色,一個個蹄印,必會拽出明麗的曙光。
馬頭琴手
以王者的尊嚴,以民俗的奕真,馬頭琴在你的指下,拉出催人淚下的婉約曲調,感人肺腑,贏享人們的敬仰。
琴桿頂端精雕細琢的馬頭,逼真的形象,奔馳出牧民崇拜的情懷。你把馬頭琴視為圣物。
馬頭琴從祖先手里,一代一代傳下來,傳到了你的手里。你手中的馬頭琴,歷經了多少滄桑?經受了多少風雪?你手中的馬頭琴,彈撥了多少凄厲?拉奏了多少歡樂?
草海蒼茫,天風低吟,霧靄縹緲。萬里綠草原就是你的家。
馬頭琴的每一個音符,都是你的愛兒寵女,都是你縈心繞膝的子孫。是生命的語言,是心靈的契合,精神的食糧。
每次演奏之前,你用奶油或奶皮點抹馬首,用綢緞哈達系于琴頸,你潔手修指,虔誠彈拉。你能拉出風,拉出雨,奏出雷鳴電閃,奏出驕陽明月,拉出草原的心跳,奏出牧民的心聲。
你的馬頭琴,是縱橫披闔于草原的駿馬,神圣而平易,端莊而不羈。你能用琴聲感化棄仔的母畜,回心轉意,哺乳幼畜。
你手中馬頭琴的藝術魅力,可以融化堅冰。
許多傳奇在你的琴聲茁長,徜徉在牧民的生活中。
萬 人 坑
北陲的海納爾要塞,是中國勞工冤魂未雪之城。輕輕地打開永遠不會塵封的記憶,一幕幕悲慘的圖景,凸現在眼前……
像惡鬼一樣的日本侵略軍,悍捕中國民眾到此建筑要塞。饑寒交迫、夜以繼日地繁重勞動,餓死、凍死、累死、病死的勞工,被鞭打得皮綻肉爛而死的勞工,用汽車接連載往海納爾河北岸的沙地挖坑掩埋。左右的敖包山和北山,酷似中國悲哀和恥辱的兩塊墓碑。
工程竣工時,為了保密日軍罪惡的證據,竟將勞工分期分批,槍殺與活埋。萬人坑的無辜骨骸,實際已超萬具。我們的同胞,在黃泉下憤怒地流著血淚……
21世紀的第一年,中日共同在萬人坑前種下一片松林,立碑為志,寫下美好的祝愿,聲稱這是象征友誼的和平之林。然而,在這片深深地留下戰爭悲慘傷痕的土地,永遠會記住歷史的血海深仇。
肅立在萬人坑前,我的熱淚流成了滂沱的河水,為我們泉下的同胞深深祈禱安寧,渴望我們的祖國日漸富強。東洋未必凈塵氛,血口又想鯨吞釣魚島,跪拜神祉的首相,讓中國人民看到了濃黑的新陰影!
金帳汗游牧風情
天蒼蒼,地茫茫。古老民歌的悠然韻律,仍在當今內蒙古金帳汗的現實時空中蕩漾。
悠悠藍天,朵朵白云,無垠綠草,遍地牛羊,點點氈房,裊裊炊煙,這些金帳汗的風物,構成了當今世界上罕有的以游牧部落為主題的旅游景觀。
呼倫目爾草原的穆爾格勒河,是“中國第一曲水”。河畔的遼闊草原,是中外馳名的天然牧場。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歷來就在這里繁衍生息。
打開史志發黃的卷頁,可看見成吉思汗曾在這里厲兵秣馬,與各部落爭雄,風卷得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的風云變色,終于占據了呼倫貝爾草原。一代天驕的腳印,至今仍氤氳著歷史和人文的氣息。
每年夏季,蒙古族和鄂溫克族的牧民,便在這山青水秀、水草豐美之地,形成了游牧部落的群體。這難道不是天時、地利、人和“三位一體”的自然融合嗎?
旅游區的布局,賡襲了當年成吉思汗行帳的格局,抑或說,是縮影,是再現。歷史與現實在這里和諧焊接。
篝火狂歡晚會的烈焰和歌舞,扣人心弦。
套馬、馴馬表演的精彩,剽悍著人們的魂魄。
蒙古式搏擊、角力擂臺賽的險勝,掀動了掌聲的浪潮。
祭敖包的習俗,世代不衰。
薩滿教文化表演的豐富多彩,給人一種浩博美的享受。
餐飲文化的奇特淳美,也愉悅著人心。
生活、文化與自然環境是相互綰系著的不可分割的臍帶,由此衍生了這個游牧部落的繽紛歷史風情。
西夏古塔
歷史的腳印不會被塵封得無法窺視。我小心翼翼地抹去歲月的塵土,即看到當年黑水河繞過黑城,流經綠城的屯田區,注入居延澤。美麗的河魂,以神話之指,繪狀了一派繁榮景象。
把眼光收回現實,本應展現在眼前的古綠洲,被大自然無情地吞噬了,只留下殘破的廢墟,見證著昔日的繁盛。
思緒繽紛。我多么渴望變成一滴清露,在這里重現的綠洲中,永遠唱著心靈的歌。
凸現在眼眸的,還是那些西夏古塔。一座座,時而飄浮在幻海上,時而隱現于褐白色的沙丘之間。
這是苦行跋涉的僧侶之化身嗎?
佛塔起源于印度。佛教是西夏的國教,西夏當年建塔成風。這些古塔,任憑風沙不斷,依然默默固守于腳下的土地,好像最寧靜的港灣是不易的禪心。
黑城和綠城遺址附近,有多處保存相對完好的土塔。許多佛教徒的骨灰被摻入黃泥,制成高約十厘米的小塔,置入佛塔下面的洞穴,以求多獲庇佑。這無疑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力量使然。我想,人總是在一種信仰的支撐著生活,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信仰是至善至美的,不愿去想信仰應否用實踐來驗證它的正確。
西夏古塔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頁史志,細心品讀,可得到啟示和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