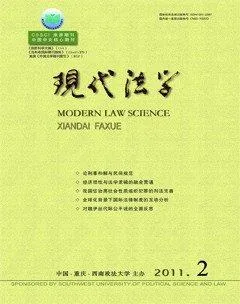傳統法律中“罪家長”制度研究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法律思想,等級制和家族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學界長期以來主要關注了君權、夫權和父權,而極少研究君、夫、父所承擔的義務。本文以家族制的核心“家長”為研究對象,以《大清律例》為切入點,通過分析家長在家庭中作為夫、父、家主依法所享有的權力以及對家庭、社會、國家所承擔的義務,來說明家族制中的家長不僅是權力的享有者,同時也是義務的承擔者。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來說明我國封建社會成功設計了與當時經濟、政治制度相適應的權力義務分配模式。
關鍵詞:家長:夫權;父權:罪家長
中圖分類號:DF092 文獻標識碼:A
法律是一種社會規范,是一個國家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甚至風俗習慣密切聯系,維護著一定社會的現實制度和倫理道德觀念。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農業文明為經濟基礎的,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家族主義和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法制通過引禮入法完成其儒家化,家族主義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之一。家長作為家庭的管理者,既享有國家賦予的特權,也承擔著其對于國家的責任。
一、中國傳統法律的儒家化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最解放的一個時代,其中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對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影響最大。西漢武帝時接受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取得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地位,古代法律開始儒家化。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漢代的引經注律和引經決獄。二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引禮入法。隋唐律繼承引禮入法的成果后成為中國法律的正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唐律一準乎禮”。儒家講貴賤有別,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于是法律中的人有了皇帝、官貴、良民、賤民之分別,與此對應的服飾、宮室、車馬、婚姻、喪葬、祭祀之制也都用法律加以規范;八議、官當制度成為官貴所享有的法律特權。儒家還重視尊卑、長幼、親疏的差別,講孝悌倫常,《禮記·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于是,親屬相犯,準五服以制罪。《孝經》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于是不孝罪隋唐以來名列十惡,標于篇首。儒家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于是法律允許親屬相隱,不要求子孫作證,更不允許子孫告父祖。禮有七出三不去,于是法律規定其為離婚的條件。除此之外,有許多原本詳細規定于禮書中的行為規范,編制法律時被納入法典中,加以刑罰的制裁便成為法律。古人說“禮,法之大分也”,又說“法出于禮”,不無道理。
唐律之后,歷代的法典雖然編制不同,內容有所異,卻都代表同一種傳統精神,即儒家的禮治精神。而禮的核心即周禮中的“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先秦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新儒學中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毋庸置疑,君權、父權、夫權都在歷代法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并綿延不絕兩千余年。正因為如此,后世的研究者更多的去關注君、父、夫的權力,而忽視了他們對國家、社會和家庭所承擔的義務。在研究有關家長的法律規范時,重視了家長的權力,而忽視了法律中有關“罪家長”的規定。其實,任何一個國家或者社會要想維持繁榮穩定,其權利義務的設定對象不可能是截然分開的,只不過對不同的群體而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不相同,有的義務重于權利,有的權利大于義務。古代社會中的家長也是權利義務的承擔者,因而法律中才會有諸多“罪家長”的規范,只有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才會全面認識“家長權”。
二、傳統法律中的“家長”
在家族制社會中,對于家庭內部而言,家長是一個家庭的管理者;對于社會和國家而言,家長是一個家庭的代表。家長對家庭成員行使管理權,對國家和社會承擔義務。
(一)就夫妻之間而言,丈夫是家長,行使夫權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認為女人始終是處于男人意志和權力支配之下的。《孔子家語·本命解》云:“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也就是說,女子自生至死都處于從屬地位,沒有獨立意志可言。在家庭分工方面,自然是男子主外女子主內,原則上“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也就是做飯、打掃、縫補之類的家務勞動,《說文》解釋:“婦、服也”。《爾雅·釋親》說:“婦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在家庭財產權方面,妻子只在一定范圍內擁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自由處分權。在丈夫去世后,妻子也沒有財產繼承權。在離婚時,不僅不能帶走夫家的財產,甚至自己陪嫁的財產能否帶走也由夫家做主。夫妻不平等的地位也在法律上予以確立,妻毆夫較常人加重處罰,而夫毆妻則采取減刑主義。
《大清律例》“妻妾毆夫”條規定:
凡妻妾毆夫者,[但毆即坐。]杖一百,夫愿離者,聽。[須夫自告乃坐。]至折傷以上,各[驗其傷之重輕。]加凡斗傷三等;至篤疾者,絞;[決。]死者,斬。[決。]故殺者,凌遲處死。[兼魘魅蠱毒在內]。”“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須妻自告乃坐。]先行審問夫婦,如愿離異者,斷罪離異;不愿離異者,驗[所傷應坐之]罪收贖。[仍聽完聚。]至死者,絞。[監候。][故殺亦絞。]毆傷妾至折傷以上,減毆傷妻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在對子女的管教方面,妻子也受丈夫的限制,甚至妻子與子女一樣都在丈夫的管束之中。《大清律例》“婦人犯罪”條規定:“凡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不許一概監禁,違者,笞四十。”
(二)就父子之間而言,父親是家長,行使父權
中國的家庭是父權家長制的,父親作為家庭中的首腦,家庭中的所有成員,包括他的妻妾子孫以及家庭中的奴婢都在他的管理之下。“父”字,據《說文》:“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字的本身即含有統治和權力的意義。儒家重視尊卑長幼,講孝悌倫常,子女要聽從父母之言,沒有獨立的權力,子孫違犯父親的意志,不遵守約束,父親自可行使權力加以懲責。《呂氏春秋》說:“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顏氏家訓》也說:“笞怒廢于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不僅社會上承認父親這種權力,法律上也有明確的規定。子孫不孝,法律除了承認父母的懲戒權可以由父母自行責罰外,還給與父母以送懲權,請求地方政府代為執行。除享有對子女的教令權外,父親還擁有決定子女婚姻的權力。他可以命令其子女與一定的人結婚,不容子女違抗,“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法律上成為婚姻成立的要件。在財產方面,作為子女,也沒有獨立的權利,不得私擅用財,父母在,不得別籍異財,只能聽從父命,以孝事親。
《大清律例》“子孫違犯教令”條規定:“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
《大清律例》“別籍異財[按此系十惡內不孝]”條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須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坐。若奉遺命不在此律]。”
《大清律例》“卑幼私擅用財”條規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長,應分家財不均平者,罪亦如之。”
總之,一個家庭中的父子之間,父親負責管教子女,安排其生活,子女只能聽命于父親,沒有自由可言。
(三)就主奴之間而言,主人是家長,對奴婢行使家主的權力
在封建社會中,家奴屬于賤民,不享有良民的獨立自主權。家庭中的家奴或買賣而來,或自己投靠而來,或國家賞賜而來,不論什么方式,一旦屬于主人以后,便完全喪失其自由與人格,成為一種商品,或留或賣,全由主人任意處分。《唐律疏議》中的“奴婢同于資財”。“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奴婢“合由主處分”等,真實地描述了主奴關系。主奴之間地位懸殊,法律上各自享有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大清律例》“奴婢罵家長”條規定:“凡奴婢罵家長者,絞[監候]。罵家長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緦麻,杖六十。若雇工人罵家長者,杖八十、徒二年;罵家長期親及外祖父母,杖一百;大功,杖六十;小功,笞五十;緦麻,笞四十并親告乃坐。[以分相臨恐有讒間之言故須親聞以情相與或有容隱之意故須親告]。”
奴婢毆家長處罰更重,《大清律例》“奴婢毆家長”條規定:“凡奴婢毆家長者,[有傷無傷,預毆之奴婢,不分首從。]皆斬;殺者,[故殺、毆殺,預毆之奴婢,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過失殺者,絞;[監候。][過失]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收贖。]若奴婢毆家長之[尊卑]期親,及外祖父母者,[即無傷亦]絞;[監候。][為從,減一等。]傷者,[預毆之奴婢,不問首從重輕。]皆斬。[監候。]過失殺者,減毆罪二等。[過失]傷者,又減一等。故殺者,[預毆之奴婢。]皆凌遲處死。毆家長之緦麻親,[兼內外尊卑,但毆即坐,雖傷亦]杖六十、徒一年;小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緦麻加毆良人罪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加者,加入于死。[但絞不斬。一毆一傷,各依本法。]死者,[預毆奴婢]皆斬。[故殺亦皆斬]”。但是,家長及家長的親屬毆殺奴婢處罰卻輕的多,同條法律規定“若奴婢有罪,[或奸或盜,凡違法罪過皆是]其家長及家長之期親,若外祖父母,不告官司而[私自]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毆殺[或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當房人口,[指奴婢之夫婦子女]悉放從良。[奴婢有罪,不言折傷篤疾者,非至死勿論也]”。“若[奴婢、雇工人。]違犯[家長及期親、外祖父母。]教令,而依法[于腎腿受杖去處。]決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
三、傳統法律中“罪家長”的規定
如上所述,被稱為家長的丈夫或父親或家主,在法律上享有優越于妻子、子女、奴婢的權力。但是法律在賦予家長權力的同時,也要求家長對家庭的每一成員和國家負有法律責任,這是家長不可推卸的義務。這在我國封建法律規范中有諸多體現。
(一)家長是家庭的代表,有些法律責任只“罪家長”
1.家庭違反對國家的義務時,家長承擔責任
在封建社會,財產的劃分是依家庭為單位的,對國家所承擔的賦稅、徭役等義務也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分配的。而在一個家庭中,妻子、子女都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對家庭財產的處理權,他們都在家長的管理之下。一個家庭的代表是家長,也就由家長代表家庭來承擔對國家的責任。
對于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國家而言,土地是其主要的社會資源,地租是其主要的財富來源,從國家到家庭都很重視土地,重視農業經濟。戶籍租稅等事本來就屬于家長的職權,所以法律往往要求由家長獨負其責。《漢書·昭帝紀》如淳引律日“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人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也就是說,早在漢代,占租律便是以家長為負責的對象,占租不實者有罪。除了土地,國家還要控制人口,以便有計劃的分配賦稅徭役,對于脫漏戶口,法律都要求家長負責。《晉書·刑法志》載:“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可見晉時舉家逃亡,對家長要處斬刑。唐、宋律規定“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明、清律的規定相似,一戶全不附籍,有賦役者家長杖一百,無賦役者杖八十,將他人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者同罪。
清律《大清律例》“脫漏戶口”條規定:
凡一[家日戶],全不附籍,[若]有[田應出]賦役者,家長,杖一百;[若系]無[田不應出]賦役者,杖八十。[準]附籍[有賦照賦,無賦照丁。]當差。若將他[家]人隱蔽在戶不[另]報[立籍],及相冒合戶附籍,[他戶,]有賦役者,[本戶家長]亦杖一百;無賦役者,亦杖八十。若將[內外]另居親屬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者,各減二等。所隱之人并與同罪,改正立戶,別籍當差。其同宗伯叔弟侄及婿,自來不曾分居者,不在此[斷罪改正之]限。其見在官役使辦事者,雖脫戶,[然有役在身,有名在官。]止依漏口法。若[曾立有戶]。隱漏自己成丁[十六歲以上]。人口不附籍,及增減年狀,妄作老幼廢疾,以免差役者,一口至三口,家長杖六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不成丁,三口至五口,笞四十,每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所隱人口]入籍,[成丁者]當差。
封建國家除以家庭為單位征收賦稅外,還以家庭為單位來分派差役。如果家庭成員中有隱蔽差役者,也是追究作為家庭代表的家長的法律責任。
《大清律例》“隱蔽差役”條規定:
凡豪民[有力之家,不資工食],令子孫弟侄跟隨官員,隱蔽差役者,家長杖一百。官員容隱者,與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跟隨之人免[杖]罪,[附近]充軍。
為了加強人口管理,法律規定私越冒度關津、私度僧道都屬于違法行為,一個家庭中有人私越冒度關津、私度僧道也罪坐家長。《大清律例》“私越冒度關津”條規定:“若有文引,冒[他人]名度關津者,杖八十。家人相冒者,罪坐家長”。《大清律例》“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條規定:“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并還俗。[入籍當差]”。可見若由家長,家長當罪;既罪家長,即私人道者不坐。《唐律疏議》及《大明律》都有類似的規定。
2.家庭違反禮制,家長承擔責任
儒家是主張禮治的,禮是一種嚴格高低貴賤等級的制度,這種等級不僅體現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還體現在日常生活方式上,衣、食、住、行無所不包。《新書》云:“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這些無處不在的差異,使人一望而知高低貴賤,“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這些等級差異要求人人遵守,不得逾越,漢成帝詔書有云:“圣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馬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
家長是家庭的代表,當家庭內發生違反禮制的行為時,無論家長是否親犯,都由其承擔法律責任。
《大清律例》“服舍違式”條規定:“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物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工匠并笞五十。[違式之物,責令改正,工匠自首免罪,不給賞]”。
如同上面所述,喪葬也是有等級的,對于喪葬違律的行為,也只罪家長。《大清律例》“喪葬”條規定:“其居喪之家,休齋設醮,若男女混雜,[所重在此]。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還俗。”
(二)家庭成員違反封建婚姻法律規范的行為,追究家長責任
在封建社會,青年男女不允許自由戀愛,更沒有婚姻自主權,子女的婚姻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締結的。因為婚姻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家族的事,《昏義》說:“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所以只要二姓的家長同意其子女的結合,經過一定的儀式,婚事便成立了,直系尊親屬,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親屬,有絕對的主婚權。既然家長有主婚權,發生違反封建婚姻家庭規范的行為就要“罪家長”。
《大清律例·戶律·婚姻》中的“男女婚姻”條規定:
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殘、[廢或]疾、病、老、幼、庶出、過房[同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女家主婚人]笞五十;[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給后定娶之人。]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從仍后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后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不用此律。若為婚而女家妄冒者,[主婚人]杖八十,[謂如女有殘疾,卻令姊妹妄冒相見,后卻以殘疾女成婚之類。]追還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謂如與親男定婚,卻與義男成婚。又如男有殘疾,卻令弟兄妄冒相見,后卻以殘疾男成婚之類。]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妄冒相見之無疾兄弟、姊妹及親生之子為婚,如妄冒相見男女先已聘許他人,或已經配有室家者,不在仍依原定之限。]已成婚者,離異。其應為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男女主婚人]并笞五十。
分析該法條可知,在男女雙方已有婚約后,如果發生一方反悔、妄冒、強娶或違期情形時,法律并不追究有婚約之男女的責任,而是追究雙方主婚人的責任。
《大清律例·戶律·婚姻》的最后一條專門規定“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
凡嫁娶違律,若由[男女之]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違律之罪,]獨坐主婚。[男女不坐]。余親主婚者,[余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得減一等。]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得減一等。]至死者,[除事由男女,自當依律論死,其由]主婚人并減一等。[主婚人雖系為首,罪不入于死,故并減一等。男女已科從罪,至死亦是滿流,不得于主婚人流罪上再減]其男女被主婚人威逼,事不由己,若男年二十歲以下,及在室之女,[雖非威逼。]亦獨坐主婚,男女俱不坐。[不得以首從科之]。
主婚人因與成婚人親屬關系的遠近而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關系越近權力就越大,責任自然也就越重。如果是由男女一方的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的,只追究主婚人的責任。如果是由余親主婚的,則主婚人與成婚人根據案情分首從論。有此法律的規定,司法實踐中自然要按律處置的。
道光六年說帖有一案,因娶大功兄妻為妻而獨坐主婚人。
陜撫咨外結徒犯楊秉德娶大功兄妻王氏為妻一案。查律載:嫁娶違律,若由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又媒人知情者減犯人罪一等,又娶小功以上親以奸論。又例載:凡嫁娶違律罪不至死,仍依舊律定擬各等語。此案楊秉德收大功兄妻王氏為妻,系由伊母楊麻氏主婚。該省聲明罪不至死,按例應依舊律定擬,照律獨坐主婚。將楊麻氏依聚小功以上親之妻以奸論,奸緦麻以上親之妻者杖徒律,擬杖一百,徒三年,照律收贖,與例相符。楊秉德收大功兄妻楊王氏為妻,系由伊母主婚,業已罪坐伊母,男女律不坐罪,所擬照律免罪自可照覆。
道光九年說帖有一案,因娶緦弟妻余親主婚而分首從。
陜西司查律載:嫁娶違律,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獨坐主婚,男女不坐,余親主婚,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又娶同宗緦麻親之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各等語。是嫁娶違律之案,應將父母主婚及余親主婚分別辦理,界限甚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楊錦椿主婚,將霜媳母氏改嫁與緦麻服侄楊宗德為妾。在母氏聽從翁命,律得不坐。而楊錦椿系楊宗德緦麻服叔,即屬余親,按律應分別首從,于娶緦麻親之妻徒罪上減等問擬。今該督以楊宗德娶緦麻弟妻系氏翁主婚,照律不坐,實屬錯誤,應即更正。楊宗德應改依聚同宗緦麻親之妻杖六十,徒一年律,系余親主婚,該犯為從,應減一等,杖一百。可見,嫁娶違律時,追究主婚媒人罪是權責相當的。
婦女逃亡改嫁者,也視情況不同,對主婚人處以不同的處罰。《大清律例》“出妻”條規定:“若由[婦女之]期親以上尊長主婚改嫁者,罪坐主婚,妻妾止得在逃之罪。余親主婚者,[余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主婚改嫁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至死者,主婚人并減一等。[不論期親以上及余親,系主婚人,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此外,婚姻法律規范中還有許多規定要求主婚人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比如:“僧道娶妻”條規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主婚人]同罪”;
“同姓為婚[為婚兼妻妾言禮不娶同姓所以厚別也]',條規定:“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居喪嫁娶”條規定:“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八十”;“其夫喪服滿,[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婦人及娶者,俱不坐”;“逐婿嫁女”條規定:“凡逐[已入贅之]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坐。[如招贅之女通同父母逐婿改嫁者,亦坐杖一百]”,并視情況予以不同的處罰。
嘉慶二十四年湖廣司有一案,因女被毆接回改嫁尚未成婚,其父被按律減等處罰。
南城察院移送張大因伊女張氏常被其夫傅保打罵,即起意將張氏接回欲行改嫁,尚未成婚。將張大依逐婿嫁女杖一百,未成婚減五等律,擬笞五十。
道光二年有一案,因婿犯竊將女接回私行改嫁已成婚,其父被依律處罰。
東撫題:趙諤子毆死王四案內之劉松因伊婿王振犯竊將女劉氏接回,私行主婚改嫁。將劉松照逐婿嫁女律,擬杖一百。
(三)家長有負監護職責時,要承擔法律責任
按照現代刑法理論,罪責自負,每個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在封建社會由于所有家庭成員都居于家長之下,法律也賦予了家長教令權,家長就應隨時督察,及時管教,所以家人犯罪,就意味著家長管教不力,失于監督,沒有履行好自己的監管職責。因而法律在追究行為人責任的同時,家長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此處系借用現代民法中的連帶責任一詞,顯然我國封建法律追究的是刑事責任),在某些情況下,家長甚至要對家庭成員的行為獨自承擔責任而家庭成員則被免除責任。
1.在共同犯罪中,一家人共犯,原則上只坐家長
《大清律例》“共犯罪分首從”條規定:
“凡共犯罪者,以[先]造意[一人]為首,[依律斷擬]隨從者,減一等。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長。若尊長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歸罪于共犯罪以次尊長。[如無以次尊長,方坐卑幼。謂如尊長與卑幼共犯罪,不論造意,獨坐尊長,卑幼無罪,以尊長有專制之義也。如尊長年八十以上及篤疾,于例不坐罪,即以共犯罪次長者當罪。又如婦人尊長與男夫卑幼同犯,雖婦人為首,仍獨坐男夫]。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造意為首,隨從為從。侵謂竊盜財物,損謂斗毆殺傷之類,如父子合家同犯,并依凡人首從之法,為其侵損于人是以不獨坐尊長]。”
在清朝發生的一起家人共販鴉片的案件中,刑部聲明了辦理這類案件的原則:
鴉片煙雖系可以害人之物,然販賣者意在圖利,非有意于害人,與斗毆殺傷之損傷于人者迥殊,買食之人皆由自愿,設因而致斃,不能坐以擬抵之罪,即不能科以侵損之條。至興販鴉片煙不準援減留養,自系因其情節較重,嚴辦示懲。惟本部辦理一家共犯案件,果系侵損于人,雖杖笞不能獨坐尊長,倘非侵損,即斬絞亦難概等凡人。現在該省咨報外結徒犯冊內,黃達盛等販賣鴉片煙泥一案,聲明黃達盛之子黃幅爽訊系知情,惟已罪坐其父,例免治罪。
這段論述表明兩層意義:一是販賣鴉片煙不算家人共犯中的侵損行為;一是刑部辦理一家共犯案件時的原則,即“果系侵損于人,雖杖笞不能獨坐尊長,倘非侵損,即斬絞亦難概等凡人”。
一起家人私鑄鉛錢的案件,也體現了上述刑部的原則:
惟查乾隆四十二年浙江省吳升遠私鑄鉛錢,令其子吳廷元相幫,共鑄錢三千九百余文,將吳升遠以例發遣,聲明其子吳廷元系迫于父命,可否照一家共犯只坐尊長律免議,聽候部示,經本部議以律內父母有罪,相為容隱者勿論,一家人共犯只坐尊長,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吳廷元聽從伊父吳升遠煽火磨錢,并非侵損于人,自不得以凡人首從論,其知情不首,系子為父隱,律得勿論,將吳廷元照律免議題結亦在案。
誣告在古代法律中多有規定,一般采用“誣告反坐”的原則處罰,但如果誣告系屬聽從父命,則罪坐其父,嘉慶二十一年直隸司有一案,方振有“誣告霸地系因聽從父命”,所以誣告的處罰由其父承擔,本人雖不勸阻其父,照不應律治罪。
順尹奏:方振有誣控張純霸地,系屬聽從父命,應罪坐伊父,惟明知伊父所告不實,并不勸阻,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
家人共犯中,除父子共犯外,還有兄弟共犯的情形,這時以兄為尊長,道光元年有一案,“聽從伊兄主使赴京抱告重情”,而罪坐其兄。
南撫奏:董宗璞遣弟董宗珠赴京誣控董宗檉藉案毀搶,并官吏故縱出入人罪等情,審系虛捏,將董宗璞依告重事不實例擬軍,董宗珠聽從抱告,復代繕呈詞,依為從減一等擬徒。本部以一家共犯,罪坐尊長,董宗珠系聽從伊兄主使,業已罪坐其兄,應免置議。
在古代社會,身為長隨,是沒有資格通過科舉為仕,捐財為官的,嘉慶二十五年有一案“長隨為子捐監加捐衛千總銜”,而獲罪,但是捐官的家長有罪,而任官者無罪。
淩廷選系屬長隨,為子淩源、淩濤捐監,又為淩源加捐衛千總,例無治罪專條……此案淩源所捐衛千總系伊父淩廷選冒捐,應罪坐尊長,將淩廷選比照隱匿公私過名以圖選用未除授者,充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淩源、淩濤業已罪坐其父,所捐千總監生一并斥革。
2.對于婦女的某些犯罪行為,原則上罪坐夫男
在封建社會,強調男尊女卑,要求婦女遵守“三從四德”。男子享有大于婦女的權力,因而要承擔大于婦女的法律責任。法律規定對于婦女的某些犯罪行為,原則上罪坐夫男。在古代中國,軍、民、僧道人等服飾器用,都有定制。若常服[大服除外]僭用錦綺、綾羅等,使用器物用戧金、描金,酒器純用金銀等。婦女僭用金寶首飾鐲釧,及用珍珠緣綴衣履,并結成補子、蓋額、纓絡等件。如被發現,一律照律制罪,服飾器用等物,沒收入官。如是婦女則罪坐家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婦人尊長與成年的男夫卑幼同犯,仍追究男夫卑幼的責任,可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這里的尊長只指男性尊長,在上文“共犯罪分首從”條的規定中寫到“如婦人尊長與男夫卑幼同犯,雖婦人為首,仍獨坐男夫”。在封建家庭中,婦人很難取得家長的地位,自然少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有很多條文規定婦人犯罪,罪坐夫男。
如《大清律例》“鹽法”條規定:
“凡婦人有犯私鹽,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決杖一百,余罪收贖]”。
《大清律例》“褻瀆神明”條規定: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告天]。七燈,[拜斗]。褻瀆神明者,杖八十。婦女有犯,罪坐家長。若僧道休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重在拜奏,若止休齋祈禳,而不拜奏青詞表文者,不禁]。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于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寺觀神廟住持,及守門之人,不為禁止者,與同罪”。
《大清律例》“略人略賣人”條例規定:
“婦人有犯,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及無夫男者,仍坐本婦。[決杖一百,余罪收贖]。
《大清律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例規定:
“凡在長安門外等處妄叫冤枉,辱罵原問官者,杖一百,用一百斤枷枷號一個月發落。婦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無夫男者,止坐本婦,照常發落”。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法律規范給與了婦女承擔法律責任方面的優待。上文的“鹽法”條和“略人略賣人”條均有“余罪收贖”的規定,在其他法律規范中,還有“照律收贖”等,這的確可以稱的上是婦女在接受處罰方面的優惠,與老弱病殘者享有同樣的待遇。
3.家長對子弟的某些犯罪行為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家長對子弟擁有教令權,沒有管理好子弟就沒有盡到家長的職責。對于子弟所犯的一些嚴重罪行,在追究子弟法律責任的同時,家長也要因沒有盡到監管職責而承擔法律責任。這些罪行主要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封建法律這樣規定也是試圖通過追究家長的責任以督促其履行對子弟的監管職責,最終維護社會的穩定。
《大清律例》“強盜”條例規定:
強盜同居父、兄、伯叔與弟,其有知情而又分贓者,如強盜問擬斬決,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問擬發遣,亦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雖經得財,而實系不知情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發落。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為盜者,杖一百。
《大清律例》“竊盜”條例規定:
凡竊盜同居父、兄、伯、叔與弟,知情而又分贓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雖經得財而實系不知情者減三等。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為竊盜者,笞四十。
《大清律例》“恐嚇取財”條例規定:
凡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或張帖揭帖,或捏告各衙門,或勒寫借約嚇詐取財,或因斗毆糾眾系頸謊言欠債,逼寫文券,或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此等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者,不分曾否得財,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俱絞監候。其犯人家主父兄,各笞五十,系官交該部議處。如家主父兄首者,免罪,犯人仍照例治罪。
《大清律例》“盜賊窩主”條例規定:
強、竊盜窩家之同居父兄、伯叔與弟,自首者,照例免罪,本犯減等發落外,其知情而又分臟,各照強、竊盜為從例減一等治罪。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窩盜者,各照強、竊盜父兄論。
《大清律例》“私鑄銅錢”條例規定:
孥獲私鑄,如本犯問擬斬、絞,其知情分利之同居父、兄、伯、叔、與弟,減本犯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本犯問擬發遣,亦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雖經分利,而實系并不知情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發落;其父、兄不能禁約者,杖一百;有能據實出首,準予免罪。本犯仍照律內得兼容隱之親屬互相告言,各聽如罪人本身自首法科斷。
《大清律例》“盜馬牛畜產”條例規定:
凡冒領太仆寺官馬至三匹者,問罪,于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不分首從,俱問常人盜官物罪,家長引例,家人不引]。
4.家奴應聽命于家主,對于某些違法行為,原則上也要“罪家長”
家庭中主奴地位異常懸殊,奴婢不是家庭成員,屬于家庭的私人財產(奴婢律比畜產),奴婢對于家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奴婢的社會關系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家主對于奴婢而言,既享有一定的家長權力,也應承擔相應的家長責任,但家主對于奴婢的責任要輕于其對妻子、子女的責任。早在五代時就有法律規定“所犯私鹽曲,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只罪家長主首。如家長主首不知情,只罪造意者,余減等科斷”。
《大清律例》在“良賤為婚姻”條中規定:“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主婚人]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指家長言],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妄冒由家長,坐家長;由奴婢,坐奴婢]。各離異,改正。[謂人籍為婢之女。改正復良]”。《大清律例》“劫囚”條規定:“其率領家人、隨從打奪者,止坐尊長。若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
由于奴婢身份的特殊性,家長對于奴婢的行為所負的責任與義務相對于其權力而言是次要的和有限的,但也是必須的。除律的規定外,道光十三年通行“家主失察奴仆偶然窩賭之例”。
江西道御史奏稱: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奴仆犯者家主系官,交與該部,系平人責十板。
四、結語
任何一個社會要維持自己運轉,必然有權利義務的分配,從權利和義務的關系看,二者不僅在總量上是等值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補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中國封建社會的運轉,必然要設計出自己的權利義務分配模式。
中國古代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社會,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條件下,家庭是最有利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整個社會是以家庭或家族為基本單位來構建的。作為基本單位的家庭也是社會穩定的細胞,家庭秩序與國家秩序、社會秩序密切相連,這是家族本位法律的理論基礎,也是儒家齊家治國一套理論的基礎,如果每一家族能維持其本單位內的秩序而對國家負責,整個社會的秩序自可維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家庭的倫理就是社會的道德,對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對于國家的犯罪。國家必須維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憑藉,以維持社會。為此,一方面國家在法律上不能不給家長以特別之權,使其對家庭成員行其專制之手段,以維持一個家庭的有序狀態,從而支持國家的穩定;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使家長對國家負責,在家長沒有盡到職責,管理不善,教導無方的情況下,要承擔家庭甚至家庭成員在法律上的責任。正如文中所提到的,家長在享有“夫權”、“父權”、“家主”權力的同時,也要在妻子、子女、家奴的某些犯罪行為中承擔獨立責任或者“連帶責任”。
從封建法律制度的整體來看,不僅設計了權利義務的分配,并且在制度設計中力求做到責權一致。比如對封建女性而言,其法律地位、享有權利明顯低于男子,要求其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因此,其對于家庭、國家和社會承擔的責任就要小于男子。女子的婚姻,無論是初嫁還是再嫁,從來不是自己獨立意志決定的,若違律,或是由父母獨立承擔責任,或是相關人員承擔連帶責任,自己完全沒責任或承擔部分責任。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依律收禁外,其余雜犯則交給其夫收管,沒有丈夫,就交給有服親屬、鄰里保管,不許一概監禁,違者,還要被笞四十。在需要婦人承擔責任的時候,要求也與男子不一樣,“余罪收贖”、“照律收贖”常見于對女性的處罰,收贖成為婦人與老弱病殘共享的優待。在脫漏戶口的情況下,唐、宋律規定男性家長要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而女戶則在減二等的基礎上又減三等,看來同為家長,女性要比男性處罰輕得多。在家人共犯中,一般只罪坐家長,卑幼不承擔責任,但是如果是婦人尊長與男夫卑幼同犯,雖然婦人為首,卻獨坐男夫卑幼,因為要求婦人夫死從子,而犯罪后再要求其承擔責任自然不合理。再比如,在婚姻違律追究主婚人責任的法律規范中,也體現了責權的一致性。就享有主婚權的順序而言,首先是直系尊親屬,其次是期親尊長。“我們從嫁娶違律的法律中可以看出尊長的比較主婚權和比較責任。嫁娶違律的婚姻,由直系尊親屬主婚的罪只坐主婚人,嫁娶者無罪,這是因為祖父母父母有絕對主婚權,子孫不敢違背,所以法律上的責任也由主婚人獨負全責。期親尊長,伯叔父母、姑、兄、姊,雖為主婚順序之第二人,卑幼仕宦買賣在外,亦可為之定婚,權與父母相同,但以尊親而論究與父母有別,事實上他們也不會像對子女似的強制執行主婚權,他們多少會征求當事人的同意,所以法律上的責任較輕。唐、宋嫁娶違律的責任由主婚人及當事人分負,而以主婚人為首,嫁娶人為從。明、清律才改為獨坐主婚,其責任與祖父母、父母相同,同時將外祖父母也加入期親主婚人之內。期親以外的尊親屬是主婚順序的第三人。《大明令》及清條例上說得很明白,‘婚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沈之奇《清律輯注》云:‘余親當盡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如無,則從余親尊長’。但這一類的親屬關系最疏,所以只是名義上的主婚人,實際上并沒有專斷的權力,而需征求本人的同意。所以法律上關于嫁娶違律的責任定為‘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除非是男女當事人被主婚人逼迫,事不由己,年在二十以下無斷制事情能力的男子及不能自說婚姻的在室女子,是不能逃避責任,單獨由主婚人當罪的。”其實,研究《大清律例》,我們會發現傳統法律中這種責權的一致性,不僅僅體現在家庭成員間的權利義務分配中,而是在整個國家管理體系中都力求這種分配的合理性,一致性。《大清律例》“同僚犯公罪”條規定“凡同僚犯公罪者,[謂同僚官吏聯署文案,判斷公事差錯,而無私曲者]。并以吏典為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佐貳官減首領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官內如有缺員,亦依四等遞減科罪。本衙門所設官吏無四等者,止準見設員數遞減]。若同僚官一人有私,自依故出入人罪[私罪]論,其余不知情者,止依失出人人罪[公罪]論。[謂如同僚聯署文案官吏五人,若一人有私,自依故出入人罪論,其余四人雖聯署文案,不知有私者,止依失出入人罪論,仍依四等遞減科罪]。若[下司]申上司,[事有差誤,上司]不覺失錯準行者,各遞減下司官吏罪二等。[謂如縣申州,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之類]。若上司行下,[事有差誤],而所屬依錯施行者,各遞減上司官吏罪三等。[謂如布政司行府,府行州,州行縣之類]。亦各以吏典為首。[首領、佐貳、長官,依上減之]。”可見,公私罪分明,過錯與責任一致。
通過《大清律例》中關于“罪家長”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到我國古代社會家庭成員間特有的權利義務分配模式。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合理的、不科學的、不公平的,認為這種權利義務結構下的家庭成員之間沒有自由、民主、平等可言。但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證明,這卻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與當時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相匹配的、合理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