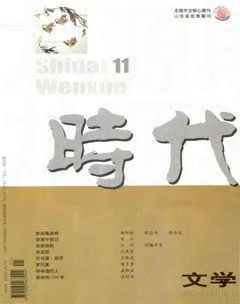為京西文化不懈耕耘的人
在文藝界,提起凸凹的大名,人們都會說,他是國內創作最活躍的實力派作家之一,幾乎每年都有大作問世。的確,他從1985年涉足文壇以來,迄今為止在全國200多家報刊發表文學作品千余篇(部),550多萬字;先后出版散文集8部,長篇小說8部;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作家協會簽約作家;被收入《中國青年作家名錄》、《中國藝術家名人錄》;2002年12月,作為北京市區縣文藝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第七屆全國文代會,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凸凹的散文創作一直引起評論界的關注。著名文學評論家何鎮邦說:“散文是房山文學創作的強項,新時期以來,房山的散文作品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相當引人注目。凸凹出版的幾本散文集,在全國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寫的散文落拓不羈,瀟灑俊逸,自成一體。”他的散文《布鞋》獲《中國作家》優秀散文獎,《呃,又一個女孩》獲第四屆全國青年文學散文獎,散文集《書卷的靈光》獲大眾讀書會優秀書籍二等獎。其中代表作《中國媒婆》、《布鞋》和《雪狐的絕唱》被收入《今文觀止》、《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經典》等權威選本。先后出版了《游思無軌》、《無言的愛情》、《風聲在耳》、《兩個人的風景》、《書性與人性》等多部散文集。由于凸凹在散文領域里的成就和影響,他被推舉為北京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于散文創作,凸凹說:“故鄉是鄉土散文的母題,但故鄉是父輩的家園,只是一種團體(或地域)文化,是我們的基點和出發點。當我們走出故鄉,剪斷與母體連結的臍帶之后,應該以生的急迫姿態,采擷城市文化的枝葉,在母體嫁接、培養一種新植株,即新的鄉土意味,構筑自己的家園。要達到這個境界,我首先不是缺少生活,缺少的是學養與識見。要想寫出鄉土巨制,首先要補補學識這一課,就是要多讀書,增加自己的文化含量。”正是由于這個動因,他開始了廣泛的閱讀和思考,寫出了一篇篇獲得廣泛影響的帶著對于人類生存思考和現代文明意識的“文化散文”。凸凹認為,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無言的友人,都肯與你親近。人只有一次生命,每個人都只有一種生命,但你每讀一本書,就多了一種生命的感受,那么,讀過千本萬本書,你就有了千萬條生命。對此,凸凹說:“這種意象在頭腦中閃過之后,這時的書房里,不是也有風聲在耳嗎?”這是多么有趣的比喻!
在凸凹的散文中,我們認識了京西的鄉情,也了解了京西人的文化底蘊。學者孫郁評價凸凹說:“凸凹生于京西,是個很有性情的人。他的散文,有鄉土的東西,也有學問的東西,很是難得。”久居山野的人,常帶野氣,那野氣中有著淳樸,也有幾分苦意。在凸凹身上,有這樣的氣息,但又多了與山里人不同的學者品位。他喜愛學人小品,對學識有著不倦的追求。因此,視野便異于他人。將野性的東西,嫁接了起來,這恐怕就是他散文創作的成功所在。
凸凹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文人型作家。長期的散文寫作尤其是思想隨筆和讀書札記,使他具備了鮮明的個體意識,也使得他的作品顯得高深莫測。他的小說寫得輕快自如,人物不多,情節簡單,好像一曲二胡,在悠長沉郁的調子里,響著人間一種寓言。有人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小說的本質。小說描述歷史過程是史學的事,史筆出自官衙,小說則出于市井。小說的出身,與小說敘述的人性是吻合的,因而,無論從起源看,還是從自身屬性看,小說是最應該具有民間的品格。應該說,真正具有民間品格的小說,才應該是好的小說。中國的鄉土社會,是一座精神寶藏,幾千年的苦難、智慧,就蘊含在其中。凸凹一直生活在鄉土社會,至今仍是其中的一員,對家鄉的風土人情了如指掌。可以說,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是生活的積累。長篇小說《慢慢呻吟》被評論界譽為是“遠離宏大敘事,用簡潔的詩性筆調反映重大主題的范本”;長篇小說《大貓》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提名獎;長篇小說《歡喜佛》正熱銷坊間,并被《羊城晚報》、《燕趙都市報》等多家報刊連載;長篇小說《玉碎》出版后,《中國作家》雜志社和北京作協、房山區委宣傳部、佛子莊鄉黨委在房山聯合召開研討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這部小說除了貼近當代人的生活,還有鮮明的京西風味特色,為當代京味小說的品種增加了一部力作。作品把一個農家姑娘進入城市后如何變成城市人的蛻變過程展現出來,具有時代意義;長篇小說《雙簧》,以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敏銳觀察和深刻思考,寫出了在相對封閉的鄉村,一個心智超常發展的孩子在成長中的困惑、苦惱和歡樂,反映了農村兒童的生存狀態和成長環境,令人在回味中產生閱讀和思考的快感。
凸凹的創作速度驚人,一本30萬字的作品,大體三至四個月便可脫稿,一般說,每天3000字的任務,他是要堅持完成的,這不能不使人佩服他的勤奮和毅力。
北京作協駐會副主席李青說:“在我們北京作家中,凸凹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作家,他是一個根植于鄉土,又熱愛鄉土的人。他關注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變化,尤其是農民失去土地時候的心態變化,對從鄉村到城市的這個落差,他很敏感。在北京作家群體中,寫城市和寫時尚的作家比較多,寫農村的作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凸凹的寫作越來越有自己的風格,那就是他的‘京西文學’特色。”對于“京味兒作品”,凸凹認為,北京作為政治、文化、社會交往的大都會,原有的痕跡會越來越淡。因此,對“京味兒文化”應重新定位在“都市文化”上,如一味地追求“京味兒文化”,勢必導致向傳統的回歸與追尋,結果是制造一批批比真實的“京味兒”更“京味兒”的偽民俗、偽文化。這種制造越酷似,作品的現實沖擊力越弱,偽文化的色彩越深。
一切文學作品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和產物,作者所生活的環境決定了作品的性質和特點。為了打造“京西文學”,2005年8月4日,凸凹借北京作家協會召開的區縣級作協工作會議之機,提出了將“京西文學”作為第二屆北京文學節的一項重要活動推出的建議,建議得到了北京作協的首肯,并得到門頭溝、石景山兩區文聯的響應。“京西文學”研討會如期在房山召開, “京西文學研究會”也同時成立,“京西文學”的旗幟正式打出,凸凹被推舉為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這就為促進區域文學的創作、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華讀書報》記者魯大智在發表《打造京西文學》一文中說,凸凹的《金菊》、《老橋、父親和我》、《飛蝗》、《青玉米焦玉米》,在思考中涉及京西及京西地理條件、地域文化和歷史傳承對京西人的性格、思維、生活方式所產生的影響,最終釀出了《慢慢呻吟》、《永無寧日》、《正經人家》、《玉碎》等,完全可以說是 “京西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流派的篇章。
因此,凸凹不僅是一個出色的文藝家,也是一位優秀的文藝活動家,他的兩方面成就,都得到了市區文藝界的廣泛認可。2000年,凸凹被北京市委列入文藝“百人工程”,成為北京市的重要文藝家之一;2004年和2010年兩次被市委宣傳部、市文聯評為北京市優秀文藝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