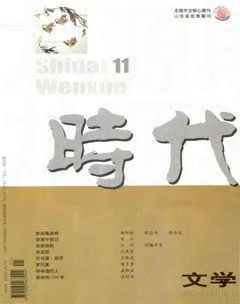凸凹編年史
——二十多年前的凸凹,二十多歲,剛剛從農學院畢業,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手里拿著一塊小黑板,架在田間地頭,給農民講科學種田。
——十五年前的凸凹,三十多歲,我們剛剛相識,那時他是鄉長,在北京房山區南召鄉。他的辦公場所,是磚徹的平房小院,一派鄉土氣息,有一天,小院里來了一群年輕的寫作者,有邱華棟、伍立楊、彭程、從深圳趕來的姜威,還有我,主人就是凸鄉長。
那時我剛剛主編一套《新銳文叢》,包括伍立楊、王開林等在內的新銳們悉數亮相。大概就從那時開始,九十年代中期,那一批寫作者——李師東先生曾命名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漸漸聚攏到一起。很多年后,我與《天涯》主編李少君兄回憶這一群體的時候總結道:這批寫作者的相識相遇,緣起于八十年代校園文化時期,那時各所大學都有文學社團和文學期刊,彼此交流甚多,我與少君、華棟、桑克、杜麗等的往來,就緣于那段時期,但那還只是早期寫作,形成相對成熟的寫作陣容,是九十年代,包括伍立楊、彭程、王開林、葦岸、周曉楓、寧肯、張銳鋒、李敬澤、李馮,以及凸凹,都是在九十年代,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勾結到一起的。不知為何,我們這批寫作者從一開始就具有群體意識,自覺地合并同類項,不像如今“八零后”、“九零后”,個人主義色彩很濃。這并非因為我們喜歡拉幫結派,而是因為相互間的敬重,尤其在九二年全民下海熱之后,奮戰在祖國的文藝戰線的,就更加難能可貴,直至今日,這批人大都步入中年,每個人的生活都經歷了一連串好的或者不好的變故,世俗地位也早已別如天壤——官升副部、正局者有之,貴為軍長者有之,像我這樣的無業下崗人員亦有之,但那種彼此的愛惜敬重,卻有增無減。
在認識凸凹之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在《光明日報》、《青年文學》等報刊,都讀過他的散文,所以,當伍立楊引見我們見面的時候,我覺得內心早已與他熟稔。那天凸凹拿出地方酒招待我們,所有人都喝得有點高,暈暈乎乎地,得到凸凹兄贈送的禮品——鄉鎮企業生產的襯衫,軍綠色的,凸凹的憨樸可愛,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交的朋友。
以后和凸凹的交往就漸漸多起來,至少,房山有了一個可以喝酒、談文學的朋友,對房山的想念便多起來,以至于很多年后,凸凹成為我最重要的一個朋友,我生命中許多重要時刻,凸凹都是和我在一起的。
——十來年前,凸凹到我辦公室,從挎包里掏出一疊厚厚的稿子,說他寫了一部小說,讓我看看。應當說,我當時沒有對這部小說寄予太大期望,只是覺得是朋友的作品,就得看看,不想讀了以后,倒吸一口涼氣。這就是我后來常常提起來的《慢慢呻吟》。這部小說,筆調平淡,沒有絲毫的裝腔作勢,實際上寫得蕩氣回腸,大開大合,遠勝于當時世面上走紅的某些名家名作,凸凹的底層經驗和他對敘事的高超把握,在這部作品表現無遺,體現出一個作家對歷史的洞察力的悲憫情懷,如同我為《慢慢呻吟》所作序言中寫道的,“作家以一種純粹個人化的視角透視他們,作家自己在試圖擺脫任何‘摧眠’……他具有了鮮明的個體意識。這使他的作品顯得高深莫測。當然他把他的個人意識隱含在背后,從不暴露,并不去破壞時間的連續性,小說便很好讀,故事起落轉合,讓人拿得起,放不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千萬個村莊中的一個。九州之內不知能找出多少個翁太元、翁息元、翁上元、翁七妹、南明陽、謝亭云……但他們一旦被作家選定,他們便同作家——還有我們——一道歌哭著上路。所謂的‘共鳴’,實際上是時代留在每個人身上的印記的煥發。作家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在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中設置的深刻的隱喻。這種隱喻,不僅是喚起我們對歷史的重新思索,更提醒我們,我們現在仍處于‘歷史’之中,不要忘了保持清醒的神經。”
我至今覺得,這是一部應當在二十世紀小說史上占有席位的作品,只是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那段時間,我幾乎全部的生活都被這部小說控制了——我上班讀,下班回家還讀,讀到緊要處,時時潸然淚下,以至于在家人和同事面前不斷丟人現眼。出于出版人的本能,我為此書出版竭盡全力,但沒有在全國一流的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我至今引為一大憾事。
《慢慢呻吟》出版之后,我對凸凹戲言:“你可以死了。”意思是死而無憾。
凸凹卻從此在小說領域一發不可收,一部部長篇,如《永無寧日》、《大貓》(原名《鄉長手記》)、《玉碎》、《玄武》等接踵而至,內容涵蓋房山自抗日戰爭時期到改革開放時期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北京城西南郊的房山,這片中國文學版圖上的空白之地,一如福克納筆下神秘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成為凸凹寫作的永久題材。
然而,凸凹也是在這段時期,顯示出他與一般小說作者的不同。他的視野更寬,閱讀范圍極廣,同時創作了大量學術含量極高的思想隨筆和讀書隨筆,這在他的《游思無軌》、《書卷的靈光》、《風聲在耳》、《以經典的名義》等隨筆集中有集中體現,在談到安妮·勃朗特《阿·格雷》、川端康成《山之音》、懷特《人樹》、卡贊扎基《自由或死亡》、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諾里斯《小麥三部曲》、繆塞《一個世紀兒的懺悔》等作品時,都頗具真知灼見。
——十年前,正是我和凸凹喝酒的黃金時代。那日我到房山,照例喝了不少酒,先醉的是凸凹,我把他扶回家,他醉眼蒙眬地說,先在臥室里睡會兒,叫我在他的書房里稍候。這使我有機會對凸凹的讀書有細致的觀察,因為了解一個作家的書房,便會了解他的知識結構和心路歷程。那天,我按照凸凹的指示,在他的書房里“稍候”了整整一個下午,下午的陽光從窗子照進來,使那間不大的書房顯得空曠和溫暖。他呼呼大睡,我并不急躁,是因為他的藏書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我第一次認真地打量他的書房,那是一幢普通居民樓里一套十分普通的三居室,凸凹用了一間作他的書房,書房里四壁書架,從底到頂,開放式的,很有氣勢,靠窗橫放著一張書桌,書桌也堆了很多書。作為一個年輕的寫作者,擁有這樣一間書房,堪稱奢侈。那時的我,書柜和書桌都是放在臥室里的,很多年中,擁有一間專門的書房,都是我的夢想。因為那個書房,所以等待并不顯得漫長,甚至成為對我的某種犒賞。除了隔壁傳來的凸凹隱約的鼾聲,周圍十分安靜,我仔細地翻弄著凸凹的藏書,對凸凹的敬佩油然而生。許多書,是八十年代的舊書,許多書我至今不曾讀過,而他很早就開始自覺地遍覽好書,而且對好書,有著獨到的判斷,許多書,他都密密麻麻地作了旁注,連我那時剛出版不久的三卷本《祝勇作品集》也不例外。那個下午,我看到了凸凹的強大,他必將成為一個有分量的作家。
《慢慢呻吟》出版之后,凸凹沒有大紅大紫,這絲毫不防礙他對寫作的熱情。與那些精于炒作的人相比,文學給他帶來的回報少得可憐。但他是一個溫厚的人,對命運也顯露出溫厚的態度。不苛求,不放棄。
——五年前,我離婚,躲開人群,獨居房山鄉下,后來踢球受傷,瘸腿半年,凸凹自是時而來看我,給我帶來諸多安慰。我也試圖像他那樣,對命運表現出溫厚的態度。我們一起去門口小店,喝小米粥,吃蔥花餅,喝二鍋頭,在無比尷尬的處境中,依然探討紅旗還能打多久這樣嚴肅的問題——后來我去美國啃洋面包,心里還懷念中國鄉村的小米粥。當年有兩個場景不能忘:一是,那年“五一節”,他到房山鄉下看望老母,先把我接上,我就這樣與他一個母親兩個弟弟一個老婆一個兒子還有一條大黃狗一起過了個節,我腿上打著石膏,拄著拐杖,第一次出門,坐在凸凹故園的小院里,讓溫煦的陽光穿越發霉的身體一路把心底照亮,另外,那天的炒雞蛋好吃;二是,一日黃昏他開車來看我,那時我腿上依舊打著石膏,不能動,我就說,在門口小店訂了幾道小菜,去野餐吧,他開車帶著我,一路開到麥子結穗的田里,四周無人,只有風吹麥穗,嘩嘩作響,我們坐在干凈的麥田里,談人生和文學,我從小畫麥穗,直到那天,麥穗才真正開放成我心中最美的植物。
那段時間里,我寫下一部自認為重要的思想學術專著——《反閱讀》。那是我文革學研究長久積聚后的一次噴發,盡管腿上打著石膏,而且腿不能豎起來,只能橫放,以免手術刀口出血,寫作十分不便,傷口的疼痛也時時襲來,但我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一定要寫好這部渴望已久的書。作為精神盟友,凸凹,自是這部書寫作的見證者和支持者。《反閱讀》后來在美國完成,經臺灣著名作家林文月老師舉薦,由臺北的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學術界引起一定反響,美國的電視臺和報紙都作了采訪報導,得到包括哈佛的麥克法夸爾、耶魯的史景遷、胡佛研究院的馬若孟在內的著名漢學家的支持和鼓勵。我回國,把《反閱讀》樣書交到凸凹手上時,他回敬我:“行了。你可以死了。”
我們就這樣給對方判了死刑,并且像兩個賤人一樣對這樣的鼓勵全然笑納。我們有如瞎子背瘸子,在困頓中互相支持。有人議論,凸凹和祝勇穿一條褲子都嫌肥。我慶幸世上還有這樣的褲子,能把兩個熱衷于文字的人結合到一起。我把那句話當作對我和凸凹友情的最佳贊揚。
——四年前,我和凸凹在周曉楓家看影碟,放的是一部以色列電影,英文名字“Walk on water”,意思是“在水上行走”,很詩意,影碟上印的中文譯名卻庸俗不堪,叫《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好像同性戀的片子,實際上不是,是講男人之間的情感,而且是兩個特別的男人——一個是德國男人,另一個猶太男人,情節很淡,沉下去,才能看出導演的功力。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作品,通過兩個年輕人的現實關系反思歷史,表面上輕飄飄,實際上沉甸甸。我和凸凹的共同感受是:這樣的作品是真正的好作品,于平凡素材中見深度,杯水中有波瀾,四兩撥千斤,勝似重大主題的寫作,我們都希望自己寫出這樣的作品。盡管凸凹說我有了《舊宮殿》、《反閱讀》 這樣的書,這輩子的寫作任務,已經提前超額完成了,但至少在我看來,我以往所有的寫作,都是在為寫出“Walk on water”這樣的作品做準備,凸凹的小說,如《慢慢呻吟》,已有這樣的跡象,但對我而言,一切才剛剛開始。
——兩年前,我在康定的一家小書店里看到凸凹一部五十萬字長篇小說《玄武》。這部小說的電子版我看過,但此次是江蘇文藝出版社作為改革開放30年獻禮巨作隆重推出的,緊接著看到報刊上的各種評論,雖遠在藏區,心里仍為他叫好。這部作品后來獲了北京市紀念建國六十周年優秀作品獎。
——半年前,凸凹給我打電話,說他中篇小說集《神醫》出版,邀我參加研討會。當時我仍在藏區,被稻城的雪山圍困,插翅難飛,所以無法參加,只能在電話中表達祝福,回來后看各大報,好評如潮。我知道自《玄武》寫成后數年中,他一直在磨礪中篇,在《十月》、《當代》、《長城》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這本書,也算厚積薄發。
張仃說,大器晚成,這是藝術的規律,誰也逾越不了。金庸說,有人給他看十四歲少年寫的武俠小說,他不看,因為他不相信少年會寫好,他可能有才華,但他沒有閱歷,不知道夫妻之愛、父子之情,不了解人生的各種喜悅和傷痛。
凸凹人到中年,兩鬢已白,但凸凹不怕老,也不怕沒有轟動效應,他有他的自信,他的自信不受他人的態度左右。他的文學路,成熟、穩健、有力。
——一天前,我寫下這篇《凸凹編年史》,試圖對凸凹的文學歷程進行徹底揭發。今天——公元2010年8月18日,我對這一編年史加上最后一句話:
寫好的作品就是在水上行走,看上去不可能,卻有人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