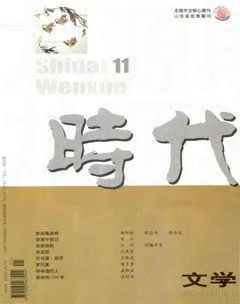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無風(fēng)之樹》:分裂語言的彌合
摘要:《無風(fēng)之樹》的立體敘事方法,使得第一人稱敘事從語言形式和內(nèi)在價(jià)值基礎(chǔ)兩方面彌合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語言分裂,即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的分裂,使作者擺脫了困擾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語言夢魘,得以用中國人的日常話語敘事,還原了漢語的原生性,擺脫了歐美語言對中國人的語言表達(dá)的扭曲。但是作者自身的價(jià)值分裂和第一人稱敘事的局限性決定了這只是暫時(shí)性的、個(gè)案性的彌合。
關(guān)鍵詞:立體敘事;第一人稱敘事;語言;價(jià)值;彌合
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①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的分裂現(xiàn)象在《無風(fēng)之樹》中得到暫時(shí)性的、個(gè)案性的彌合,第一人稱敘事使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一定程度上的統(tǒng)一,使作者擺脫了困擾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語言夢魘,得以用中國人的日常話語敘事,還原了漢語的原生性,擺脫了歐美語言對中國人的語言表達(dá)的扭曲。在歐美文化主導(dǎo)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造成的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的撕裂,在語言上的效應(yīng)是漢語從詞匯到語法各個(gè)層次上的歐化現(xiàn)象,造成了中國人的生活意象和書面語言表達(dá)之間的非原生性,使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描寫和表達(dá)總是有隔靴搔癢之感,對于中國的地方(指北京以外地區(qū))作家來說,更是雙重的痛苦:他還要把方言構(gòu)筑起來的生活意象轉(zhuǎn)換為以北京方言為主的普通話語言意象。余華曾非常形象地描述過這種感受:“我就是在方言里成長起來的。有一天,當(dāng)我坐下來決定寫作一篇故事時(shí),我發(fā)現(xiàn)二十多年與我朝夕相處的語言,突然成為了一堆錯(cuò)別字。口語與書面表達(dá)之間的差異讓我的思維不知所措,如同一扇門突然在我眼前關(guān)閉,讓我失去讓前進(jìn)時(shí)的道路。我在中國能夠成為一位作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語言上妥協(xié)的才華。”②我們把這種語言的轉(zhuǎn)換比喻為“語言進(jìn)城現(xiàn)象”:方言進(jìn)普通話的城,漢語進(jìn)歐美語言的城。
從上個(gè)世紀(jì)三十年代以來,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在語言上的困境已經(jīng)爭論得太多,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荷花淀派”、“山藥蛋派”,企圖用充滿中國鄉(xiāng)土民俗的文化意象去克服語言的異域化,但這是一種偷換概念的做法,文化意象是表達(dá)的內(nèi)容,語言是表達(dá)的方式,即使內(nèi)容完全“國粹”,也絲毫改變不了表達(dá)方式的假洋鬼子品性,八十年代的“京味小說”“尋根文學(xué)”都是相似的情形。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語言困境是歷史造成的,無論今天我們拿出多少種解決方案,都無濟(jì)于事,這是一件人力無可奈何之事,唯一的辦法就是:時(shí)間。這是一個(gè)語言的文化沉積過程:生活意象如何滲透到詞語以及詞語之間的聯(lián)系中去,詞語如何從生活意象中生長出來,詞語如何自然地連接在一起去表達(dá)生活意象,達(dá)到水乳交融的原生狀態(tài),以及詞語自身構(gòu)建起氣象萬千博大精妙的意蘊(yùn)世界,這是一個(gè)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不幸的很,我們所有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是拓荒,我們所有的現(xiàn)代作家注定只是篳路藍(lán)縷的拓荒者。
《無風(fēng)之樹》的第一人稱敘事用口語的形式無形之中突破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語言困境,捅破了中國人生活意象和書面語言表達(dá)之間的隔膜,這種語言和意象的水乳交融狀態(tài)使作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從原來高度控制井然有序的書面敘述,到自由自在錯(cuò)雜紛呈的口語展現(xiàn)的轉(zhuǎn)變中,我體會(huì)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豐富。”③模擬人物的口語,而這些人物又是幾乎未受到現(xiàn)代文化沾染的鄉(xiāng)土中國里的農(nóng)民,他們的語言是他們生活的原生產(chǎn)物,這就使小說語言和生活意象完全統(tǒng)一起來。為了實(shí)現(xiàn)整個(gè)敘事的口語化,作者找到了一種獨(dú)特的敘事方式,我們把它稱為“立體敘事”。這種敘事的特點(diǎn)是:A在B的第一人稱敘事中是被敘述的對象,此時(shí)呈現(xiàn)在他者視域里的外部表象,當(dāng)轉(zhuǎn)換到A的第一人稱敘事中,在前面敘述過的外部表象得到里內(nèi)部動(dòng)機(jī)的重新詮釋,這不是次數(shù)上的重復(fù)描寫,而是內(nèi)涵的深化,使一個(gè)人類行為的展示立體化。與繪畫上的立體主義比較而言,時(shí)間藝術(shù)的文學(xué)顯然比空間藝術(shù)的繪畫有著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繪畫的空間是有限的,一個(gè)側(cè)面的表現(xiàn)必然搶占了正面的空間;而文學(xué)的時(shí)間是無限的,可以多角度多層面重復(fù)展現(xiàn)。但是這種敘事方式的缺點(diǎn)也是無庸諱言的:敘述速度遲緩。這種敘述方式?jīng)]有能力敘述史詩性的內(nèi)容,不可能容納下宏大的社會(huì)圖景和跨度很大的故事框架,它只能集中敘述某一個(gè)事件或是某一個(gè)場面,在敘述這個(gè)事件或場面的過程中它可以外延一些前因后果,把信息量擴(kuò)大,但只能是點(diǎn)到為止,我們無法想象用這種立體敘事的方式去講述像《紅樓夢》那樣的一個(gè)故事,——那將是一個(gè)漫漫無期的災(zāi)難。
這部小說所要講述的歷史話題,在文本中呈現(xiàn)為兩種語言的斗爭,而這個(gè)斗爭的過程和結(jié)果異常深刻地揭示了文革的真實(shí)面相,嚴(yán)酷的歷史現(xiàn)實(shí)竟表現(xiàn)為語言的分歧,這是讓我們感到十分驚訝的一個(gè)看法。這使我們想起了海德格爾的一句話:“因?yàn)檎Z言的命運(yùn)根植于一個(gè)民族對存在的關(guān)聯(lián)中,所以,在我們看來,追問存在的問題與追問語言的問題在最深處交織。”④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借用作者闡釋小說主題的“巨人”和“矮人”的說法,把這兩種互相斗爭的語言稱為“巨人語言”和“矮人語言”,這是一種象征式的表達(dá),其實(shí)就是官方或?qū)W術(shù)話語和老百姓話語。巨人語言主要表現(xiàn)為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特點(diǎn)是其異域性,即與生活現(xiàn)實(shí)的完全悖離;矮人語言主要表現(xiàn)為日常口語,特點(diǎn)是原生性,即與生活現(xiàn)實(shí)的水乳交融。巨人語言借助國家機(jī)器(暴力)實(shí)現(xiàn)了對矮人語言的統(tǒng)治。但是矮人語言的價(jià)值自圓性于無形中自動(dòng)消解了巨人語言的統(tǒng)治,使之流于物質(zhì)的、形式的,而不能觸及矮人的精神世界。官方或?qū)W術(shù)話語之所以在老百姓的價(jià)值觀念層面上失效,原因在于它與老百姓的生活現(xiàn)實(shí)的悖離。這個(gè)觀點(diǎn)不僅勾畫出了文革這個(gè)特殊歷史時(shí)期里中國人的真實(shí)生存樣態(tài),而且在解釋中國社會(huì)廟堂文化和草根文化長期分裂的現(xiàn)象時(shí)也是有效的。
在第一人稱敘事的日常口語的書寫中,作者感到了“體會(huì)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豐富”,這不僅是因?yàn)榭谡Z能生動(dòng)貼切地表達(dá)出生活意象,更重要的是因?yàn)檫@種原生性語言傳達(dá)出來的價(jià)值自圓性帶來的道德感。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的分裂,其實(shí)質(zhì)是價(jià)值的分裂。敘述語言滲透著作為現(xiàn)代人的作者的價(jià)值感,這種價(jià)值感有時(shí)是自覺的,更多的時(shí)候是不自覺的,它滲透在詞匯、語法、意象各個(gè)層面,它其實(shí)也是一種“巨人語言”,敘事對象在這種語言的表述中自然會(huì)被價(jià)值過濾。這種現(xiàn)象彌漫在整個(g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說到底,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是用現(xiàn)代性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國社會(huì)。但是這種現(xiàn)代性的價(jià)值在一個(gè)半世紀(jì)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并沒有成形,形成穩(wěn)定的中國自圓性價(jià)值體系。它身份可疑,一直都處在一種猶豫徘徊的狀態(tài)。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普遍道德感軟弱的根本原因,因?yàn)榈赖赂衼碜詧?jiān)定的價(jià)值觀念。道德感缺乏導(dǎo)致了文學(xué)的詩意的枯涸,就整體而言,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缺乏詩意是一個(gè)不爭的事實(shí)。廣而言之,其實(shí),這是世界范圍的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在中國的一個(gè)縮影,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德蛻化已經(jīng)使人類的藝術(shù)除了復(fù)雜的技巧、豐富的表現(xiàn)力而外毫無詩意可言。康德的名言:“世界上唯有兩件事使我們的靈魂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心頭崇高的道德法則。”作者的理解是:沒有心頭崇高的道德法則,仰望星空,我們的靈魂不會(huì)被感動(dòng)。沒有道德的沐浴,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展現(xiàn)的必然是一個(gè)俗艷的精神荒原景象。
《無風(fēng)之樹》的第一人稱口語表達(dá),一定程度上逃脫了作者的現(xiàn)代性價(jià)值過濾,還原了敘述對象的原生形態(tài),使它的自圓性價(jià)值得到較為完整的呈現(xiàn)。這個(gè)自圓性價(jià)值的獨(dú)立和穩(wěn)定不僅使矮人們的行為具有了道德意義,而且使作者也獲得了道德感。為了獲得這種價(jià)值的自圓性,作者必須把矮人坪置于一個(gè)極其荒僻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局限在一個(gè)封閉的敘事框架內(nèi),它就象是現(xiàn)代文明的海洋里的一座孤島。但是在現(xiàn)實(shí)中,這樣一種鄉(xiāng)土社會(huì)是理想化的,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的深入,特別是現(xiàn)代傳媒在農(nóng)村的普及、農(nóng)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鄉(xiāng)土社會(huì)正在分崩離析。這就使這本小說更象是寓言,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的那樣:“《無風(fēng)之樹》寫了三個(gè)月,是我下筆最快的一部作品,講的就是文革,把文革寫成一個(gè)寓言,一場巨人與矮人的故事。歷史總是巨人們高高在上地指導(dǎo)矮人們的歷史,可又總是給矮人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zāi)難。”⑤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圖景中,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價(jià)值觀念保持了相對的獨(dú)立和穩(wěn)定,所以鄉(xiāng)土社會(huì)相較其他的社會(huì)形態(tài)表現(xiàn)出更多的道德感,盡管也許這種道德簡單樸素,甚至愚昧。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第三人稱敘事中,被敘述的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道德經(jīng)過作者分裂的價(jià)值觀念過濾,被弱化、扭曲,但是在第一人稱敘事中,情況得到糾正。在《無風(fēng)之樹》中,矮人們(草根階層)的生活意象和價(jià)值觀念得到了酣暢淋漓的表達(dá),表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道德感,作者被人物語言牽引,不由自主沉浸在道德的莊嚴(yán)和詩意中,所以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豐富”。
但是時(shí)代決定了作者不能解決自身的價(jià)值分裂和混亂,所以這種道德感是曇花一現(xiàn)的,而且我們所有的敘事不可能都采用第一人稱,所以不論從語言形式還是從語言內(nèi)在的價(jià)值基礎(chǔ)而言,《無風(fēng)之樹》的語言彌合的現(xiàn)象都必然是暫時(shí)性的、個(gè)案性的。
注釋:
①本文中的“現(xiàn)代文學(xué)”一詞,指的是從一般所謂“近代文學(xué)”直到“當(dāng)代文學(xué)”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國文學(xué)。本文所論述的問題呈現(xiàn)出來的歷史連續(xù)性,足以提供一個(gè)個(gè)案佐證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在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概念的合理性。
②余華.《余華小說精品·自序》,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6月版,第5頁。
③李銳.《無風(fēng)之樹·后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65頁。
④Hei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