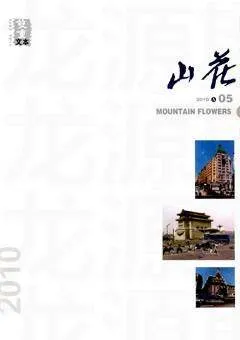屋溪河以北(二章)
小鎮上的圣誕老人
很多時候,我都在幻想小豬伢是我的父親,這種想法,在每次給父親打過電話之后,尤其強烈。小豬伢在我們鎮上可是個名人,他的真名叫什么,沒有幾個人記得了。一般來說,大家都把他當成反面教材,如果小男孩不聽話,大人就會說,如果你再不聽話,我就把你送給小豬伢焐腳。如果是小女孩不聽話,就會說,如果你再攪糊漿,就把你拿去給小豬伢當老婆。一聽這話,小孩立刻就變乖了。但我是個例外,我特別羨慕小豬伢的生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記得那會兒,小豬伢應該有四十歲了,他的個子很矮,皮膚出奇的白,即使放到鄉政府里和那些整天不曬太陽的女干部比起來,都毫不遜色。只是,他的衣服從來就沒有合身過,袖子老長老長,像是唱戲的一樣,但他的衣服,都挺干凈,據說,這些衣服都是人家送給他的,他從來就不洗衣服,只要臟了,他就毫不猶豫地將它扔了。小豬伢還有很多過人之處,據說,他吃過的碗,從來沒洗過,每次吃完飯,就舔干凈,然后倒扣在桌子上,以備下次再用。他洗臉也是很有技術,他起床后,就來到孫呆子的開水店,孫呆子揭鍋蓋的時候,他就把臉蹭上去,讓水蒸氣將臉打濕,然后,用袖子一抹,就大功告成了。一年四季,他都穿著一雙拖鞋,晃著羅圈腿,背著手,在街上無所事事地晃悠,仿佛從來就不知道什么叫憂愁,整天笑瞇瞇的,臉上泛著一層柔和的微光。
小豬伢的住處很小,是由石棉瓦搭起來的,就在我們上學的路上。每次遇到他,他都會從口袋里掏出一點東西,比如花生、水果糖或者一個小桔子。我一邊吃,一邊還會跟他提要求,因為他有求必應。我記得最多的是跟他要錢,我會說,小豬伢,給我五毛錢吧。他會一本正經地說,要錢干什么?而我們則會隨便編一個理由糊弄他,比如說,明天去春游,老師要讓我們買練習本之類的。然后,他就認真地搜著自己的口袋,然后擺了擺手說,今天忘了帶,明天給。我們便說,你說話要算話,不然就是小狗。他則笑瞇瞇地說,我是大人,說話當然算話。可是,第二天,我們就把這件事忘得一干二凈了。有一段時間,鎮上傳言有外地人來剝人皮,說是在頭上劃一條口子,把水銀倒進去,皮自然就脫落了。我和另一個同學一心想當英雄,各拿了一條拴狗的鐵鏈子,在大街上晃悠,想把那個壞人找出來。見到小豬伢,我忙問,你有沒有見到那個剝人皮的人?小豬伢說,你找他有事嘛?我像李小龍一樣摸了摸鼻子說,我要把他抓起來,送到派出所去。小豬伢笑了,說,你放心,我一見到有可疑的人,就跟你們報告。我像電影里的人那樣,拍了拍他的肩膀說,辛苦你了。然后,繼續漫無目的地尋找起來。記得還有一次,我被高年級的同學欺侮了。放學時見到他,就會說,小豬伢,某某今天打了我一個耳光,下午,你幫我揍他一頓。小豬伢依然笑瞇瞇地,沒問題,包在我身上,他打你一個耳光,我幫你打他五個。我說,五個不夠,起碼十個。他說,十個就十個,要不要吊起來打?我咬牙切齒地說,要。聽他這么一說,我們心里的氣也就消了一大半,雖然,他或許根本就不認識打我的那個人。
聽母親說,小豬伢原本的家境是很不錯的,只是在他父母離世后,家里就亂套了。小豬伢的父母死之前,辦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給他娶親,娶的是鄰村的一個寡婦,皮膚黑黑的,個子高高的,身子壯壯的,干起活來很利索。女人能干了,自然就把男人養懶了。每天一早,女人一大早就起床,弄好了早飯,去兩里地以外的煙山上割茅柴,回到家的時候,小豬伢還沒有起床。她去叫他,他就裝病,今天說頭暈,明天說肚子疼,反正,如果女人不煮好午飯,他是不愿意起床的。小豬伢的脾氣很差,他還很喜歡打女人,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聽到女人跟隔壁的光棍有說有笑,氣得不行。女人提著水進屋的時候,他掄起就是一扁擔,正好打在她的眼睛上,血一下子就涌了出來,他還不泄氣,又掄起扁擔,打得女人在地上亂滾,打完之后,他扔下扁擔,上了床,繼續睡起了覺。村里的一些閑婦聞聲趕來,女人愛面子,聽到動靜,趕緊從地上爬起來,洗了個臉,將頭發散落下來,遮住眼睛,做起飯來。那些滿心好奇的人,看到好戲已經散場,一個個失落地走開了。女人跟了他三年,這三年,他沒有下過一次地,沒有做過一次飯。
女人決定離開他是在那年冬天,那年冬天可真叫冷,屋檐下掛了長長的冰凌,池塘里結了一尺厚的冰,衣服只要晾上幾分鐘,就像鐵塊一樣堅硬了。那天夜里,風很大,像獅子一樣怒吼。女人聽到有人在撬門,伴隨著斷斷續續的說話聲,接著聽到了輕微的腳步聲,她警覺起來,推了推小豬伢,壓低了聲音說,好像有人在偷我們家的東西。小豬伢一動也不動,咂了咂嘴說了一句,神經病,這么冷的天,哪個小偷愿意出來偷東西。女人很想起來,但是她膽子小,連出氣都不敢大聲。十幾分鐘后,屋子里漸漸寂靜了下來,女人披衣起來,才發現小偷已經將今年收的稻子全部搬走了。她驚叫著告訴小豬伢,不好了,不好了,家里遭賊了。小豬伢一動不動,她邊搖著他邊說,快起來,快起來,家里遭賊了。誰知道小豬伢連打了三個呵欠說,老子要睡覺,就是天要塌下來,也得明天再說!女人覺得這日子沒法過,哭哭啼啼地收了衣服,就準備回娘家,小豬伢一言不發,出門時,他說一句,把門關上。這也是他對女人說的最后一句話。最后,母親嘆息地說,小豬伢不知道,女人這時候已經懷上了他的孩子。
女人走后,小豬伢還是有一絲后悔的,因為,從此之后,就沒有人服侍自己了。不過,他并沒有去干活,而是把主意盯在了自己的房子上,他開始賣房子上的木梁。先是廚房上邊的木梁,反正,女人走后,他也沒有開過火,接著是堂屋的木梁,最后,只剩下臥室了,這個時候,他還真的猶豫了一下,因為,他怕下雨的時候,淋到自己的床。能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他就厚著臉皮,到處去蹭飯,好心人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就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提一個籃子去賣些小食,比如瓜子、杏仁酥、麻餅之類的。冬天的時候,天氣很冷,他把手塞在袖管里,懶得伸出來,別人取了東西后,還要把錢塞到他的口袋里。到了晚上,一算賬,掙了一兩塊錢,就會去切點豬頭肉,打點酒,一邊聽著收音機,一邊喝。這樣,沒過多久,他的老本也吃光了,只能靠撿破爛為生了。
除夕夜,是小豬伢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了,他會拿著一只蛇皮袋在鎮上挨家挨戶地拜年,每到一家,都會說一些吉利的話,而主人家,也會給他一些團子,一些熟菜。每年,他都要裝上一蛇皮袋子,然后分給那些行動不便的孤寡老人。有一年,我回家過年。聽到有人敲門,開了門,見到了他,有些吃驚,他明顯地老了,頭發花白,一半臉被燒得黑乎乎的,另一半臉上布滿了老年斑。母親有些感傷地說,有一回,東破圩的一個老人家躺在床上抽煙。煙頭點燃了棉絮,并且迅速蔓延開來,火勢太大,老人的兩個兒子在外面看著,不敢進去,小豬伢正好經過,想都沒想,就沖了進去,把老人背了出來,左邊的臉被火舔了一下,就變成燒焦的山芋了。母親說話時,他有些不好意思,不停地搓著手。臨走時,我給了小豬伢半只風雞,他不停地道謝,又說了一大堆好話。看著他戴著狗皮帽子,背著鼓鼓的蛇皮袋子,在雪地上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我突然想到了圣誕老人。一晃,又快過去十年了,不知道他還在不在人世?
被遺忘的北街
每個小鎮都有一個神秘的部分,北街就是堰頭小鎮最神秘的部分。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北街開始荒蕪,原先的商鋪都搬到河對岸去了,雕花的窗欞拆下來了,孤苦無援的房子像乞討的瞎子,冰涼的臺階是他們伸出的無助的手,他們在陽光下坐著,日復一日,靜寂無聲,只是,有時候會有一只鳥從空洞的眼睛中飛出來……
北街的最后一家店鋪是孫呆子的開水店。孫呆子是一個老光棍,他坐在老虎灶上,看上去像皇帝一樣神氣,仿佛連嘴角的黑痣也在閃閃發光。他手邊的鋁盒里,裝滿了叮當作響的鎳幣,最多的是兩分的鎳幣,偶爾會有五分的,很多時候,我都想趁他不注意,抓一把就跑。他喜歡和寡婦們開玩笑,喜歡摸小孩的雞雞,還喜歡拿很臭的豆腐干下酒,特別是夏天,太陽還沒落山,他就迫不急待地從河里提一桶水澆在茶水店門口,青石板在滋滋聲中慢慢涼卻下來,他便擱一張靠背椅、一張方凳子喝起燒酒來。他很節約,一塊小小的豆腐干,就可以下半斤燒酒。我記得他總是穿著一條藍色的背心,背心上到處都是洞,仿佛是一張蜘蛛網。孫呆子是突然死掉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在喝酒,那天早上,打開水的人見他的門關著,便咒罵起來。他死后,盒子里的那些硬幣,讓我掛念了很久,每次經過時,都想從窗戶里鉆進去找,最后還是因為害怕作罷了。
一排一排的房子空了出來,很少有人居住,門鎖生銹了,房子倒坍了,院子里野草瘋長,一年勝過一年,終于可以沒過人的頭頂,孩子們不敢去那里玩,因為,有一個孩子曾在那里被一條扁擔長的蛇咬過。留在那里的,是一些孤獨的老人,空氣里彌漫著一種深邃的死亡氣味,暮春的雨后,墻根還會長出紅色的菌子。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孩子,對一切都充滿好奇,我不知道陽光會不會透過細長的窗欞,涌進屋子,而在那些漫長的,近乎折磨的下午,老人們是怎么度過的。
我記得,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冷棱從檐上倒掛下來,幾乎要碰到地上了。我穿得嚴嚴實實,但身子還是像一塊冰,我的嘴像是煙囪一般,邊走邊呼出熱氣。經過北街時,我看到一間房子,沒有門,里面鋪著陳年的稻草,透著濃重的霉爛氣息,光線昏暗,突然,我看到墻角有一團黑乎乎的東西動了一下——那是一個老太太,裹在一堆爛棉絮里,瑟瑟發抖。據說,老太太是個慰安婦,她結過兩次婚,但她的男人知道她的過去,都嫌她不干凈,離她而去了。有一年臘月,大雪漫過膝蓋,小鎮上來了一個小乞丐,衣衫單薄,快凍死了,她收養了他,省吃儉用,含辛茹苦,把他培養成了大學生,畢業后,他在上海工作,又在上海成了家,再也沒有回來。每到過年,老太太天天都要去汽車站,她的眼睛都望瞎了,還是沒有看到兒子回來。有一年,老太太家失火了,她連一床棉絮都沒有了,好心人給她寫了封信給兒子,很快,她兒子寄了五塊錢回來,但人始終沒有回來。
還有一位老太太,她是北街最神秘的部分,不知道多少年沒有人在白天見到她了,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連她的姓也不知道。據說,她總是后半夜出來活動,這個時候,小鎮早已進人了甜美的睡眠,月光清冷,如同簫聲中吹出來的音符。她就這樣走著,穿著年輕時的藍色旗袍,有一段時間,上夜班的人,都說看到了一只藍色的狐貍,當她們上前的時候,它已經消失不見了,那個人后來生了幾天的病,直到最后,才知道那不是狐貍,而是那個老太太。她為什么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呢?沒有人知道。也許是在緬懷著什么。她的家是舊式的宅子,門口有兩面石鼓,鐵皮門上釘著釘子,房子的主人姓胡,是一名中醫,這個女人是他的姨太太,她是從上海來的。不知道為什么,她一直沒有生育,大太太的兒子早搬出去住了,每到月初,他總是會把食物擱在門口。關于她的傳說很多,有一個聽起來,非常恐怖,說她的房子里有一千只老鼠,她并不睡在床上,而是睡在老鼠的背上。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下了幾天的雪終于停了,家家戶戶燈火通明,每一句話里都有一種明亮的、喜慶的氣息,而北街,黑暗、死寂,如同棺槨。我一個人走在北街,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突然,我聽到前面一陣響動,心臟迅速收縮成一團,接著,我聽到關門的聲音,原來,我已經來到了胡中醫家的老宅前。我想,剛才的聲響,肯定是那個老太太發出的。這會兒,宅子里一丁點聲音都沒有了,也許人老了,身體輕了,走路也沒有聲音了,像一片樹葉落在地上。這樣想著,便加快了步子,直到過了河,看到一片片彌漫著食物清香的燈光,我才松馳下來,一摸額頭,竟然已沁出了冷汗。
那個恐怖的夜晚已經過去快二十年了,我也離家多年,不知道現在的北街變成了什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