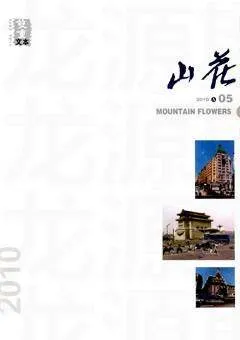撤退(短篇)
緊急撤退的命令是在四六年深秋下達的,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天早晨特別的冷。
列車一出山海關進入東北境內,上車就躺在軟臥車廂里的老父親一下坐了起來,用悠遠而略帶沙啞的聲音對我說。可他說話并不看我,兩眼望著窗外,兩道目光像兩條筆直發亮的鐵軌投向了無盡的遠方。那一瞬間,我好像有點明白了耄耋之年的父親去參加校慶,為什么不坐飛機,堅持坐火車。六十年那是多么漫長的歲月,多么厚重的一本書,飛機上的幾個小時來不及翻閱那本書,它需要時間慢慢地去解讀,去品味。隨著列車的漸行漸近,如煙的往事又歷歷在目,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開啟了塵封在心中半個多世紀的秘密。
那時我們部隊到東北接受日偽軍投降,還不到一年,蔣介石就撕毀停戰協議,大舉向東北進攻。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我們放棄了大中城市,向農村大踏步轉移,也就是撤退。這個階段后來的歷史書上叫什么時期來著?
是不是叫戰略防御期。我提醒了父親一句。
對!就是戰略防御期。猛地,父親止住了話題,陷入了深深的回憶之中。車廂里猝然靜了下來,只聽得見列車的車輪摩擦在鐵軌上的“唰唰”聲。好一會兒他才長長的嘆了口氣說,一撤退,建立不到一年的解放軍衛生學校就散了,原打算在那踏踏實實地學幾年本事,也落空了,還弄出以后那么多的事情來……
在父親的講述中,我頭一次聽說父親曾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吳燁。他告訴我那是抗日戰爭時在淪陷區做地下工作用的化名,全國解放后他才把名字改過來。那一刻,我突然涌起想了解父親的強烈沖動。父親的講述斷斷續續、支支離離,有些事情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好在校慶期間,我見到了父親的那些老戰友,白發蒼蒼的叔叔、阿姨們,向我講述了父親和他們當年許多的往事,彌補了父親那些不便于跟兒子言說的空白。幾十年來,我還是頭一次走進父親的內心世界里。
凌晨,緊急集合的哨聲把吳燁從睡夢中驚醒,嘈雜急促的哨聲和人們的喊聲交織在一起,此起彼伏,在校園的夜空上回蕩,在瑟瑟秋風中顫抖。吳燁像打在墻上反彈回來的子彈一樣,一下從炕上蹦了起來,憑經驗他覺得這不是學校搞訓練,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一邊穿衣服,一邊用腳踹睡在身旁的王尚明,對屋里的同學大聲喊道,緊急集合了,趕快起床。王尚明一臉的不高興,嘟囔著剛要說什么,一聽到屋外的哨聲和喊聲,他驚呆了,忙問,出什么事了。吳燁急促地說,別問,趕快,去操場。
操場上集合的同學們以班級為單位,按縱隊排列。吳燁他們班站在右邊第二排,第一排是衛校警衛班的戰士。只見校長面對他們站著,虎著一張臉,全無平時的和藹可親。過了一會兒,還有三三兩兩的人朝操場上跑來。吳燁借著冷月的光亮,發現原來四十來人的班級,只剩下不到二十人。校長繃著臉,嚴肅地對大家說,國民黨匪軍已經突破了我軍阻擊部隊的防線,朝我們這座城市壓來。上級命令我們衛生學校馬上隨分部機關朝北撤退。
王尚明用變聲期的公鴨嗓子喊道,報告。我們要撤多遠?
校長皺著眉頭不耐煩地說,不知道。
報告。我們撤到什么時候為止?一個女孩尖聲地問,那聲音里透著遭難般的觳觫。
不知道。校長焦躁地大聲喊道。
真他媽的,一幫新兵蛋子,全他媽的屬耗子的。黑暗中吳燁聽到警衛班的張排副低聲罵了句。他看見張排副仍像以往集合列隊那樣,不是站在警衛班的隊伍里,而是面對大家站在隊伍外,一副二首長的派頭。吳燁頂看不慣張排副顯擺的樣子,氣狠狠嘟嚷道,就你能耐。
父親對我說,張排副剛進城時,胳膊上挨了暗藏的日偽特務的黑槍,來衛校的醫院治療。當時警衛班缺人,他傷好后就留了下來,偶爾還給同學們代代軍事課。他是從胡子改編過來的,說起話來有駱駝不吹牛,滿口的零碎,一張嘴就帶臟字。他還有個要命的毛病,見到漂亮的女同學就邁不動步,眼珠子瞪得都要滾落出來了。
校長簡短的動員后,命令道,各班學員馬上回去打背包,五分鐘后集合,輕裝急行軍。
回到宿舍,吳燁趕快收拾東西,該拿的拿,該扔的扔,不一會兒就把背包打好了。王尚明卻緊張得手忙腳亂,不時地用衣袖擦著額頭上的汗珠。別看吳燁剛十九歲,比王尚明才大兩歲,可吳燁十三歲就投身革命,參加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參軍也已經三年,是個老戰士了。王尚明是衛校成立后才來的青年學生,滿打滿算入伍也就半年。
吳燁說,我幫你打背包吧。
王尚明伸手一攔,執拗地說,不用,我行,你先集合去,我一會兒就到。
吳燁見他態度那么堅決,猶豫了一下也就沒堅持,背起自己的背包走了。臨出門叮囑道,抓緊時間,不然就來不及了。
路過女生宿舍時,吳燁見屋門大敞四開,從屋里傳來一陣哭聲。他進屋一看,他們班的韋穎和另一個女同學正坐在炕沿上哭呢,行李還散亂地堆在炕上。這時吳燁不知哪來的一股火,大聲地吼著,哭,哭,都什么時候了,敵人馬上就要來了。倆人一下被嚇愣住了,立刻止住哭聲。韋穎還從沒見他發過脾氣,在她的印象里吳燁少言寡語,即使說起話來也是慢條斯理的。在學校里只要他們倆人單獨碰見,吳燁總是臉一紅,表情特別不自然,緊張、害羞、懼怕?好像是,又好像不全是,惹得她的臉也熱乎乎,挺不自在的。她說什么也沒有想到他會對自己這么大呼小叫的,她氣惱地翻陵了吳燁一眼,賭氣地扭過身,坐在炕沿上就是不動。吳燁還想再說什么,可一看韋穎的樣子又忍了回去,低下頭幫她們打起背包。站在一旁的女同學用手使勁拽了拽韋穎的衣后襟,她才起身收拾東西。吳燁打好了背包,對她倆說,趕快去集合,我去看看王尚明。
吳燁覺得王尚明今天有些反常,心里直犯嘀咕。平時搞訓練他挺麻利的,根本就不像今天這么笨手笨腳。往常王尚明有什么事總愛找他商量,讓他幫忙,可今天王尚明拒絕得那么毅然決然。聯想到這幾天隨著形勢一天一天的惡化,學校里的小布爾喬亞們一臉霜打的蔫樣,一下課就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傳播小道消息,接著三三兩兩地向學校請假,有說家里有事,有說父母病重,有說上街買點東西,然后就一去不回頭。沒幾天就跑了快一半了,他擔心王尚明一時糊涂干出傻事來。
他飛快地朝宿舍跑去,遠遠地聽到宿舍的門被陣陣秋風狠狠地摔打著,撞在門框上,在黑暗中發出孤寂的聲響。屋里一個打好的背包扔在炕上,卻不見王尚明的人影。他拎起炕上的背包在宿舍的四周找了一遍,還到廁所看了看,都沒找到。突然,他想起王尚明會不會到教室拿書去。他趕忙跑到教室,推開門,屋里黑乎乎的沒有一個人,他不甘心地喊了兩聲。就在他走出屋隨手關門的時候,不經意間的一回頭,一束月光投照在講臺的中央,把地上散亂的教具照得清晰可辨。他還記得那個講臺原本是四根木棍支著一塊灰不唧唧木板的破桌子,是老師找來一塊灰軍布,順著桌腿圍了一圈,使那桌子莊重了不少,有個講臺的模樣了。那些圓規、三角尺、直尺一干教具上完課就放在布圍子里。今天他值日,是他把那些教具放到布圍子里面的,這會兒怎么被弄到外面來了?他走到講臺旁,蹊蹺地打量著散亂的教具。突然,他發現講臺的布圍子,像一個發燒的病人瑟瑟發抖,他立刻明白了。“砰”地一聲,他一拳狠狠砸在講臺上,大聲地喊道,滾出來,你給我滾出來!
好一會兒,王尚明才從講臺的布圍子里哆哆嗦嗦爬出來。吳燁一把揪住他的胸襟說,你想投敵叛變?
王尚明嚇得聲音都變了,一副哭腔,冤枉,冤枉,我沒想叛變,沒有,我發誓。我就是害怕,我,我想回家。
吳燁一聽他沒打算投敵叛變,語氣就緩和下來,他說,想當逃兵,你以為逃回家就沒事了?敵人回來了,知道你參加過解放軍,能饒過你嗎?見王尚明低著頭不說話,吳燁就把手上拎著的背包扔給他,順勢推了他一把,說,趕快集合去吧。王尚明怯怯地瞟了吳燁一眼,抽噎著說,我不敢。吳燁一愣,馬上又明白了,他說,你只要今后不再動搖,今天的事我對誰也不說,我保證。
王尚明一聽竟像個孩子似的“嗚嗚”地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發誓,我再也不動搖了。
衛校隨著撤退的隊伍開始了急行軍,不少同學還是頭一次走得這么急,汗水浸濕了衣服的領子,晨風把汗吹干,在衣領上留下一道道白白的汗堿,但不一會兒干了的汗跡上又出現了汗水。當衛校的學員全都登上了饅頭山,已經累得兩腿拉不開栓,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學校只得命令原地休息十分鐘。這時天已經大亮了,吳燁倚著一棵老松樹休息了一會兒就站起身來,呆呆地眺望剛剛撤離的城市,整座城市就像個困倦的孩子,裹著籠罩在空中的薄霧般的輕紗酣然大睡,全不知大難lI缶頭。晨曦中衛校的鐘樓還高高地矗立在那里,可它已不再屬于他們了,或許今天下午就成了敵人的兵營。形勢變化得真快,去年的秋天他跟隨山東軍區的同志們奔赴東北接受日偽軍的投降,他們的學校也就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當時學校里除了他們四十幾個從部隊抽調來的學員外,其余的全是當地的青年學生。那時的校園里充滿了笑聲歌聲,同學們大聲地談論著理想,談論著未來,白大褂,無影燈下,人道主義……可這些美好的愿望幾乎就在一夜間化為泡影。
突然,吳燁聽到身后傳來抽噎聲,他回頭一看韋穎站在身后,含著眼淚,一臉絕望地輕聲問他,完了,我們是不是完了?吳燁不高興地皺了一下眉頭,想狠狠說她幾句,可一看她眼淚汪汪的,尤其是她那哀憐求助的眼神,心又軟了下來。他想一個資本家的闊小姐能脫離家庭參加革命已經不易了,她是插班生,入學還不到半年,對她的覺悟不能要求得太高。他轉過身對大家說,打仗難免有進有退,抗日那會兒,有一次反掃蕩,我們讓鬼子追著一口氣跑了一百二十里地,我兩條腿都跑直了,要不是兩個戰士架著我,我早就掉隊了。等沖出包圍圈,我的兩只鞋不知什么時候跑丟了,兩腳血糊糊的,可是小鬼子到底還是讓咱們打敗了。說著他用眼睛瞥了韋穎一眼,想用堅定的眼神鼓勵她,不想韋穎一陣慌亂,眼睛里全是茫然、失望的神情,逃避似的趕忙低下了頭。像流行感冒一樣,吳燁的心也一陣亂跳,把原來已經想好還要說的話全忘了。
形勢越來越嚴峻,衛校跟著分部機關向北撤退三天了,敵人卻越追越近,他們已依稀聽得到敵人的炮聲。那幾天晚上每在老鄉家里住宿一次,1BmxjN4F8Fsa2ZQ+MTMCGgJiZ7Hj3Y6Zm2UEm6LGeYQ=早晨集合出發時準又少了幾個人,他們肯定是在夜里偷偷逃走的。眼看著班里的同學越來越少,吳燁心里特別著急,在第二天行軍的路上,他秘密地召開了黨小組會。父親告訴我,當時的黨組織是保密的,即使在革命隊伍里也不公開活動。會上他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每個黨員都看住一個有動搖傾向的同學。決不能讓他們當逃兵。黨員不夠就動員立場堅定的同學參加。
那天晚上隊伍路過一個縣城,在一個叫張家堡子的村莊里住下。吳燁幫助協理員把班里的同學們分散到老鄉家住下,為了防備敵人突然包圍村子,他把抗日時期反掃蕩的經驗教給了大家,他讓每個同學都認真地了解一遍房東家的情況,還認了房東的大叔大嬸作了爹媽。當把同學們都安頓以后,吳燁把王尚明悄悄地叫到屋外,一臉嚴肅地說,今天我們開了個黨員會,認為你表現得堅定,現在黨組織交給你一項重要的任務。
黨員會?我怎么不知道。我還不是黨員嗎?王尚明瞪著一雙驚訝的眼睛不解地問。
現在還不是,你只要努力今后可以是。吳燁鼓勵著王尚明,接著又說,我們班有幾個同學是這個縣的人,家離我們的駐地不遠,為防止意外,組織上派你盯住一個,不許他離開駐地。你明白嗎?
王尚明先是一愣,馬上又認真地點了點頭,他為這任務的重要而有些緊張,為得到黨的信任而感到激動,臉上洋溢著自豪又崇高的莊重。突然,他像想起什么問道,如果他要跑怎么辦?
死活也要把他勸住。吳燁毫不猶豫地說。
他就是不聽怎么辦?
吳燁一下被問住了。他真沒仔細地想過這個問題。遲疑了一會兒,他猛地一揮手,毅然決然地說,要是那樣,你就把他打傷,讓他跑不了。
這……行嗎?王尚明膽怯了。
見王尚明有些害怕,他開導地說,把他打傷了,我們還可以背著他撤退。如果他當了逃兵讓敵人抓去,不是叛變就是死。
王尚明信服地說,行!我聽你的。
吳燁見一切都安排妥當,就獨自往自己的住處走去,可是不知怎的,他竟鬼使神差走到韋穎住的地方。油燈的光亮把韋穎身影剪紙般地投照在窗戶紙上,就像皮影戲里的影人。他不禁又想起撤退的當天早上,她望著自己的那種哀憐求助的眼神,不知為什么,他既眷戀又害怕她的目光,那目光常常帶給他朦朧卻美好的想象,那目光也常常攪得他的心一陣一陣地亂跳。
記得第一次見到韋穎是在校長的辦公室。她見了他,一臉矜持地點了點頭,然后眼睛望著別處。很隨意地說了句,我叫韋穎。吳燁不在意地笑了笑,當他禮貌地說出自己的名字時,她好奇地望著他問,你是哪個ve啊?
他說,一個“火”字旁,加一個中華的“華”。
燁——光輝燦爛的火光。這名字挺好。說完她非常得意地笑了,不知是為了名字好,還是為了她能欣賞這好名字。
校長說,吳燁出身書香門第,是我們隊伍里多才多藝的大秀才,鬼子占領了他的家鄉,他就參加了革命,是經過考驗的老戰士了。
韋穎聽了一愣,用驚訝的目光重新審視起吳燁,一身灰了巴嘰的衣服,一雙農村納底布鞋,土得直掉渣,不是鄉下扛活的,至多也就是她們家雇的伙計。她怎么也不能把眼前這個不比自己大幾歲的人和少爺、秀才、老戰士這些相互對立的概念聯系在一起。頃刻,她眼睛里沒有了高傲和矜持,一絲自卑的眼神稍縱即逝,她有些懊悔地低下頭。可只一瞬間,她又把頭抬了起來,一雙哀憐求助的眼神里透著純潔和真摯,有些膽怯地紅著臉說,我剛來,什么都不懂,你多幫助我。
吳燁一陣慌亂,臉“騰”地一熱,就像喝了酒脹乎乎,燒乎乎的,他不知所措地急忙點了點頭,又趕緊搖了搖頭。在同學里,韋穎對吳燁比別的同學更多了幾分尊重。后來發生的一件事又拉近了倆人的關系。那天下午,吳燁下課回宿舍,遠遠地他看到站在女生宿舍拐角的張排副嘻嘻哈哈地和韋穎說著什么,還沒走到跟前就聞見張排副身上濃烈的酒味,走近一看韋穎臊得滿臉通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張排副甜膩膩的聲音,讓人聽了直起雞皮疙瘩,邊說邊要拉韋穎的手,嚇得她像個小雞似的縮成了一團。見到吳燁走過來,她趕緊躲在吳燁的身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她雙手緊緊抱住他的胳膊。吳燁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一把揪住張排副,張排副借著酒勁抬手一拳打在吳燁的臉上,血當即就從嘴角流了出來。吳燁一個背摔把張排副按在地上,說要拉他去見校長。張排副的酒這才被嚇醒,他掙開吳燁,從地上爬起來,灰溜溜地走了。張排副已經走得沒影了,可韋穎眼睛仍然呆呆望著吳燁。好一會兒,她才像意識到什么,趕忙從口袋里拿出手絹遞給他。當倆人四目相對時,韋穎的臉紅了,吳燁的臉也紅了。從那以后,吳燁在班里總感到有一雙眼睛在看著他,不經意地一轉頭,韋穎的目光就和他絞纏在一起,他的心總會一陣慌亂。
借著夜空炮彈劃過的光亮,吳燁進了屋,看了看韋穎,又叮囑了她要注意的事。當他離開的時侯,韋穎從口袋里掏一塊用手絹包著的干糧,硬塞到他手里,還把一支自來水金筆送給他。他想推辭,韋穎的眼淚流了下來。他急忙說,別哭,別哭,我收下,我收下。他覺得應該說點什么,可他不知該說啥。隱約的他感到韋穎的情緒有些異常,可又沒有發現什么,站了一會兒他走了。
半夜,一陣劇烈的槍炮聲把吳燁從睡夢中驚醒,他趕緊朝指定的集合地點跑去。沒跑多遠他想起了韋穎,又轉身往她住的地方跑。半路上碰到了王尚明和那個被他盯著的同學,王尚明會意地向他點了點頭。他們跑到了韋穎的住處,只見院門大敞四開,屋里韋穎那根本沒打開的背包還扔在炕上,卻不見她的人影。幾個人跑出屋朝四下大聲喊著她的名字,他們的喊聲被夜晚的漆黑和越來越激烈的槍炮聲吞噬。
喊聲驚動了房東的大嬸,她從屋里出來對他們說,剛才俺們在屋里聽見有人來找你們的小同志,小同志跟來的人叫表哥。倆人站在院子說了好一陣,我還聽到那閨女哭了。后來倆人朝院子外走了,俺們還以為他倆到隊伍上去了。
吳燁他們幾個互相望了望。她逃了?吳燁的話一出口,自己嚇了一跳,其他幾個人也一愣。突然,王尚明指著通向村外的大街說,他們在那。吳燁朝村口望去,一男一女剛跑出村子,正往村邊的小樹叢里跑。他毫不遲疑的舉起了卡賓槍,瞄向了倆人。
月亮正迎著兩個逃跑的人懸垂在天際,一輪明亮的滿月閃著熠熠的銀輝,照得大地一片光亮,反而襯得倆人的背影更黑更暗。卡賓槍瞄準了女人的腿。可槍并沒有響。槍口又對準了女人的后背,卻顫巍巍地又猶豫了。當卡賓槍的準星最后定在女人的頭上時,吳燁的心一顫,端著槍的兩只手不禁顫抖起來。他一咬牙,用力扣動扳機,隨著一串脆響,夜晚的天空劃出一道美麗的弧光。
張排副集合經過這里,當他看見吳燁端著槍,明白是怎么回事時,槍已經響了。他看見隨著槍聲,兩個人倒了下去。張排副像瘋了一樣,沖過來一拳把吳燁打倒在地上,用劈裂的嗓子罵著,操你個奶奶的,你他媽的心都讓狗吃了。吳燁慢慢地從地上爬了起來,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的血,沒有理會張排副,傻子似的呆呆望著前方。他猛地揚起脖子,沖著夜空,扯心裂肺地喊道,混蛋,——
我曾在參加完校慶回來的列車上,向父親問起過韋穎。父親當時一愣,竟像姑娘似的靦腆地笑了笑。半天沒說話,一臉的沉思,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之后,就像我不是在問他似的,扭過臉呆呆地望著車窗外,好半天才說,她完了。做人是有底線的,那底線決不能突破。就像人站在懸崖邊,只要向后退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人就整個毀滅了。
我問父親,你后來沒有再想起她?
父親望著我,過了一會兒說,起初還想過她,但不像現在的年輕人要死要活的。他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對她我是又生氣又可憐,就像你小時候調皮,把胳膊摔斷了,我生氣還心疼一樣。但不知為啥,我不恨她,有一陣我還恨自己為什么就恨不起她來。戰爭年代里生死離別的事多了,沒多久我就差不多把她忘了。要不是后來發生的事,我或許都不記得這世界上還曾有過她這么個人。
不久,在撤退的途中衛校解散了,學員們被充實到戰斗部隊里當衛生員。后來部隊和國民黨打了一仗,那是一場惡戰,整整打了兩天兩夜。那天,師衛生隊隊長把吳燁找來,一臉嚴肅地說,剛接到緊急命令,讓我們馬上把重傷員撤到后方的分部醫院,你帶著醫護人員用專列把傷員運走。讓張排副帶兩個班隨車護送,歸你指揮。三百四十一個傷員就全交給你了,務必安全送到。
院長的表情和突如其來的緊急命令,讓吳燁的心陡然一緊。盡管他不知道戰場上發生了什么,但他意識到勢態的嚴峻。一個小時后,吳燁帶著專列出發了。
列車第一天行駛得很順利,到了指定的車站,專列一停靠站臺,就有鐵路工人進行例行檢查,該加水的加水,該上煤的上煤。臨時改裝的專列沒有餐車,車上人的吃喝,全是從車站送上來。早中晚吃飯的時候,當地婦女還上車幫助護理人員給傷員們喂水喂飯,端屎倒尿。可是第二天早晨情況就變了。列車到了指定的車站沒人加水上煤,也沒人給車上送吃喝,吳燁正要下車問問情況,車站調度室就急急慌慌地下達了開車的指令。
中午專列停靠在預先安排的車站,可半天也沒見到一個人。這時天上飛來一架敵機,沖著專列投下幾顆炸彈就匆匆地飛走了。吳燁趕忙領著王尚明找到了車站調度室,屋里一片狼籍,紙片扔了滿地,屋里的柜子、抽屜被翻得亂七八糟,吳燁的心一下揪了起來。這時負責護送的張排副領著幾個戰士也跑了過來。
王尚明神情緊張地說,敵人已經占領這里,我們不能再往前走了。
張排副鼻子“哼”了一聲,用眼角剜了王尚明一眼說,別他媽的扯蛋,打過仗嗎?哪有飛機打自己的列車,往自己陣地扔炸彈的。他那趾高氣揚的樣子就像教訓個新兵蛋子。
吳燁皺了下眉頭,對張排副他有說不出的反感,又瘦又矮的身子頂著一張絲瓜臉,一臉的絡腮胡子把本不寬的臉擠得更窄了。更難看的是臉上的那道刀疤,從腦門正中一直劃到右耳朵根,有人說那是小鬼子砍的,也有人說是當胡子時,為爭一個女人和別人動刀子留下的。改編后他仍改不了一身的匪氣,因違反紀律幾次被降職。討厭歸討厭,但吳燁還是覺得張排副說得有幾分道理。他不耐煩地說,別吵了。你們說現在是進還是退?這一問把張排副問住了。屋里的人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也不吭聲。
突然,敵機又飛來了,俯沖著朝專列來回掃射,臨飛走時又扔下幾顆炸彈。掃射沒讓專列受什么大損失,只是幾顆炸彈把列車尾端的鐵路炸壞了好幾十米。看著炸毀的鐵路吳燁下了決心,退是退不回去了,原地不動肯定是死,向前沖或許還有生的希望。他果斷地對司機說。向前,全速前進。他對全體人員說,各就各位,做好戰斗準備。
列車大吼一聲,向前奔馳而去。沿途他們看到了不少逃難的老百姓。下午兩點多鐘,列車拐出一個山坳,一條公路與鐵路并行著,眼前頓時一片開闊。突然,飛速前進的列車發出了刺耳的剎車聲,龐大的身軀猛地抖動了幾下,戛然停了下來。司機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過來對吳燁說,不好了,前面的大橋被炸斷了。吳燁一聽急了,趕忙朝車頭跑去。二百來米寬的靈漳河橫亙在眼前,前幾天的一場寒流在河邊上掛了一層薄薄的冰渣,河上的鐵路大橋已被炸成了三截。他頓時傻了眼。空中又傳來了敵機的響聲,他趕忙對司機說,把車向后退,別當敵機的靶子。司機剛一上機車,敵機就俯沖下來,沖著車頭一通狂轟亂炸,車頭被打中了,它像一個受了重傷的戰士,發出了幾聲沉悶而悲壯的長鳴,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頑強地掙扎著轉動了兩下車輪,然后就臥在軌道上再也不動了。
吳燁立刻派人找當地的老鄉了解情況。很快派出去的同志回來告訴他,今天早晨鄉政府和村干部剛轉移到河對岸。他馬上意識到,這里還沒被敵人占領,但是情況很危急,必須趕快撤離這個地方。他命令王尚明立即過河去,聯系當地人民政府,請求他們支援。同時他命令張排副派一個班的戰士到一里多外的西邊山頭擔任警戒,他發現那山頭是這一片的制高點,是扼守鐵路和公路的有利地形。
一個小時過去了,派過河去的王尚明仍沒有回來,河對岸也不見一個人影。急得吳燁在河邊上來回的走著,不時地望著河對岸。
父親告訴我,戰爭年代里,成天在槍林彈雨里摸爬滾打,不知道啥叫怕,可那次他真的害怕了。三百四十一個生命全掌握在他的手里,敵人馬上就要來了,可傷員們走不能走,動不能動。
身后一陣劇烈的爆炸聲讓他吃了一驚,扭身一看,西邊的山頭打響了,他趕忙向回跑。遠遠的他就聽到那個剛從西邊的山頭回來的戰士大聲地對張排副說,敵人的先頭部隊上來了。
有多少人?張排副著急的問。
二百來人。敵人的大部隊離我們還有二十多里地,正朝這開來。
戰士們一聽慌了,圍著張排副問,怎么辦?
張排副沉思了一下,朝列車瞄了眼,把手一揮,撤!戰士們略一猶豫,跟著張排副向路基下跑去。
站住!站住!吳燁大聲地喊道,有人扭頭看了他一眼,就像沒聽見似的。情急之下,他拔出腰間的駁殼槍朝空中連放了幾槍。奔跑的人們猛地停住了腳步,吳燁趁機沖了上去,一把揪住張排副的衣領,用槍頂住他的后腦勺說,你敢臨陣逃跑。
老子不想在這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的等死,不想讓弟兄們讓國民黨包了餃子。
列車上的三百多個傷員怎么辦?
張排副不耐煩地一揮手說,老子管不了那么多,少死一個是一個,總比全死了強。吳燁被噎一愣。張排副乘機一個轉身,右手向后一伸,抓住倒背著的卡賓槍的槍管往胸前一擰,眨眼的工夫,槍就握在他的手上。嘩啦一聲,槍栓拉開了,又推了上去。隨著槍栓發出冰涼、堅硬的金屬撞擊聲,兩把子彈上了鏜的槍口都頂住了對方。
西邊山頭剛剛停下來的槍聲,又猛烈地響了起來。
你敢逃跑,我就斃了你。吳燁眼睛噴著兇狠的火焰,可握著槍的手卻濕漉漉的全是冷汗。
張排副歪著頭瞥了吳燁一眼,把頂在腦門上的槍口輕輕用手一撥說,你敢開槍打女人,還敢打老子?借你個膽吧。他漫不經心地轉過身,沖著戰士們一揮手說,走。
突然,一聲槍響,吳燁感到腦瓜“嘭”地一炸,耳邊響起刺耳的囂叫。當他看見張排副應聲倒下時,自己手里那支槍管還冒著煙的槍無力地滑落到地上,他兩腿一軟,一屁股坐了下去,像傻子一樣地呆住了。張排副破口大罵,掙扎著要拿槍和吳燁拼命,幾個戰士趕忙連摁再勸地把他拉住。直到鮮血從張排副單薄的褲腿滲了出來,吳燁才清醒過來,他一下撲到張排副跟前,一把撕開他的褲腿趕緊給他包扎。包扎完傷口,他像個做了違心的事又找引子為自己開脫的人,嘟嘟囔囔地說了句,還好,只蹭下塊皮。
父親說,就從那聲槍響之后,他耳朵就背了。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為什么父親不到六十歲就兩個耳朵都帶上了助聽器。
這時王尚明回來了,還帶著兩位當地干部。當地干部說,他們已經組織好了一百多人的擔架隊,個把小時就能把傷員轉移過河去,河對岸已經準備好了一列火車。吳燁讓王尚明組織傷員撤退,自己帶著戰士和衛生員到西邊山頭去阻擊敵人。從張排副身邊走過時,他一把抓住了吳燁的褲腿說,把老子帶上,老子不怕死,老子就是不想白送死。打仗你還嫩點。吳燁心一顫,對兩個戰士說,找副擔架,把他抬上。
敵人已經發現了停在河邊的列車,對山頭的攻擊更加猛烈了。密集的子彈颶風般的向吳燁他們卷來,周圍的空氣頓時變得熾熱,烤得人臉灼疼,作為掩體的土堆被掀起一股股塵浪,石頭頃刻間就被打成齏粉。這時王尚明跑來對吳燁說,抬擔架的老鄉看這邊打得這么激烈,心里也沒了底,說什么也不敢再過河了。列車上還有八十多個傷員沒有撤過河去。
張排副對吳燁說,你回去對他們說,有老子在,就是一只鳥也別想從這飛過去。吳燁說,不行,陣地上更需要人。王尚明你回去把這里的情況跟老鄉們說清楚。張排副很不屑地說,扯他媽的什么蛋,他說要是管用,就不來找你了。見吳燁猶豫不決的樣子,他不耐煩了,他說,老子改編后當過解放軍的副營長,你沒老子官大。現在老子命令你滾,快滾,不然老子就開槍了。
河對岸的干部和老鄉見吳燁他倆安然無恙地回來了,心里頓時塌實下來,很快就過河把剩下的傷員撤到了河對岸。就在他們準備把最后幾個傷員抬上列車的時候,河對岸的西邊山頭傳來了一陣劇烈的爆炸,隨后就寂靜無聲了。不一會兒,山坳里沖出了敵人的馬隊,揚起一片黃塵。只眨眼的工夫,敵人的馬隊就過了河,朝列車撲來,子彈不斷地打在列車上,已經能看清敵人的面目了。吳燁立刻命令司機開動列車,自己帶著兩個人飛快地趕到了尾車。臨時加掛的尾車上用沙袋做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吳燁一聲喊打,跑在前面的一排敵人一頭栽到馬下。他們邊打邊撤,二十多分鐘后終于把敵人甩掉了。第二天在天剛亮的時分,列車終于安全抵達目的地。
正像老人家當年在西柏坡那個農家小院里信心十足說的那樣:現在看來,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才一年的時間,形勢就有了一個根本的變化,解放軍由原來的戰略防御轉為戰略反攻,只用了五十二天就結束遼沈戰役,東北解放了。
一次,已經入關南下的吳燁到東北出差,順道去了兩個地方,一個是靈漳河,另一個就是原來的衛校。到了靈漳河他特意去了趟鄉政府,打聽那次阻擊戰戰士們的下落。一問他才知道參加戰斗的三十多個人全部犧牲了。他找到掩埋戰士尸體的老鄉,問看沒看到一個臉上有道長長刀疤的人。老鄉不假思索地說,那是條漢子。右腿炸沒了,滿嘴是血,還叼著塊東西。我們費了老大的勁才把嘴里的東西掏出來,一看是只耳朵。那天吳燁找人用木板給張排副立了塊碑,默默地在他墳前坐了許久。后來部隊報社的記者不知怎么知道了吳燁護送傷員的事,來采訪他,他沒講自己,卻跟記者說起了張排副。不過開槍打傷張排副那段他沒有講,他不愿把英雄身上弄得湯湯水水的。記者回去后寫了一篇《遲到的報告》的通訊,在部隊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文革期間這競成了一件他說不清楚的事。
解放后他轉業到地方,在一家軍工廠擔任黨委書記。文革剛一開始,來了兩個人找到他外調,說張排副是叛徒,逃跑時被他開槍擊斃的。他氣得直拍桌子,大聲地吼到,放屁。他是英雄,是烈士。沒過多久他也讓造反派揪出來了,其中的一大罪名是“特嫌”,說他開槍殺害了張排副。他知道他不把事情的原委說出來,他就不能洗刷潑在身上的臟水,可是在那個環境下,他什么都不能說,他要是說了,對不起死去的烈士,對不起烈士的家人。當年他沒跟部隊報社的記者說,現在就更不能說了。但他也清楚要是不說點什么,這一關是過不了的。斟酌再三,他對造反派說,他的槍是打了張排副,但那是槍走火,并且只受點傷,烈士是在同敵人的搏斗中犧牲的,犧牲得很壯烈。造反派根本不相信,還是把他關了起來。那些年不管怎么斗他打他,說他什么不對他都認帳,惟獨有兩點他不承認:說張排副是叛徒,他不承認。說他是殺害張排副的兇手,他不承認。
后來落實政策,許多老干部都重新安排了工作,他卻還被關著。最后人是放了出來,可問題得不到落實,遲遲不給安排工作。在他的檔案里,對他的歷史問題有這么一個結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他被吊起來了,整天呆在家里無所事事。本來就不愛說話的他,變得更沉悶了,常常躺在屋里的躺椅上,蓋著條毛毯,一呆就是半天。好幾年后,還是找到剛剛出來工作的王尚明,這才把他的問題搞清楚。
我至今還記得當年母親剛一聽完父親歷史問題的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消息就號啕大哭,父親卻只是用鼻子哼了一聲,推門獨自走了。那天晚上父親很晚才回家,他一進屋我就聞到一股濃重的酒味。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吳燁到衛校的時候,正趕上學校的課間操。他在學生隊伍里看到好幾個當年的同學,現在又被抽調來上學。同學們也認出他來,下了課間操同學們就圍了過來,望著他問這問那。他也打聽起其他同學的情況。一個同學突然說,我前些日子見到了韋穎,簡直就像變了個人。另一個同學說,我也見過她,就住在槐楊胡同最漂亮的院子里,還有傭人伺候著。吳燁的心一顫,他突然意識到在懵懂的意念中還有一份對她的牽掛,他的心里還為她留有一個空間。一當明白這些時,他感到臉上燒乎乎的,渾身燥熱,眼神也怯怯地慌亂起來。上課的鈴聲響了,同學們匆匆跟他告別,說好過兩天找他去玩。
后來我問起父親,就他的槍法為什么沒打著韋穎?一向威嚴的父親競像個淘氣的孩子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其實我知道她根本就沒有死,當時我就沒想用槍打她們倆,我就是恨,失望。
離開學校后,吳燁的情緒陡然低落下來,心里就像紅葡萄酒的瓶口硬塞進軟木塞似的,一陣陣地堵得慌。按說知道了韋穎的消息他應該高興,可在初始的激動退卻后,他更感到的是不知所措,應該怎樣面對韋穎呢?他還能跟她說什么呢?他茫然地在大街上走著,腳步一會兒急促,一會兒躊躇。最后他還是敲開了韋穎的院門,一個女傭把他領到客廳坐下。客氣地給他倒了一杯茶。不一會兒就聽見客廳的走廊里傳來一個女人嬌嘀嘀的聲音,呦!是哪位先生這么早就來拜訪本姑娘呀?隨著聲音走進一個穿著絲緞旗袍的女人,燙著一頭大波浪的卷發,臉上搽著胭脂,嘴上涂著口紅。進了客廳她把叼在嘴角的香煙拿了出來,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夾住,翻翹著端在胸前。見到一身灰軍裝的吳燁她先是一愣,繼而驚訝地張大了嘴巴,香煙從她的指尖滑落到地上,她驚恐地尖叫了一聲,轉身跑走了。
吳燁不知自己是怎么從韋穎那走出來的,回到招待所渾身發冷,每個骨頭節都朝外透著涼氣,他裹著棉被躺下,迷糊糊地做著一個又一個的噩夢,午飯、晚飯都沒吃。第二天的早晨他剛被一個噩夢驚醒,就聽到屋外傳來急促的敲門聲,一個同學進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昨天,韋穎投井自殺了。他的腦瓜“嗡”的一聲,一屁股坐在床上。原打算還要住幾天,可他當天中午就去火車站買了車票,離開了這座城市,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父親對我說,這輩子總有一個夢纏著我:懸崖邊一只求助的手伸向我,就在我要抓住那只手的時候,那只手猶豫了一下,只一眨眼的工夫,那只手沒了。接著就是“啪,啪”的兩聲槍響。我總是在槍晌之后就驚醒了。
列車在站臺上人們熱情的期盼中緩緩地停住。校慶活動搞得特別好,那慶祝活動的熱烈,對老校友的崇敬和關懷,老同學相聚的興奮和激動,那場面那情景你就盡情的想吧,怎么想象都不過份。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王尚明叔叔也來了。他的身體一直不怎么好,從省軍區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下來后,原想是要好好休息休息,頤養天年,可沒幾年卻得了腦血栓,下肢不能行走,口齒也不那么清楚。他知道這次老同學都來相聚,尤其是父親也要來,他硬是讓閨女陪著驅車好幾百公里的趕來。他一見到父親立刻淚流滿面,坐在輪椅上,艱難的舉起不靈活的右手,認真地給父親敬了個軍禮。屋里的叔叔、阿姨都流淚了。我見父親蹲下來,緊緊抓住他的手,淚從父親的眼里淌了出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父親哭,當年奶奶去世的時候,我也沒見他掉過一滴淚。我們兄妹私底下都說父親的心一定特別硬。
校慶回來后,父親就病到了。他發著高燒,昏睡了三天,一會兒像是叫著什么人的名字,一會兒嘴里又嘟嘟囔囔說著誰也聽不清的胡話,把我們全家人都嚇壞了。
那天清晨,父親從昏睡中蘇醒過來,他睜開眼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竟是:我眼前紅紅的一片,但不都是血。我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我知道父親的眼睛沒毛病,那是他的錯覺,可我不知道那紅紅的除了是血,還會是別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