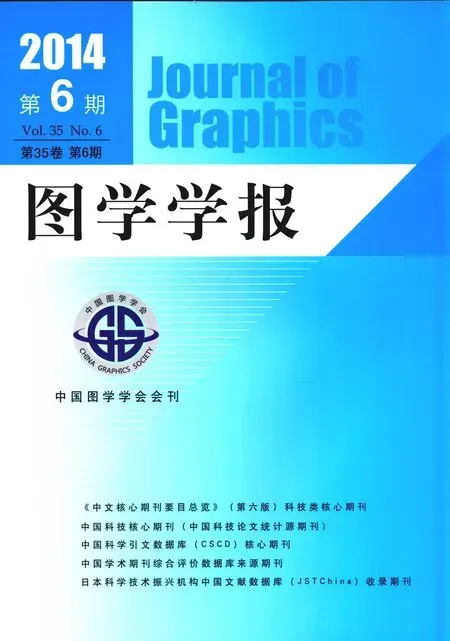圖學學報
- 基于掃描區(qū)間表示的不規(guī)則多邊形快速定位算法及應用
- 基于序列模型的三維矩形布局算法
- 用于空間態(tài)勢表達的海量空間目標可視化
- 熔融沉積快速成型零件成型方向的多目標優(yōu)化
- 云制造環(huán)境下制造設(shè)備云服務(wù)異常處理模型
- 飛機結(jié)構(gòu)件加工域單元分層識別及構(gòu)造方法
- 一種NSCT域多聚焦圖像融合新方法
- 基于顏色傳遞和對比度增強的夜視圖像彩色融合
- 基于多特征和多核學習的行人檢測方法的研究
- 基于碼書的霧天圖像質(zhì)量評價方法研究
- 基于幾何法立體圖像校正的研究
- 一種快速的基于稀疏表示的人臉識別算法
- 毛筆書法臨帖的計算機評價
- 混合動力汽車快速控制原型系統(tǒng)仿真平臺開發(fā)
- 三維數(shù)字重建在青銅器修復中的應用研究
- 土木類工程制圖課程的雙語教學模式探索與實踐
- 圖學在人類文明進展中的作用研究
- 應用直接立面法與輔助心點量點法繪制透視圖
- 以工程意識教育為導向的工程圖學能力培養(yǎng)方法探析
- 吊管機翻車保護結(jié)構(gòu)的有限元分析與試驗研究
- 合成孔徑聚焦超聲成像在混凝土探傷中的應用研究
- 刀具輪廓亞像素精度閾值分割算法研究
- 2014年總目次
- 第五屆中國圖學大會(China Graphics′2015)征文通知
- 中國圖學學會《圖學學報》2013年度優(yōu)秀論文評選結(jié)果
- 動態(tài)圖像的拼接與運動目標檢測方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