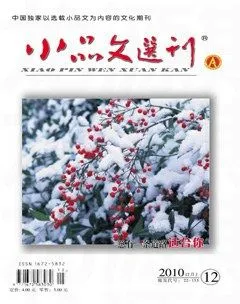云岡人
云岡礦對我來說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我到過那里。那時我的一位小兄弟與她的媳婦住在單身宿舍里,她們兩口子邀了文友若干,大家擠在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暢飲,我們談舊俗新習,我們談手頭雜亂而無法擱置的工作,我們談誰誰的走向運勢,我們談內心紛亂的想法,談到興致處舉杯共飲。最后,一位報社的朋友攤開了一張礦工報,礦工報的頭版頭條寫著前進中的云岡人。我是那種不喜歡前進、亦不談退步的人。但“云岡人”這三個字卻在我的內心里是一幅幅熟悉的畫面與場景,那懷舊的水就真的漫上了心際,濡濕了我的內心。
那是暢飲貪歡的一夜。有詩,有歌,簡單的生活因此而蔥郁。小憩蘇醒已是凌晨,為了趕著上班,拖著歡倦過了的身體,急急地踏上返歸的路途,云岡礦匆匆一瞥的景致就刻畫上了心。“云岡人”涵蓋著辛苦勞作的礦工,涵蓋著鋤地刨食的農民,涵蓋著涌流而來的外來勞工……那感人的背影,那歡愉的笑聲,做買賣的吆喝聲,陽光下的老者,月光里的琴聲,活生生的一幅清明上河圖啊!
今天的云岡溝正在經歷一場變革。北魏時期建造的云岡石窟現在已是世界文化遺產,作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這條曾經安詳的溝壑,如今正迎來各方的賓朋。一個地域的變化,也具備了人性的遷徙。記憶中的云岡鎮,云岡村,云岡人也在這樣的遷徙中觸動,感覺是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經,或許,它就在歲月的肌理之中而有知。城市滾滾涌流的激情,重新蕩起人們早已暗淡的熱度與表情。
我曾經把建在山坡上與佛為鄰的小屋稱作“安樂窩”,那是我理想的憩所,一壺酒,一簞食,一瓢飲,禪釋自我。誠然,追求與抵達永遠充滿了距離,沒有理由讓他們世世代代住在山坡,住在小屋。多年后,一場聲勢浩大的遷徙開始了。于普通的云岡人來講,滄桑的感覺具有悲喜交織的過程,這過程中每一個人都經歷著一場歷練,在這種歷練的過程中,糾葛就像斷了環的大鐘,碎了的巨響四溢的火花逐漸分散,進而淡定。真正的云岡人,他們有著大起大落的輪回,也有著一份真正的寵辱不驚,得失不計。
云岡人是普通的,同街面上任何人都相同,沒有標簽來甄別。石鑿的大佛也遭遇著風化的過程,更何況普通人乎?歷史上曾經抵達的輝煌與沒落,真正是幾千年的文明留下來的精神衣缽也要霧化?城市與城市在雜交中越來越相似,脾性、氣味、著裝、相貌,個人的理想、追求,一切都被重新組織,一切都被重新集中,殘存的痕跡在哪里?在云岡人那里。
云岡人同大佛一樣遭遇風化,也同大佛一樣保留自我。
石鑿的大佛朝拜者無數,他們求一份福祿,保一份平安,盼一日升遷,人不能解決的,到佛那里尋找答案,到佛那里歸置自己。云岡人是淡定的,他們要一種與佛為鄰的簡單,與佛為友的自然。誠如我的一位朋友、云岡詩人張智有一首詩:我愿意創造一片葉子/那種會說話的綠葉/用它飽含童音的濃汁/召喚那只羔羊/那只/緩緩走來的/做輕聲應答的羔羊。輕聲應答的羔羊與怒吼的雄獅更加堅定了我內心的唯美,所謂困惑的卻是為內心唯美的弱小而擔憂。
生在礦山長在礦山的我曾為一些街道而備受煎熬,壓抑與困惑,閉塞與落后,找不到心智微弱的亮光,也在佛前燒香,求一份寧靜,求一份內心的唯美。好在有眾多的人保留著內心的唯美。比如云岡人,他們不時尚,他們不追星,他們的遭遇,他們的困惑,他們的歷史變遷都是隨著大的變化而改變,留存的卻是做人的一份底氣,那十足的底氣就像蒼老遒勁的古松,這就是云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