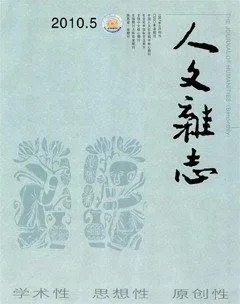漢魏之際的人物評論與士風變遷
內容提要 東漢末年人物評論的興起,是多種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勢的現實壓力、鄉舉里選的傳統影響、名士系統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評論的權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貫大多屬于文化核心區。人物評論的內容主要圍繞才和性而進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標,同鄉關系更是重中之重。評論活動由不同地域不同層次的評論軸心構成重層結構。漢魏革命,名士系統的人物評論被官方賦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結性的社會體系逐漸形成。士人風尚隨評論風氣的漲落發生轉變:漢末剛大方正的儒風,以道家風貌為過渡,轉型為魏晉時期的浮華之風。
關鍵詞 漢魏之際 名士系統 人物評論 地域意識 士風變遷
[中圖分類號]K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0)05-0127-08
漢末中央政府失序,選官體系紊亂,諳熟經籍的士子仕途艱難,東漢統治階層內部醞釀著激烈的沖突,最終體現為黨錮之禍。以黨錮為分水嶺,學界研究漢魏士人的政治史、思想史可謂不遺余力。作為對中央政府失序刺激的回應,漢末名士系統依托地域意識的蘇醒,在黨錮前后得以確立,名士系統的重要活動是在政治體制外進行大范圍的人物評論,人物評論風氣的高漲在某種程度上是漢代鄉舉里選的回光返照。漢魏革命,九品官人法確立,政府賦予中正以官人之法,凝結性的社會等級逐漸形成,士族社會由此確立,此為中古社會轉型之關鍵。鑒于此,筆者致力于考察名士系統、人物評論與地域意識的互生關系,探討漢魏士風變遷的內在理路,以深刻理解魏晉時期士族社會的形成。
一、評論風氣的形成環境
東漢晚季,社會問題在各個層面凸顯出來,就統治階層而言,屬于上層階級的豪族勢力出現分化之勢:屬于濁流的地方豪強,以外戚和宦官為代表,富而無知,不擇手段聚斂財富,覬覦權柄,置儒家道德于不顧;屬于清流的地方豪族,以士大夫為代表,不甚富而有知,服膺儒家倫理的價值觀,沒有霸占大量財富的欲望。@同屬濁流勢力的外戚和宦官視鄉里評論如無物,崇尚威權,輪流把持朝政,隨意安插濁流子弟和附庸人物進人政府機構,堵塞士子正常的入仕途徑,正常的選官秩序變得紊亂不堪,這就破壞了東漢社會階層流動的均衡態勢。莘莘士子學而優卻不能仕,群起反擊,激烈批評破壞晉身之階的黑暗政治。士人抵抗的手段是大規模發動社會輿論,其依托便是名士系統的卓然自立。黨錮迫使體制內的“官僚——名士”群回歸地方,與地方豪強和光同塵,名士陣線迅速擴大。三君、八顧之類的名士秩序與政府體制毫無關聯,名士系統的形成是門生故吏“二重的君主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漢末名士李膺等煽揚論政之風,袁宏評論到,“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托以謠言。”任何時代都有人物評論的現象,但是漢末的人物評論豁然之間成為社會風尚,賢達士子莫不如此,京師州郡皆慕其風,除卻儒家理念如“天下無道,處士橫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長期熏陶外,尚有選官體系紊亂致使士子仕宦無門的現實原因,同時具備更為深刻的社會基礎。
人物評論與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度關系密切。鄉舉里選,是兩漢察舉選官的重要精神,即以人物居住鄉里的公眾評論,作為選舉的基本依據。漢和帝發布詔令“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所謂鄉曲評論,就是一種群體性的人物評論FFG6S9KnviRRfVKNdGA5Gg==,主持人多為耆舊父老級的民間領袖。鄉曲評論對人物的名聲沉浮、仕途進退都產生莫大影響。清人顧亭林洞若觀火的指出,鄉曲公論就是清議,“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政府選官離不開鄉曲的人物評論,甚至任官之后還必須接受鄉曲評論的監督。漢末鄉舉里選的公眾評論依然存在,卻不再分布中國各地,而是形成類似月旦評一樣的評論中心、評論權力操持于少數人手中的評論態勢。常態的鄉曲評論與漢末人物評論的差異在于,大批精英名士、太學生及其同志好友進入評論團體之中,形成意見領袖群。名士系統的卓然自立,加劇了人物評論的漫延之勢:漢末的人物評論從地方走向全國,從選舉制度的有機組成變成對抗選官體系的行為。
人物評論成為時代特色、并且成為世人普遍感興趣的歷史現象,不是旦夕之間,其淵源見于馬援警誡子侄好議論之時,“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愿聞子孫有此行也。”馬援的誡言表明,東漢初期,整個社會開始流行尚俠好義的風氣,與這種風氣亦步亦趨,士人評論之風起于青萍之末,“好論議人長短”成為士人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東漢初期的人物評論只是個別性的出現,尚未形成社會風氣,也沒有深入士大夫之心。東漢末期,人物評論之風大盛,評論主角不再是鄉曲評論的父老級人物,而是以名士為主體的人物評論家。翻檢漢魏史籍,士林的意見領袖諸如潁川荀淑、潁川茍或、潁川司馬微、山陽仲長統、山陽度尚、陳留田盛、陳留韓卓、沛國曹騰、汝南謝甄、南陽何頤、北海鄭玄、北海孔融等善于知人,明識人倫、獎拔賢達。其中影響最大的意見領袖是許劭和郭泰,“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許劭和郭泰核論鄉黨,品評人物,進善黜惡,所舉人物仕途通暢,所貶人物如墮深淵,正如魯迅所云“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于片言”。
對上述評論家的籍貫出身進行簡單分析,發現眾多評論家的籍貫大致是陳留、汝南、潁川三郡。據學者量化分析,這三地為東漢文化核心區,地處洛陽附近,易于接受儒學教育,文化教育極為昌明,士子薈萃,清談盛行。相鄰三郡出產的士人如雨后春筍,數量之多、名望之高遠遠超過其它郡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物評論家和黨錮人士之間存在很大的交集,評論家的要務是通過評論人物影響鄉舉里選,進而改變政治資源的過渡傾斜,因而他們是兩面體的結合:一面是退居鄉里、無心仕宦的處士,另一面卻是評論人物、改良政治的黨人。
二、評論內容的認識
人物的批評鑒識,又稱為“品藻”。《后漢書·郭太傳》稱贊郭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李賢注‘釋云,“禮記日:擇人必于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人物評論的實質就是對人物分門別類、定其等級。評論方式為“品題”,“品”指人物的才性高低,“題”就是對人物的簡單評語。人物評論就是通過品題劃定人物品類,如郭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此處所謂的“人品”不是指品格道德,而是品類等級。與此相應,士人在地方具有高低貴賤的座次表。名士座次表就是通過人物品題來確定的。時人又將天下士分為五個等次:鄉里士、縣廷士、州郡士、公輔士、天下士。具體查驗人物評論家的評語,結論大致不溢這個范圍。桓帝延熹九年(166)黨銦之后,政府強令黨人回歸鄉里,禁錮終身,造成“正直廢放,邪枉熾結”的局面。名士黨人不甘心退出政治領域,于是在政府體制外獨立創造一套名士系統,與之抗衡。名士系統內,有所謂三君、八顧、八及、八廚等,恰好與士的五個等次相對應。其時黨人互相標榜品題,名士領袖多冠以天下、海內的頭銜,評語多為七言諺語:前兩字表示士的等級,次兩字表示士的特性,后三字表示士的名號。評語中關于士的特性,無非是道德高潔和學術雅博。

學術雅博屬于“才”,道德高潔屬于“性”,才性問題是漢魏史上的重要課題,學人予以充分關注。王充認為評價人物有三大特征:才、性和命,尤其看重的是命。學術才能不能作偽,但道德問題卻可沽名釣譽,正是由于名聲高潔可以帶來諸多好處,浮華之風由此而起,囂然成為魏晉之際的主要風尚。盡管如此,士大夫所持道統觀浸然上升,儼然有凌駕政統之勢。郭泰同郡名士宋沖以“孔子”擬郭泰、符融評價郭泰“高雅奇偉”、李膺認為郭泰“高雅密博”。郭泰成名,得力于同郡及文化核心區名士的擁護。魏昭曾經對郭泰慨嘆,“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漢末亂局,士人心中的英雄人物不是風光顯赫的累世公卿、當朝軒冕和政治顯要。而是德行引人的經師,名士領袖李膺、陳蕃之所以能獲得太學生的擁戴,不是由于煊赫的政治地位,而是憑借文化地位和道德品質。王夫之云,“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能持,亦非茍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此所謂文化英雄觀,漢末名士在政治體制外,另立名士體系,以道統對抗政統,企圖重塑國家體制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均衡態勢。
人物評論的內容,大致為四個方面:一、服務仕宦、拔擢人才;二、抨擊邪佞、揭露腐敗;三、評價品格、褒揚德行;四、預測未來、占卜前途。其中第一條和第二條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這種政治性的批評未必興于后漢中期。后兩條則是關注士人群體自身的前途命運。東漢末期的人物評論,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與政治評論密切相關的話題,抨擊宦官專權,外戚攬政。抨擊風潮的發動者是以體制內的李膺、陳蕃等名士官僚為領袖、太學生為骨干的左翼名士群,采取激進手段發動抨擊政治的風潮,意圖在于改革政治、革新吏治。意見領袖群危言深論,采用極端手段——甚至不惜違反法律精神——打擊宗室外戚及濁流豪強,由此遭到當政者的反噬,是為兩次黨錮之禍。其二是與人物評論密切相關的話題,主要評論人物才干,德行風貌。操持者是以在野的郭泰、許劭等人為領袖、蕓蕓士子為支柱的右翼名士群,這種人物評論是漸進的改良政治的活動。兩個名士群主持的人物評論恰成鮮明對照,又互為補充。罹難黨錮的多是左翼名士群,右翼名士群不為危言核論,幸免于難。如,郭泰雖為名士共同體成員,卻韜光養晦,故能免于黨錮之禍。事實上,評論家在評論對象的選擇上,也有不同。郭泰所評論的對象大部分屬于尚未弱冠的青年俊杰,抑或是沒有仕宦的在野人物。質言之,郭泰的評論對象很少涉及清流士人深為痛絕的宦官及其主導的官僚體制,這正是“不為危言核論”的歷史內容。
東漢人物評論的方法大致是自外而內,即通過外表體貌特征推定內心本質。王充《論衡·骨相篇》載:“人命稟于天則有表候于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人物的體貌容止與選官制度密切相關,漢代選官的容止標準是身材高大、儀容端正、須美音大三個特征。魏晉之際以總結漢魏人物評論術而聞名的劉劭在《人物志》中提出評價人物的“九征”,實際上與重視人物體貌的精神一脈相承。東漢人物評論的形式多是預言未來,其中很多資料難以斷定是否可信,譬如班固年僅十三歲時,王充見到他就撫背感嘆:“此兒必記漢事。”預言性的評論如此離奇玄乎,難免讓人覺得這種資料是后人偽作。但是這種資料如此大規模地成群出現,原因至少有兩條,一是受東漢讖緯神學思想的影響,并對神學思想的反動,評論活動是以人物為中心而進行;二是漢末人物評論的氣氛比較濃厚的客觀反映。
人物評論標準歷經彌新,至郭泰和許劭時已經發生變化,人物的本相(才和性)成為評論的主要內容,至于表相(命)已經退居其后。《后漢書·郭太傳》載:“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所謂“卜相之書”,大致是陰陽家測算性命貴賤的方士書籍。郭泰對評論標準抽象意義的探求,已經形成人物評論的理論體系。《世說新語·政事篇》載:“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彥,六十余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繼之而起的許劭,在評論人物方面繼承郭泰的評論風格。郭泰成為人物評論的軸心,關鍵原因是能夠汰除以往理論中的蕪雜成分,如命相之說。郭泰“先言后驗”,與王充的不言而定,有著本質的差別。從郭泰的評論實例分析,絕大多數人員的評論情況得以驗證,可以想見郭泰必然有合乎情理的評論邏輯和品評方法。郭泰評價人物并不重視人物出身貴賤(命),而是看重才性高下、道德善惡。郭泰發明的評論術,與命相術已經完全剝離。郭泰評價人物無視人物出身與王充重視命之貴賤截然相反,或許與郭泰本人出身貧賤存在關聯。
人物評論內容中,另需注意的是評論家高度贊譽復仇之事。復仇是對現行體制不滿而采取的極端行為,但評論家予以高度評價,居然得到名士共同體的認可,應當看作是名士系統抗衡官僚體制的行為。郭泰對蘇不韋發人冢墓、蹂躪枯骨、以報仇怨的殘忍行為予以高度贊揚,又對同郡賈淑慢法滋事、快意恩仇、為舅雪恨的沖動行為進行援救。漢魏以降,復仇逐步遭到國家法律的嚴格禁止,但是存在不少例外,實際上,漢代的復仇風氣還是非常濃厚的。漢末名士蹈義忘利、慷慨激昂、士風高漲,與太原上黨由來已久的風俗頗有暗合之處。因此,蘇不韋掘人父冢的乖張行為,居然得到郭泰的贊揚。太原郡是復仇事件頻繁發生的地區,離不開當地社會風俗的影響,《漢書·地理志》載: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
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家屬。
太原、上黨一線相通,風俗相近如此,非為偶然,與地理因素外封閉而內通達相關,其地自戰國以降,任俠剽悍,粗俗豪放,尚武輕文。郭泰對復仇行徑出人意料的表彰,必須置于地方風俗的傳統影響、地方勢力競爭郡姓次序的現實利益以及評論風氣的高漲中考慮方得其筌。名士系統公然支持反秩序的復仇行為,與濁流人物破壞選官秩序的影響殊途同歸,共同促成帝國秩序的崩潰和瓦解。
三、人物評論的地域特征
人物評論和地域結合在一起,歷代都有,但程度不同。不同地域的人物比較優劣高下,是漢末士大夫群體自覺和地方主義高漲交互作用的結果。不同的地域環境,孕育不同風貌的人物,《漢書·地理志》載之甚詳。人物置于地域中進行評價,前代有之,如“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楚人勇,齊人怯”,但是這些人物評論是某一地域、某一環境與該地區所盛產的人物氣質,存在相生相潤的因果關系。評論對象被籠統地歸納于行政級別不一、范圍大小不同的區域進行抽象概括。
東漢中葉以降,以郡為地域單元的意識深入人心,表現在以郡為中心的地域評價塵囂云上,核心內容便是表彰州郡名流,以之凌駕于政府官僚之上,郡守刺史在人物評論的風氣中無所作為,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嘯”。地方上的郡因為名士涌現,由行政單元轉變為社會意義上的名郡,成為名士系統的地方載體。士人借名郡而顯明,州郡因名士而益貴,交互作用互相煽揚。合理的選官體系日漸凌夷,必然造成中央政府權威的消失和控御力的削弱,以郡為單位的地域意識日漸強烈,專門評述一地人物的地方志開始出現,漢末州郡涌現大批富有地方特色的史籍,這些書籍大部分是標榜和表彰地方州郡的賢達之士,多數冠以“耆舊”、“先賢”的美名,如《汝南先賢傳》、《巴蜀耆舊傳》、《山陽先賢傳》等等,這些地方名譽和“三君”“八顧”之類較為高級的名士序列相互影響,構成名士系統的堅實基礎。這類著作群的大規模涌現,其宗旨當然不僅是“褒善敘舊,以勸風俗”,而是對中央的一種對立,這種對立正是名士系統卓然自立的地域基礎。名士系統表現在地方上,便是地方主義的抬頭。名士系統在政府體制外另創“三君”“八顧”之類的稱號、在地方上依靠“耆舊”“先賢”的基礎,形成獨立體系。但是在名士系統內部,各以同郡人物自夸驕矜,正是鄉里地域生活圈形成的標志。名士系統的形成,以及名士系統內的地域分野,反映了漢末士人、地方州郡與中央政府之間漸行漸遠的實態。
漢末風俗,造謁拜見前輩名士,是不可偏廢的人倫風氣,更是利害攸關的日常行為。各地士大夫皆有部黨,同郡士人標榜援引之風大熾,地方主義逐日高漲。從這個意義上講,黨錮之禍的緣起是中央政府防止地域意識高漲的彈壓行為,歷經兩次黨錮,地域意識得以暫時壓制,卻以名士系統的姿態強勢存在。矜夸同郡名流,有諸多案例,學界廣泛征引的是孔融和陳群關于汝潁人物優劣的爭論,孔融力主汝南士勝潁川士,“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孔融以頡頏天子推尊汝南士人,“頡頏天子”在漢末名士系統形成、地方主義復蘇的社會環境中,指向意義無疑會被放大。頡頏天子不獨為汝南士人所有,太原王霸特立獨行,極力倡言“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郭泰聲名未著之前,汝南名士范滂贊揚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名士系統所持的道統精神抗衡官僚體制的強硬姿態,在東漢末葉體現的淋漓盡致。
同郡士人相互援引成為慣例,甚至在京師具有同鄉會所——郡邸。諸郡賢達獎拔同郡后進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人物評論,而評論對象不是隨意挑選,同鄉人物在評論對象中占有相當的比例。以郭泰品評士人為例,據《后漢書》本傳載其所提拔獎掖者六十余人,查驗史籍。具有名號者三十八人,再加上對郭泰進行評論的七人,合計四十五人。據此對郭泰評論人物的具體特征進行分析,茲將評論對象一人以上者的情況列表如下:
分析上表,可以發現郭泰評論人物的過程中明顯帶有地域特色,上述五郡中太原、云中同屬并州,兩郡十一人,占郭泰評論對象的31.7%;其他陳留、汝南為文化核心區,兩郡七人,占評論對象的20.4%,尚不及太原;扶風郡二人,應當出于和并州地緣接近的緣故。從上述統計數據即可看出,郭泰評論人物的地域范圍主要集中在三個地方:陳留、汝南以及太原。如果再結合對郭泰進行評論的人物籍貫,陳留士人將升至七人,汝南四人,太原十人,上述分析郭泰評論人物重視地域的特征將得以強化。郭泰對太原士人的獎掖,無一貶詞,郭泰評論的太原士子九人皆蔭其恩澤,名聲地位呈現上升之勢。即便是同鄉之中,郭泰的評論對象也有親疏,郭泰評論太原郡九人中,王氏家族成員為四人,占44.4%。漢末人物評論集中于一家,至為明顯。郭泰品評提拔的太原士人,最為顯貴的是祁縣王允。王允既有家世背景的內因支撐,又得同郡郭泰品評的外力援助,接替郭泰執掌漢末太原名士之牛耳。兩者不同的是:郭泰在野、王允在朝,郭泰以名聲動天下、王允以權術貴朝野。郭泰品評王允的象征意義通過王允的活動即可洞見。王允政治發達之后,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族人王宏為右扶風,王允弟懋為幽州刺史,又見同郡孫資而奇之。孫資是魏晉嬗代的關鍵人物。“郭泰一王允一孫資”這樣一個提拔同郡人的傳遞系列,集中反映出士人群體自覺、抬高郡望、相互援引的地域共同體特征。
郭泰評論人物重視同鄉關系外,對陳留、汝南兩郡人物格外看重,不僅因為這些地區是東漢文化核心區和清議盛行之地,也和其地人物對郭泰的評論密切相關。郭泰從貧賤子弟成為名士系統的“八顧”之首,主要得益于同郡宋沖、陳留符融、潁川李膺、汝南范滂、陳留蔡邕對其生前身后的高度贊揚。李膺師承同郡茍淑,荀淑以拔擢鄉間英彥而聞名,陳留符融又師事李膺,這樣就形成荀淑→李膺→符融→郭泰的評論軸心。由此可見,如果以郭泰為人物評論的參照物,我們發現郭泰既處身太原郡的評論軸心,也處身全國范圍的評論軸心,這就形成了評論活動的重層結構。
四、士風變遷的儒道因素
關于東漢士風的流變,范曄在《后漢書·黨錮傳》中描繪的較為傳神:
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幕襲,去就之節,重于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
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嫜直之風。于斯行矣。
研究者認為范嘩以桓靈為界限,將東漢士風分為兩個階段:隱匿高蹈、去就之節和品核公卿、嫜直之風。東漢立國將相多儒者氣象,文化氣氛濃厚,在這種崇尚知識的社會環境中,豪門子弟,即便是三公子孫,仍需“少好學”、“步行千萬里負笈求學”;同時考慮察舉制度的現實要求,士人在東漢社會中地位崇高,學問淵博和道德高潔成為東漢的至高美德。翻檢漢代史乘,士子在面臨政府征辟的時候,“不就”的情況屢見不鮮;皇帝王公前往拜訪儒生之事,多有發生。
我們恐怕不能斷然認為東漢一朝的士風轉變在桓靈之間或和帝年間,至少“去就之節”在東漢一朝一直獲得尊重。“去就之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內容。士人“婢直之風”的高漲,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主荒政繆”的現實原因。外戚宦官鳩占鵲巢,壟斷政治資源,堵塞士人延頸起踵的仕宦道路。二、士人地位崇高的生態環境,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之事時有發生。三、鄉曲公論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婢直之風”的形成與評論風氣的高漲亦步亦趨,動因亦大同小異。南朝范曄以降,對漢末黨人予以較高評價者。不絕如縷,最典型者首推顧炎武,他有感于明亡之禍,慨嘆漢末局勢云,“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③這種評論不可否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顯然沒有考慮到士人面臨的特殊環境和傳統影響。
黨錮之后,士人嬸直之風隨評論風氣的急轉直下而逐漸變弱,隱逸之風驟強。前者頗合儒家學說,后者則屬道家風貌。兩者變遷,絕非旦夕之間。黨錮之前,名士系統尚未成立,但采取隱逸方式對抗國家體制的名士不絕如縷;黨錮前后,名士系統正式形成,抗衡皇權,遭致血腥鎮壓,元氣大傷。喪失共同體的名士如鳥獸散,注意力從國家轉向家族,從中央轉向地方,如“八及”之一的劉表退居荊州,“八廚”之一的張邈龜縮兗州。流風所及,魏晉士大夫的士風轉變為戀家忘國,主持清議的剛正之士嬗變為隱逸君子,轉變的樞紐在于評論風氣的漲落。漢末士大夫由慷慨激昂、匹夫抗憤、舍身為國的儒家風尚轉向自適任情、避禍保身、持家忘國的道家風貌。與這種轉變配合的是,學術中心轉移至家族,學術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已為學界公論。學術家族化使中古極為有限的學術資源被家族壟斷,因此有累世公卿、累世經學之家族,于是產生大量門閥。學術家族化、地方主義復蘇、評論風氣落潮都是士風轉向道家風貌的客觀環境。同時應注意到,東漢中葉以降,地方名豪除卻信奉儒家道德主義之外,對老莊道學的逍遙自由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儒家式的道家人物大量涌現,即便很優秀的儒生,提倡儒家主流思想之余,難免熏染道家之風,表現出玄儒雙修的矛盾情結。具體來說,他們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清”的特征。名士系統的“清”與宦官外戚的“濁”形成對比,但是過度的“清”會滑向“介”,陳群曾經稱贊華歆“通而不泰,清而不介”。這個評語實際上隱含著雙面的觀念,即褒義的“清”會流于貶義的“介”,“介”是指胸襟狹窄。郭泰批評袁閎“清而易挹”,所謂“易挹”,就是胸懷不大,為人纖介。盡管如此,“清”作為東漢士大夫的傳統美德,在《后漢書》中以相關的詞匯頻繁出現,諸如“清平”、“清節”、“清識”、“清裁”等。“清談”一詞之構成,耐人尋味,“清”是士子所持之道,“談”是突出士人持道之手段。人物評論轉變為清談,與士風轉變相發明。
其二,“異”的特征。“見而異之”,是漢末人物評論經常出現的詞匯。士風流變,士子追逐之名,景仰之輩,已非高官顯宦。獨行之士層出不窮,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條記載:“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茍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獨行之士,以退為進,不求仕宦,甚或輕生死,重名節。《后漢書·范滂傳》載范母言,“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其時名士不但生前為人推重,死后亦有碑銘以頌之,例如郭泰卒,四方之士千余人來會葬,志同道合者刻石立碑;陳蹇卒,海內赴葬者三萬余人,門生弟子刊石立碑。集會之頻繁、清議之狂熱正是名士共同體形成的集中表現。謚號本為統治階層成員獨自享有,東漢以降,私謚之風大盛。私謚是門生弟子推崇師道尊嚴的集中表現,私謚之興,亦為人物評論之內容,代表道統已經凌駕于政統之上,是非臧否,權操名士。其他方面,至于漢魏之際名士好驢鳴、飲酒之無度、舉止之乖張,皆為士風嬗變中“異”的表征,這些特征與漢末“異”的特征存在差別,是由于評論風氣的變動所致。
其三,“逸”的特征。逸民的廣泛存在,被學者納入清流集團的右翼勢力。名士之逸,是對政府體制的消極對抗。郭泰出身貧賤,不愿給事縣廷的真實原因有兩層:其一是嫌棄官職低微,其二是士風影響所及,求學成名遠勝于供職政府。郭泰成名后,擁有司徒征辟的仕宦良機,卻斷然放棄。漢末如郭泰一樣對政府持疏離態度者,不在少數。郭泰之隱,并非真隱,而是對政府失望之極持觀望態度。黨錮禍后,郭泰的態度已經由觀望轉變為絕望,翌年郭泰卒。范滂之死固然悲壯,但他臨死時規勸其子,“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言辭之間,足見其心態之蕭條落寞。幸免黨錮的名士張儉洞見漢魏嬗代形勢已成,沒有抗爭,而是闔門歸隱。郭泰之死,許劭之隱,成為漢魏之際評論風氣衰歇、士風轉變的標志,忠君思想漸趨瓦解凌夷。
漢末人物評論的形成風氣是多種因素的合力:政治腐敗、選官失序、鄉論基礎、名士系統等。評論權力基本上掌控于名士之手,這些名士大多數是在野之人。曹魏肇建,九品中正制確立,人物評論的權力從鄉野名士轉移至中正之手,曹魏官僚化的中正制是對漢末人物評論的顛覆。馬端臨評價漢魏選官制度,“蓋鄉舉里選者,采毀譽于眾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漢魏革命,曹丕登基,眾大臣面露喜色,華歆則不悅,曹丕問其故,陳群回答說:“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漢魏士風由忠君愛國到保身全家的劇烈轉變,不啻為中古士風之大變局。士風變遷不僅標志著東漢帝國的政統走向盡頭,也表明東漢一朝的學術傳統和士林精神壽終正寢。漢末的人物評論大多具有實際內容,而魏晉清談則流于玄遠理趣,正如學人概括的六朝風氣之變遷:“由嚴肅而變為含糊,由明實而變為幽深玄奧”。東漢的人物評論是臧否人物,選拔賢才,而中正制度拔擢官吏則出于門閥考慮,正所謂以貴承貴、以賤承賤,凝結性的門閥體系逐漸形成,君權在士風轉變的過程中大為削弱。名士系統雖然破壞無遺,士族社會的門戶卻因此開啟。
責任編輯:黃